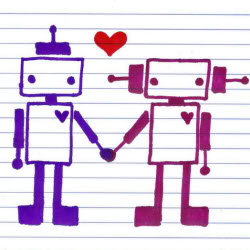隔壁家的那点事儿-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柯子末沉思片刻,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老爷子又道:“你觉得凭什么不会是你呢?
“……”
“老师你在逗我玩么?”柯子末无奈道。
“别胡思乱想了,安静待两天,”老爷子继续不紧不慢地浇花,“该有的总会有。”
柯子末回到自己的小屋里静坐,望着窗外,春寒料峭,柳梢添新绿,麻雀声扰人清闲。
他想,今年若是考不中,我还会等三年再考吗?若是一直考不中,我……
柯子末捂住自己的眼睛。
放榜那天,柯子末已经不记得自己都在考卷上胡扯了些什么,他唯一清楚的是,他不能输。
大红色的纸张,在天光微曦里略显黯淡,金色的大字好像长了翅膀要飞,他站在人群里,往前走了一步,又退了一步。
“柯子末,”他低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想好,你一定不能哭鼻子。”
旁边的同学奇怪地看他一眼。
柯子末走上前,只看到一片参差不齐的后脑勺,再往上,他抬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周围乱哄哄的声响都蓦地远离,他仿佛不认识那几个字了。
柯子末多年以后回想那一天,仍然只觉得冥冥之中连老天都在帮他。
四个月后,又逢中秋。
马车在空荡荡的官道上轻快前行,两旁高大的乔木郁郁森森,叶片间黄绿交杂,筛漏出斑驳的光线。
“公子,现在已进苍冉境地了。”
柯子末放下书,伸手撩开车帘探头望了望,“别停,走吧。”
“哎。”
时隔一年,他再度踏上返乡的路,他还记得那时自己的心情——平静的,还带点喜悦和惴惴不安,如今却是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去年初冬离开苍冉的一路上,柯子末浑浑噩噩,失魂落魄,无所适从,心里想着一个人,整日整日地想,想他身在何处,过得怎样,想他是不是也在惦念着自己,想他什么时候才回来。
想着想着,就不敢再想。
柯子末闭上眼睛往后靠住软垫,不由地感慨,到底还是回乡了,大约后半辈子也就在这过了。
当然,首先要把旧账算清。
陶台升,你给我等着。
八月,焕河城知府换任,御前钦点一品状元柯子末任焕河城知府。
随后,他四处搜集陶台升多年下来累积的罪证,详细写了一份奏折,上表朝廷。刑部受理此案,据说牵连甚广,苍冉郡一众大小官员均曾对其暗中贿赂,助他倒卖军饷、私通外敌、盘剥过往客商,陶台升本人更是在边境拥兵自重,欺压异族,并且跟前任知府沈惠的死脱不了干系。
皇帝看到折子勃然大怒,当下呵斥御史台纠察不力,派巡府前往焕河城。
巧的是,巡府正是柯子末同榜探花,与他颇有几分交情,陶台升拉拢无果。
十月,兵部、吏部、御史台接连转发三道圣旨,收去陶台升所有兵权,官降三级,削爵,抄家,流放北疆,无诏不得入京。
陶台升被押解进京的时候,柯子末前去送别巡府。
“陶大人,”他拱手笑笑,“一路顺风。”
陶台升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仰头大笑!
“柯大人,你也不过是个伪君子!”
柯子末负手,唇边的笑意冷了下来,“陶大人还是多操心点自己吧。”
十一月,柯子末上奏阐明苍冉郡形势,地域狭小山寨林立,不宜多建城池,知府与苍冉总兵分责不清,官制冗沉人浮于事,结党营私之流甚多,百姓怨声载道,肯请裁练精兵,选拔干将,减少官职名目,免去苛捐杂税。
朝廷争讨再三,最终同意了他的办法,并颁布圣旨,苍冉郡三城合并,撤知府衙门,设郡守提督府,命柯子末为首任苍冉提督,兼苍冉军主军参赞,在总兵到任之前代为督军。
“哎哎,瓜子壳别乱丢,你看你都扔到地上去了。”柯伯母拿扫帚敲敲藤椅腿。
柯子末懒洋洋的,“嗯,我一会儿扫扫。”
柯伯母没好气道:“省省吧,等你扫,能等到明天去!”
柯子末哼唧两下,不吭声了。
柯大叔走过来,抽着烟杆在门槛上坐下,咧嘴笑,“别说他了,你不是在扫地么,顺便扫了就行嘛。”
柯伯母叉腰看了他一眼,“我就是觉得他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特别碍眼。”
柯大叔吐出个烟圈,“你也省省吧,过两天他还得回去城里,和和气气的比什么不强。”
柯伯母叹口气。
秋夜的风略有萧瑟,卷过树梢和衣角,带来一丝冰凉的气息。
弦月高悬,残蝉歇晚,虫鸣声消停了许多,柯子末毫无睡意,在寨子里游荡。
像个孤魂野鬼。
柯子末非常烦躁,他挠挠头,转过身,顿住,又转过身,原地转了个圈。
“唉。”他拿着提督令牌看看,“我还真是傻。”
还以为扳倒陶台升之后缚刀凌就能回来,现在才想到,天下那么大,苍冉郡又在边境,缚刀凌跑到别国去,怎么会知道呢?
万一缚狐狸铁了心远走他乡一二十年不打算回来,上哪儿找他去?
柯子末慢慢拾阶而上,走到藏刀殿前的枫树下,金乌火还是那么漂亮,红叶遮天蔽日,如同烈烈的火焰。
他随手把令牌系在树枝上。
“送你了,神鸟。”
金乌火……它当然不会说话,就算会说话,估计也不想说什么了。
柯子末打个呵欠,终于感觉到一点困意,但是还不想睡。反正夜里没人,他就走进藏刀殿去看看。
殿中还是老样子,就像枫溪寨也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没变,毁掉的石像已经重砌好,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那把神刀了。
柯子末待了半个时辰,光是坐着不动,发呆。
好没意思,他有点失落,却说不清到底在失落什么,他又打个呵欠,决定回去洗洗睡觉。
“吱——”
嘹亮的破鸣犹如苍凉的呼唤,瞬间摄住人的心魂。
柯子末怔愣,随即奔出大殿。
一团飞鸟状火焰展开双翼,从高高的夜空俯冲而下,撞向地面,在他面前一瞬熄灭,又一瞬铺延开遍地火海。
在火焰的尽头,是红光潋滟的古老枫树。
满目的灿烂与明亮,灼热的风扑面而来,柯子末抬头远望,天空不复黑暗,被火光映红。
随后赤色的火焰黯淡下去,渐渐变为幽幽的蓝色。
柯子末屏住呼吸。
蓝色的火焰只及膝,在地面上勾勒出一个图案。
曾经他见到的,在缚刀凌的佩刀上——
一只狐狸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团子。
柯子末呆呆地看着,脑海中一片空白。
火红火红的枫树上跳下一个年轻男人,身后背着雪亮的长刀,眉眼间尽是温柔。
他朝柯子末走过来,停在台阶下,仰头凝望他。
他伸手,勾起唇角,“这块牌子不要了吗?”
柯子末一开口才发现说不出话来,全都堵在喉咙里。
缚刀凌严肃地点点头,“那好吧,我帮你收着,”说话间就揣进了怀里,然后腆着脸道,“怎么样肉末儿?有没有很好看啊?我琢磨了半个月呢,那烟花我自己做的!”
“……”
太扯了,我在那边郁闷得要死要活,你倒是闷着头捣鼓些小玩意儿,柯子末真想拿什么东西糊他一脸。
缚狐狸揪着衣角,忐忑地盯着他,见他看自己,赶紧摇尾巴。
“嘿嘿……”
“……”
柯子末气结,“滚。”
后来呢,缚刀凌就被自家媳妇儿领回去了,至于怎么挨揍挨训的,就不得而知了。
他确实杀了沈惠,但就像当初陶台升那样,现在焕河城柯子末说了算,他把罪名推给陶台升,也没人敢跟他计较,更何况刀族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缚刀凌为了讨好媳妇儿,在跑出去躲风头的日子里给酒楼打下手,跟大厨学手艺,现在能烧出一手好菜,天天变着花样喂饱肉末儿。
于是柯子末终于消了点气,特赦缚刀凌不用再打地铺了。
男人简直热泪盈眶,立马抱着铺盖卷滚到床上。
“喂喂,那边点!”柯子末嚷道:“衣服被你压皱了!”
缚刀凌趁机把人抱住,“媳妇儿……”
“什么?”
“相公……”男人改口。
柯子末满意地点点头,“说。”
“我……”
“打住。”柯子末捂住他的嘴,斜睨他,“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是。”
“……”缚刀凌瞬间整个人都亮了。
柯子末慢悠悠道:“你不就是饿了么。”
男人蔫了。
缚狐狸还真是好打发,好养活。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藏刀殿添了一把新的刀。
它是刀族这一代里最好的刀。
它的刀柄上刻了一只狐狸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团子。
它有个名字,叫姻缘。
作者有话要说:
☆、裴晓乾
“哗哗哗——”
算盘声充斥着不大的房间。
“哗哗哗——”
锦衣的公子斜卧在榻,午后的日光越过窗棂,照在他脸上,微微模糊了轮廓。
“少爷,安静。”
算盘声停了。
桌边的阿顿生呼出口气,继续埋头算账。
那锦衣公子百无聊赖,低头瞅了瞅手中的算盘,往旁边一扔,“阿顿生……”
“啊?”阿顿生头也不回,随口问,“啥事?”
“唔……其实也没事。”
“……”
阿顿生把最后一笔写完,揉了揉眼睛,叹息道:“少爷,这个月发给下人的月钱又不够了。”
“我们去隔壁借点?”
阿顿生简直要郁愤死,“裴晓乾!你能不能长点志气有点追求!”
裴晓乾,“……也去隔壁借点?”
“……”
阿顿生抹一把脸,直觉不能这么下去了,他语重心长道:“少爷,你是老爷亲儿子,你绝对是天生会做生意的,只要你肯学,世上无难事啊!”
裴晓乾歪歪头,“那看来我爹不是我爷爷亲生的,我家祖上种地。”
阿顿生没话说了。
确实,作为从小伺候少爷长大的小厮,他对裴家的发家史那真是门儿清,裴晓乾的爹——裴恪孝不知道是种地时哪根筋搭错,突发奇想去做买卖,在赔本赚吆喝了两年之后一下子财运亨通,又过五年,俨然把裴家弄成了土财主,不仅在宜元城添置豪宅,还开了家颇有派头的绸缎庄,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也不为过。
可惜,他后嗣稀薄,年近五十才得一子,也就是裴晓乾。
裴晓乾长大之后对他爹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嗤之以鼻——老子还只是“赔客笑”,儿子就要“赔小钱”了,再来个孙子还不得“赔干净”啊?重孙子是别想了,绝对“赔不起”的。
裴恪孝没活到古稀,不算高寿,但晚年无病无灾,倒是喜丧。他生前是个混不吝的、痞子样的生意人,当爹也没当好,更是养出裴晓乾这么个油盐不进铁打不动的懒人,可谓家门不幸。
裴晓乾在他爹罩着他的年月里那是少爷,在他爹撒手人寰之后隐约展露出堪当乞丐的才情,人人说他败家,兴致高昂地等待着裴少爷最体现人生如戏的那一天。
裴晓乾不在意。
仿佛真的不在意。
一个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但往往,外人喜欢用他们的眼光看你。
裴晓乾伸了个懒腰,“唔……好累。”
“……”阿顿生噎住,“你累?”
“是啊,”裴晓乾捏捏肩膀捶捶腰,“躺了两个时辰,浑身有点酸。”
阿顿生张张嘴,又赶快闭上,他怕自己一口老血会喷脏了面前半天才写好的账本。
自家少爷这秉性,应该习惯了才对,还能被他的话堵死,那说明是自己的问题。阿顿生拍拍胸口,安抚自己越来越铁打一样的小心肝,没事,这货特么的少爷脾气,不能计较。
“月钱不够?”裴晓乾忽然问道,“家里还有几个下人?”
“还有四个,管家一个,丫鬟一个,厨娘一个,车夫兼小厮一个。”
裴晓乾想了想,“不如把那个车夫辞了,我又没车。”
“……少爷,那个车夫是我,还有,我正职是小厮。”
裴晓乾愣了下,恍然大悟般——“原来是你啊,我说我怎么没见过他。”
阿顿生想挠墙。
裴晓乾又歪头想了想,“那就把除你之外的人都辞了。”
“……好吧。”
宜元城挺小,但是商贾云集,城中不乏豪门大户,也不乏土财主。
裴家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中……
咳咳,好吧,现在惨淡了点,说不定以后会更惨淡。
裴晓乾坐在饭桌边发呆。
阿顿生收拾收拾账本,从他旁边经过,奇怪道:“少爷你坐这干嘛?”
裴晓乾愣了愣,“中饭呢?”
“啊,因为我要去绸缎庄交账,所以就没做饭。”阿顿生理所当然道,“而且我们的存银不多了,省着点吃吧,早上剩的还有葱油饼,您要饿了就先垫垫肚子。”
裴晓乾呆了一瞬,笑了,“阿顿生,咱们已经揭不开锅了吗?”
阿顿生狐疑地望向他,“你还笑得出来?”
裴晓乾往椅背上一靠,懒懒道:“为什么笑不出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呲牙一笑福寿安康。”
阿顿生抱头哀嚎,“我不跟你说话了我会疯的!”
裴晓乾淡定地喝口茶,摸摸下巴,冲他勾勾指头。
阿顿生擦一把辛酸泪,走过去,俩人大眼对小眼,相对无话。
半晌,阿顿生道:“啥事?”
裴晓乾道:“看你疯了没。”
阿顿生又要叫,裴晓乾先一步让他憋了回去,“不逗你了,就是要跟你说件事。”
“……?”
“我们把那个绸缎庄盘出去,要是盘不出去就清仓贱卖,然后把地契当掉,”裴晓乾神色很认真,一点不像在开玩笑,“酒楼关门,辞退所有人,杂货铺的掌柜、帐房、伙计都不要了,以后每天我们亲自去打理生意,听清楚了吗?”
阿顿生震惊地睁大眼睛,像是不认识自家少爷了。
裴晓乾沉吟片刻,又道:“在我房子后边砌堵墙,把后院隔开,找人打口井,院墙上开个门,然后把它租出去,告示就贴到铺子门口,房租一月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