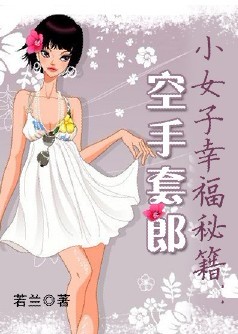真假状元郎-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担,若说不会不安,怕是没人会相信。
“不是我……”想来岳心凡也是极端不安的,这一下变故,对二人来说未知更多,将来会如何,已经不是他们能左右的了的了。
本以为可以安安分分编史读书,却偏就叫他们遇到了几位大官出差公干、却路遇风暴葬身运河这样荒唐的事情。可笑偌大□□,一时竟然找不到可以顶替的人——或者说,这几个职位对于朝中帮派而言,无疑成了从天而降的肥缺,只要借机抓住了,没准以后就可以坐稳,便有了稳固的地位。对于圣上而言,不论哪一派势力大了,都不是好事。幸运的是,赵天志是他的人,赵天志推荐的,自然也是毫无疑问的“自己人”。
这个人,正是岳心凡。
朝中几位重臣的损失,是天灾,那么朝堂中波涛暗涌以至于夹杂在中间的小鱼儿不得不随波逐流,便是人祸了。
岳心元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十九、一隅苏杭
一声清脆的响声在脚边炸开,这是钏儿这天打碎的第三个碗。
她有些心神不宁的匆匆收拾了,手指却不小心划过锋利的碎片边缘,于是浓浓的药香里混了淡淡血腥。
这是给岳心元的药粥,她专门去向任大夫讨来的方法做的。
自打上次朝中几位重臣意外出事,岳心元以岳心凡的名义临危受命担任要职,因为职务需要,除了四处奔波,便是住在宫里,一年来回府里待的日子十个手指头都可以数的完。又是自强惯了的,连钏儿也没带在身边。好不容易急招人才的大考结束,审完了卷子忙完了吏部礼部的事,皇帝才恩准其在放榜这几日告假回府稍作休息。
这一回来却着实吓坏了府里的人。
岳心元本就瘦弱,肤白齿皓,罩着一身浅色宽袖长衫衣带当风,蝉衫竹架,淡雅脱俗。而如今,虽然容颜不改,却是形销骨立,苍白憔悴得好像病入膏肓之人,回府不久便又睡得昏天黑地,问过这些日子一直在为他打下手的文官才知道,这一年来他的嗜睡之症竟是愈发严重。不是没找大夫看过,甚至几次还被赵天志押着不许工作等人去请太医,只是连为太后治好了多年顽疾有神医之誉的太医院首都诊不出端倪,一套说辞与一年前的任大夫不谋而合。
时隔一年,房间里又燃起了岳心元惯用的香。想来在宫里也没离去,让人总觉得这独特的清香已渗入骨子里。过去钏儿觉得那是清高遗世,如今看着袅袅青烟里岳心元苍白的脸和瘦的仿佛只剩皮包骨的身形,她却觉得可怖。一种生怕眼前人随时都会驾着这烟云乘风而去的恐惧感。
“钏儿,你没事吧?”听见响声,阿东匆匆走进来,看见她冒血的手指头,心疼的皱起了眉头,“啊呀……怎么这么不小心!来,我来收拾,你去找点药膏包一下手!”
“没事……我没事……”钏儿摇摇头,紧蹙的眉却是丝毫没有放松。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样子……”阿东见她这站也站不住的样子,只觉得十分担忧。
“我——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看少爷那个样子……我……我……”说着,竟急的掉下泪来,“阿东……你说、你说少爷他会不会……”
“别胡说,”阿东严肃的制止他,“管家是爷的兄长,爷怎么会让他有个什么呢?一定会想办法的——你就别在这里胡思乱想了,你看、这厨房还要收拾……”
一边说着,阿东一边弯腰去收拾。钏儿看着他,心不在焉的道着谢,也不顾手上正冒着血,重新倒了一碗粥,匆匆出了厨房。
“对了,钏儿!”阿东却在这时追了出来,“昨儿个霖烟坊的老板将管家的香料送了来,我给放在了你们外间暖阁的橱子里,你记得拿给他。”说着又憨厚的笑了起来,“我是不太懂,不过感觉管家那么妙的人物,跟这些香啊烟啊的,还真不是一般的衬。”
钏儿知他在安慰自己,感激的笑笑,端着托盘转身离去。
回到院子里,正巧岳心元醒着。
岳心元并不是个奢侈浪费之徒,只是能享受的时候绝不含糊。初入状元府的时候,岳心元便将自己住的小院彻底改造了一番——命人运来了山石草木,引水作塘,搭了亭台楼阁,住在其中,如临画里。赵天志第一次来便称赞为“一隅纳苏杭”。
而此时岳心元便坐在临水的一块平整石板上,靠着假山,神情慵懒,一身青色衣衫几乎要与满园翠绿融为一体。
听他那个在吏部的副手说,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睡过去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醒,所以醒着的时候,他工作的卖命程度“就像发狂了一般”,这是那个副手的原话。
好在大考结束,只要有新官上任,他就可以好好休息调养了。
想到这里,钏儿的心神定了定,这才走到岳心元身边。
“少爷……”
“嗯?”岳心元闻声回过头,看到钏儿这副样子不觉苦笑起来,“又让你担心了。”
钏儿不语,眼泪却是不停的掉。
“别哭了,与其哭的什么也看不清,倒不如再看看我们这小院子,回头……可就见不着啦。”
这话里的意思,钏儿不敢去猜,也不敢猜。
“少爷你——你要走么?”
岳心元点点头,又摇摇头:“是‘我们’——左右我说我要离开,你也不会让我一个人走,不是么?”
“钏儿曾立誓,愿终生侍奉少爷左右!”
岳心元叹口气,并非劝解,只是无奈:“可是你分明知道,我也并不希望你为了我牺牲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岳心元此生注定孤身,而你……”
“少爷请不要说了,若不是少爷,钏儿现在早已不知身在何处!”钏儿急急打断他的话,“能伺候少爷就是钏儿这辈子最大的福气……钏儿什么都不要,只求跟在少爷身边伺候少爷!”
又是一声长叹,岳心元发现自从自己考下这状元来,叹息的次数快要赶上过去二十余年。
“只是少爷……您要去哪?”虽然自幼担负起照顾岳心元饮食起居的责任,却也一直被岳心元当做胞妹照料的钏儿毕竟还是少女心性,何况她不满岳心凡已久,对于岳心元要离开一事,反而是比他还要期待。
“这个么……还是要看天意。”
“天意?”钏儿觉得好笑,“您莫不是打算做个竹筏子,随着大江而下,漂到哪算哪?”
此时岳心元正在喝钏儿端来的粥,一听这话,险些没有被她呛死。
“少爷!”钏儿吓了一跳,手忙脚乱为他顺气。
“我没事……”一边咳着,岳心元好歹是没有笑得岔气,点了点钏儿的鼻子,“你啊……”
钏儿吐了吐舌头,也不敢狡辩。
倒是岳心元坦然开口:“此番大考,心凡也是参加了的。以他的才学……若是好运,兴许能中个进士……”说着摇了摇头,“也不尽然,他满心尽是那人,一心想证明自己,反倒会弄不好,估计是要名落孙山。”
“那……”
“那时,这世上便只有一个状元岳心凡,一个草莽之夫岳心元了。”岳心元笑道,笑容却没有保持太久,只因这小院中凭空出现的第三人声。
“堂堂状元郎远离朝堂去做个乡野草民,是否有些大材小用?”
另一袭青衣从郁郁葱葱的矮树边走了出来,却不是赵天志是谁?
二十、深山含笑
“贤弟好兴致,耍了圣上与满朝文武一通,如今玩儿够了便要走了?”说着笑语,口气却是冷得厉害,更何况赵天志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表情。
赵天志向来是笑脸待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朝中对头私下提起,无不怒骂“笑面虎”,却只有熟识的人才知道,他脸上越是看不出感情,才越是怒的厉害。
这一年之内,岳心元恰巧成了这熟识之一。
有次钦命要案,牵涉众多,宰相赵天志主审,岳心元作为代吏部尚书旁听作辅,只见他面无表情,口中逼问却是字字狠戾,只把那买凶烧了京城三条街、灭了几户大家的主犯逼得跪在堂前连头也抬不起,一个贪生怕死之辈生生起了自刎谢罪的念头,却又被及时制止——而后,判了凌迟之刑,株连九族。
那一次,让岳心元明白这个男人的狠绝,也让他领教了惹怒他的下场。
而如今,他这般怒视着自己,是说,满门抄斩的命运,终究是躲不过了?
岳心元感到有些悲哀,只因自己一时私心,连累岳家上下数十口。
似乎还有一丝怒气,对赵天志,却不知因何。
“赵相这话可是冤枉了岳某,区区草民,纵使食了熊心豹胆,又怎敢欺瞒圣上。”挥挥手示意钏儿先行离去,岳心元开口,语气是一如既往的谦卑,眉头却是紧蹙。
“草民?你堂堂金科状元,代吏部尚书同礼部侍郎,见我不称下官也就罢了,何时又成了草民?”
“赵相怕是认错人了。草民心元,乃是状元府的管家。”
赵天志狠狠一甩袖子:“这里就你我二人,方才是我亲耳所闻,你还不承认,是不是?!”
“承认什么,草民不知。”岳心元垂眸。
方才在场只有三人,钏儿是岳心元的贴身侍女,自是向着自家主子,若要拿到公堂上,无凭无据赵天志也只会讨个没趣。
岳心元就是料定了这点,才敢这么死不认账,一心赖也要赖过去。
“岳心元,你、你当我赵天志是什么人?!”
“大人是一国之相,草民岂敢欺瞒。”
“一国之相?岂敢欺瞒?连圣上都被你蒙在鼓里!”赵天志一把扣住岳心元过于消瘦的手臂,强迫他抬头看自己,“你就以为我当真分不清你们兄弟二人,就可以这么由着你们胡来是不是?!岳心元,你当我是瞎的么?”
“草民不敢,草民斗胆请问赵相,因何在此质问草民?若是怀疑草民有欺君之嫌,何不将草民带进大堂上去审讯?”
“你以为我不敢?”
看着眼前气得眼睛里恨不能喷出火的男人,岳心元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赵相,”他轻唤,“您失态了。”
“失态,呵……”赵天志忽而怪笑一声,松了抓红了岳心元手腕的手,“连心都失了,还有什么必要惺惺作态?”
岳心元愣住。
他万万没有想到赵天志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吐露心声,让他毫无防备。
“别躲!”察觉到岳心元本能的逃避,赵天志猛地抓住他的肩膀,迫使他对上自己的眼睛,那里面太过强烈的感情,藏也藏不住,“你分明知道我在想什么的!你分明一直知道!”
岳心元看着眼前几近疯狂的男人,谈笑如风的他,何曾有过这种神情?不是不知道他为谁,只是这份感情太过沉重,他岳心元,受不起。
“心元不知。心元卑微,见过赵相几次?能称得上是‘点头之交’已是大人抬爱,又岂敢妄猜大人心思?”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看着眼前人冷静的近乎冷漠的眸子,赵天志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你——到底还是不承认?”
“心元不懂赵相所言。”
“好……好!”赵天志气得咬牙切齿,狠狠甩开抓在手里的岳心元的手,“你既无情,便休怪我无义!我今日就是赌上这颗头,也要证明你就是岳心凡!”
“……”岳心元张了张口,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头脑有些晕眩,他不觉苦笑。
这些时候来的经验,若是急了怒了,便会头晕目眩,然后……就会昏迷不醒。
“怎么?”
“您证明不了的……”淡淡叹口气,岳心元背对赵天志,面向水塘,水塘不深,却也不浅,刚好是水浅绿将蓝的最好看的颜色,潋滟清波刚好能将岸上人一脸愁容扭曲成三分笑意,“因为我就是岳心元,而非岳心凡……”
回答他的,是赵天志冷哼一声,和决然而去的脚步。
头突突的疼,眼中已是黑云罩顶,什么都看不清,他摸索着抓住之前依靠的假山石,想借此维持住站立的状态。
然,只是一时。
赵天志负气而去,出了岳心元的院子却又后悔起来。两人相识也已近两年,要不是自己总是做出这副正人君子刚正不阿的嘴脸,怕是换了谁都不信。总以为是心意相通,或许只是他自作多情也未必?毕竟这世上……退一步说,就算原本如他所求,自己摆出这么一副判案求证的面孔,他心中有怨也是理所当然。
想到这里,赵天志更加觉得自己混蛋之极,当下也顾不得什么面子,转身便回到了岳心元的小院。
便看到了让他的心跳生生一滞的一幕。
令他想都没想都跟着一步跳进水塘的一幕。
“心元!心元!”死命将人托出水面放到一块平整的石板上,轻拍着他的脸。
好在岳心元刚掉进水便被他救了上来,并未喝多少水,咳了一会,呼吸便渐渐恢复顺畅,只是人依旧昏迷不醒。一身薄衫被水湿透变成深色贴在身上,更显得人面白如纸瘦弱不堪,赵天志慌忙将他打横抱起来要带回房。
一缕异香却在此时飘入鼻翼。
深山含笑……?
二十一、毒
赵天志手肘支着桌面,拇指和中指用力捏着两边太阳穴,却仍是展不开眉心。
“大人。”坐在一边研究手中物事半天没有说话的人这时终于出声,引得赵天志急忙抬头看他,“不会有错,这香料里面确实被人掺了东西。”
“是什么?!”
“这是一种叫做‘梦浮生’的迷药,用于安神香中,少量可起到静气安神的作用,而过多则会使人昏然嗜睡,长时间过量使用,便会昏迷不醒,最终不知不觉间丧生。”老大夫不愧为太医院首,博闻强识,连这种世人鲜知的药都认得,也省去了他的一番麻烦,“这种药一般都调在普通香料中,无色无臭,极难察觉,只是沾了水汽便会有较为明显的类似于松脂焚烧之味。”
赵天志抖了抖,复又开口:“那这香料里的药量……”
“实不相瞒,以赵相您带来这香料中混的‘梦浮生’之量夺人命,恐怕用不了两年。”
赵天志身形一晃,险些向后倒去。
“可有——可有方法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