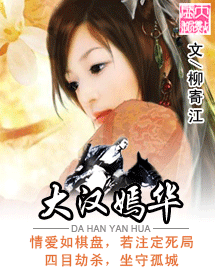大汉歌姬-第9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料,那华玉娃却突然间跟发了狂似的,她站起来,扑向我,抓着我的手臂,摇得我快散了骨架,“夫人,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肯不肯救司马大人?你要救他,不然就来不及了,我听说,陛下已经准备下旨,要将司马大人充军塞外。”
什么?充军塞外?
骨架,终于被震散,一时之间便如同三魂失了两魂,心神大乱。
阿满已然上前,拉扯着玉娃,想把她拉开。不想华玉娃却像足下生了根似的,阿满拉不动她,只得招呼其他的宫人进屋,七八双手一齐使力,才将她拽离我。
最后,华玉娃几乎是让人架着拖出了常宁殿,她的双脚依然不甘地向前蹬着,她的叫声凄如厉鬼,“夫人,你好狠的心,好狠的心……”
我堵住耳朵,却挡不住那凄厉,我不害怕玉娃的凄厉,我只害怕有朝一日我的凄厉会胜她千倍。我怕司马洛等不及我学成,就要被汉宣帝送到那大漠黄沙苦寒之地。
不能再耽搁了,我一定要尽快练好曲子!勉强自己静下心,将双手置于琴面,可是我静不了心,旋律越加散漫无神,
“夫人”阿满走过来,想是要安慰我,却让我厉声一喝。
“滚!滚出去!”
不用抬头,我也知道自己肯定又伤到了阿满,但我却是连安抚她的力气都没了。魏夫人站了起来,好像低低地跟阿满说了句什么,阿满低低地应了一声,便出了门,走远了。
魏夫人又把那门重新关好,才回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子服,你也别太着急,不错,我也听闻陛下似有此意,但陛下也还在犹豫。你还有机会,我保证,在陛下下定决心之前,让你尽快将此曲练到炉火纯青,便与,”语声颤了一颤,“便与他一般无二。”
叫人洞察心思的愕然一惊,“夫人,你,猜到了?”
魏夫人哀哀一笑,“子服,你用心之良苦,实非常人可比,亦非常人能解。”
今天两更。明天会多加一更。
魏夫人果然说到做到,更加悉心地指导我,她干脆住在了常宁殿,陪着我熬那一个个的白天、一个个的夜晚。
终于,借她吉言,有一天,在汉宣帝尚未痛下决断之前,魏夫人告诉我,虽然我仍未学到那十成十,却已经有了七八分的相似。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稍稍放下了些许,魏夫人望着我,忽生感叹,“子服,我到底见你笑了,真不容易啊。”
我无语,沉默,听见魏夫人又问:“子服,你可知,你弹的这把琴,叫什么名字?”
我不解她这一问的用意,她走到我面前,伸臂抚那琴弦,便像是抚着情人一般的留恋。
“子服,此琴名作深绝,得自于子服曾对我念过一句诗。”她的声音里流淌着的,是和那名字一样的,深;绝。
“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心下一震,勉强地道:“夫人,这诗也便只有一个深字,但不知那绝从何而来?”
魏夫人的回答,意味深长,“这就是我想告诉子服的,倘若子服还不能慧剑断情,终有一日会将萧郎逼上那绝路。”与此同时,抚于琴面的手指猛地一拨,金弦骤鸣,铿锵作响,绝音直欲入心。
琴声未息,阿满叩门,却是送茶点来了。魏夫人立马走开,我也故作淡然,只将这“深绝”搁在心头翻腾。
阿满放下茶点,并未离开,面色犹豫,欲言又止。近来,大概是我过于情绪化,就连阿满在我跟前也变得有些畏缩。
我叹了口气,“阿满,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阿满仍在埋伏笔,“夫人,有件事,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笑了一笑,“阿满,难道我不让你讲,你便不讲了么?你进来,不就是想告诉我的么?”
阿满一愣,魏夫人亦好心情地调侃阿满,“你这丫头,也敢在子服面前耍心眼,你不知道你家夫人,才是那耍心眼的祖宗。
阿满见惯了魏夫人不苟言笑的模样,不由更是愕然,继而腼腆,我挑眉向魏夫人:“夫人这是在夸奖子服么?夫人的夸奖,只这一句,最是悦耳。”
我们三人均是会心一笑,室内气氛顿时轻松。只可惜这难得的轻松,却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阿满带给我们一个消息,昨夜,汉宣帝又新宠了掖庭的一名女子,一个舞伎,华玉娃。据闻,此女是在宣帝半醉半醒之时,主动献歌献舞,极尽媚态,迷得宣帝神魂颠倒,这才脱颖而出飞上枝头。
想是夜间侍奉得宣帝龙颜大悦,今儿一早便下了圣旨,封她作了美人,赐居雅风阁。宫中传言纷纷,皆道她华玉娃是托了我的福,才一步登天。因为她献的歌舞,正是当年我得宣帝“歌倾天下”之赞的逍遥游》。
阿满向我道:“夫人,你说那华玉娃,故意亲近陛下,会不会是为了,为了司马大人?”
这还用问?该死的华玉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丫头,你把自个儿搭上去,是你家的事,可你要是沉不住气,坏了我的大计,我跟你没完!
恨得牙根痒痒,“阿满,立刻更衣,我们这就去雅风阁。”
雅风阁,皇帝新宠的居所,自是一派生机勃勃、万象之状。
只是它的主人,却像是摆上了神台的祭品,那面上的喜色,总也保持得吃力,在那初试云雨后的曼妙风情里,更藏了几分落寞。见到我,又将落寞拉长绷紧成了倔强和敌意。
懒得跟这种不知所谓、胡乱牺牲、又牺牲得毫无价值的女人多费口舌,我直奔主题。
“华玉娃,你最好给我闭紧嘴巴,你不要以为陛下宠着你,你就能左右陛下。我敢担保,你如果在他跟前为司马洛求半句情,他立刻就会把你打入冷宫。”
华玉娃居然死不悔改,“你少来吓唬我,陛下待我温柔得紧,他不会如此绝情。”
一头无名火起,恨不能扇她俩耳光,打醒这个只有脸蛋却没脑子的笨女人,“他若是知道,你是为了司马洛,才把自己献给他,我保证,他会比你能够想象到的更绝情。”
经过我,汉宣帝是再也禁不起这样的打击。他能饶过我,却肯定不能饶了华玉娃。
“华玉娃,既然陛下已经册封了你,你最好安分守己做你的美人。你要是不知惜福,执意要往那冷宫钻,我管不着,可你别害了司马洛。倘是你一意孤行,你会害得他永无翻身之日。你忍心么?你敢冒这样的风险么?”
把话说到这份上,想那华玉娃再没大脑,也不会轻举妄动了。预备拂袖而去,却叫华玉娃扯住了我的袖子,眼泪汪汪,六神无主。
“那我该怎么办?司马大人该怎么办?”
好一个深蹙蛾眉、泪湿愁靥的倾世佳人,我却只能为她徒叹扼腕。
“华玉娃,你若真想救司马洛出天牢,你就在这几天晚上,想办法,引陛下去太液池。”
今天两更结束,谢谢你果果。明天三更。
太液池位于未央宫西南。池中建有渐台高达二十多丈,另造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座仙山,精巧别致,烟雾缭乱,恍如仙境。
而我便在那秋末月夜之下,池中轻舟之上,抚琴,等待。
我奏的是那曲高山流水》,令伯牙子期相互引为知音的一支曲子,曾经萧屹最拿手最喜欢的一支曲子。我背对着岸边,盘膝而坐,身穿青色长袍,长发披肩,仅以绸带缚住,曾经萧屹最经常的装束。
身后,水声渐起,另一只小舟在向我靠近,不由心中一喜,却不让那喜悦影响我的心情,高山流水,讲求的是意境高远、空灵飘渺,倘若喜形于音,便落了俗套。
把自己想象成萧屹,指间便越发地流畅,那小舟已然停下,应是停在了距我几尺开外的之处,想那舟上定然有人立于船首,他在看我,听我弹琴,却不作声。
一曲既罢,我停手,片刻,如我预期,汉宣帝的声音响起,小心而迷惑。
“屹?”
自此,我那些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便没有白熬。
深深地吸一口气,成败在此一举。我从船中站起,缓缓地,转过身,面朝宣帝。
宣帝的震惊,理所当然。“是你?!”
随即的面沉如水,也是理所当然。不过,那水面,并不平静,是涟漪,是暗涌,端看我和司马洛的运气了。
我半身见礼,“廉子服,见过陛下。”
汉宣帝却侧过面庞,不再看我,那船头,只他一人站着,华玉娃早已不见踪影。
他负手朝那池子中央的长鲸石雕,深秋的夜风清寒,却清寒不过他的面色。那清寒,已非温言软语、低眸浅笑可以化解。所以,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忍不住开口。
但凡我笃定的,鲜少有失算的时候。
“想不到,不足一月,你的琴艺竟然进步如此神速,似乎这世上,就没有廉子服办不到的事情。”
他顺势把那清寒的眸光移向我,却不能用那清寒的眸光瞒过我,他在等我回答,我知道他并不在乎我答了些什么,他只是在借这等的瞬间看一看我,近距离地仔细地看一看我。
我知道,却不想知道,我倒是希望能被他瞒过。
“那陛下以为,子服的琴艺,比起萧大人,如何?”
那眸光乱了一乱,也不过刹那工夫,便风平浪静,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衣着、我的发式,清寒中透出了了然,了然里显出了讥刺。他还在恨我,原本快要平息下去的恨,因着今晚,死灰复燃。
“朕只当你当真修身养性了,却原来,你费尽心思,还是为了他。”
他看破了我的用意,不过我也没打算能够骗过他。他能够看破我,但有些事情他却是不能看破的。
“陛下错了,子服费尽心思,为的,不是他。”
宣帝在嘲讽,嘲讽我这低劣的谎话。“你不是为了他,又是为了谁?莫非是为了朕么?你在此寒夜守候,莫非是像其他后宫女子,来讨好取悦朕的么?”
我从来不会撒低劣的谎,便是撒谎,我也会让他明知是谎言,却戳穿不了我的谎言。
“子服在此守候陛下,为的不是他,也不是陛下,而是萧大人。”
把目光深入到他的眸光里,“子服是替萧大人,传一句话给陛下。”
宣帝在尽力稳定他的眸光,他不想被我说服,或者,他是不想被我打败。他把我看作敌对,却总是不能真正地把我看作敌对。
我陡然地收回了目光,逼得太紧,只会适得其反。我垂下头,不去瞧他的表情,“其实,这句话,算得上是萧大人的遗言了。陛下可知,萧屹萧大人,在临死时,对司马洛司马大人说了一句话。他说,”
不费吹灰之力,我便陷入了回忆,仿佛那日情景,又在眼前重现,那一幕也许早已铭心刻骨。
有意识地,再到下意识地,我真把自己当作了萧屹,萧屹说:“洛,别恨陛下。这不怪陛下,是屹愧对了陛下。洛,萧屹死后,陛下就只有你了,只有你了,洛”
抬眼,我又加了一句,“陛下,萧屹死后,陛下就只有司马洛了。陛下已然后悔了一次,难道还要来后悔这第二次么?”
今天三更。第二更中午上传
有时候觉得,我和宣帝之间,便像是一场战争,攻心之战。他想攻破我心里最软弱的地方,我也想攻破他心里最软弱的地方。只是,我们的目的,却有着天壤之别。
“朕从没想过要杀他。”
“陛下将他送到塞外,他迟早也是一死。与其熬死病死在异乡,倒不如给他个痛快,一刀杀了干净。”
“那你要朕如何?”
“陛下是天子,谁敢凌驾陛下的意志?自然是陛下要如何,便如何。”
“那你今夜来此作甚?”
“奏一支曲,带一句话。请陛下莫要忘了,曾经的患难相交,在陛下还不是陛下之时,那天地间的盟誓。”
“……”
“夜色已深,还请陛下早些回宫歇息,子服告退。”
我吩咐宫人撑船,汉宣帝陡然出声,叫住我。
“子服,朕可以不杀他,朕可以放他出天牢,朕可以将他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封,他依然是朕的宠臣,朕的知己,”话到此处突然转折,“但是,朕有个条件。”
……
天牢重地,戒备森严,走进去,打开一重重的铁门,浑浊的空气,阴暗的光线,司马洛便在那牢房里,席地而坐。
宣帝倒没有过份苛待他,将他单独关在了里间,与别的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隔离开来。很安静,不受打扰。
司马洛背对着门,听到我的脚步、狱卒开牢门,他都未曾动过一动。我几乎要以为,他已然坐化,坐化成仙。
“洛。”
快要坐化了的仙人蓦然惊醒,却不能立刻从长久的僵硬麻木中摆脱,他困难地移动着他的头,一点一点向后,终于,与我,目光交汇。
那一刻,他的目光让我心疼。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慌乱地起身,他张嘴,唇瓣做出了口型,却蓦然地停滞,发不出声,眼神开始悲哀,悲哀而无力。
我读出了他的唇形,我知道他要叫我什么,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停滞、眼神悲哀。
“洛”莫名其妙地哽咽了,却在把那哽咽拼命地遮掩,不让它显现在声音里,因为我要给他力量,我要尽我所能减少那悲哀。“洛,你有资格,唤我子服。”
有什么冲出了司马洛的眸子,那样的猝不及防,他也在拼命地遮掩,因为他不想让我变得和他一样悲哀。
偏过视线,好一会儿,才又转回到我的脸上,他已经准备好了笑容,他笑着唤我的名字。
“子服”
司马洛的笑,从来都是桃花嫣红,现在却像那花败的残枝映在水里的影子,那样地不真切,唯一真切的,是酸楚。
那面若冠玉的精致脸颊,如今只剩下了倨傲的颧骨,倨傲而孤独。至于曾经倨傲不羁的下巴,则满是拉杂的胡碴,拉杂得潦倒。绸缎的外袍沾着草屑,大块大块的污渍,晦暗了原本的光鲜。在他的脚边远处,我看到了他今天的午餐,一只肮脏的碗,一碗馊水样的汤饭。
这所有的所有,都让我坚定了决心,这里不是司马洛应该待的地方,我要把他弄出去,只要他出去,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
“子服,是来为我送行的么?”不管如何遮掩,仍是掩不住那伤感,虽然伤感,却满足。“能在离开长安之前,再见子服一面,陛下终是厚待了洛。”
厚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