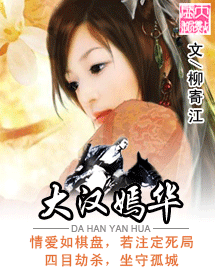大汉歌姬-第9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沅立时欢天喜地,满口应承着,喜滋滋地过来扶我,“阿满姐姐,我陪夫人就行了,你就别去了。天牢,总是个晦气地方,能不去,还是不去的好。”
阿满原本不肯,无奈我站在了小沅这边,小沅的话有道理,天牢,的确是个晦气之地,能不沾边,还是不沾边的好。
我和小沅登上马车,内侍关上车门,扬鞭喝斥,马蹄声声,踏着路面,拖着车轮轱辘轱辘向前滚动,平缓的节奏,颠簸,像幼时坐在母亲的摇篮中,困意袭上心头。
“夫人,你的脸色很差,是昨夜没睡好么?不若靠在奴婢身上,小睡片刻。”
刹那的恍惚,似曾相识的记忆。
苏云昭温和地拍拍我的手,“子服,累了么?来,靠着我,睡会儿吧。”
那一年,是本始元年,廉子服十五岁,苏云昭十八岁。
那一天,也是这么个早晨,我半倚着苏云昭,也是小睡了片刻,再睁开眼,已是宫内宫外两重天。
从那天起,我进了皇宫,也许便是从那天起,我就已经把自己断送。
身心俱疲地靠向小沅,她的肩,比苏云昭更加柔弱,那纤细的骨骼,几乎弱不经风,被我压得往旁边侧去,侧倚着车壁。
我该起身的,可自己实在太累了,便是动一根小手指,总也是心懒意倦。马车里,散发出一阵一阵清新好闻的香气,而我,便在这香气里,酣然入眠。
惊醒,缘自小沅的推搡,“夫人,夫人”
乍然的浑沌,惊惶之感更甚,“怎么?到了么?”
一问之后,惊色骤去,唯留惶然。
到了?到了哪里?如果当初,我能够先弄清楚我们要到哪里,然后再上马车,是不是,我和苏云昭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小沅口齿清晰地告诉我,这条不归路,我已经走得太久太久了,没有办法再回头,便是回头,也已经找不到来时的方向。
“回夫人,天牢已到,已有内侍进去禀报。”
“哦。”我应了一声,不是为了应小沅,而是为了听见自己声音,让自己暂时摆脱那惶然。
静静地坐在马车里,等着天牢的守卫来迎我。这是皇帝妃子应该享有的尊崇,虽然我并不享受这尊崇。
又过了一会儿,车外响起略显凌乱的脚步,由远而近,恭谨谦卑,“卑职拜见夫人。”
小沅打开车门,首先探身而出,下了马车,跟着向随后的我,伸出胳膊,我弯腰起身,蓦然间有些头重脚轻,继而浑身绵软。
好在,这突如其来的晕眩与无力,来得快,去得也快,随即便恢复正常,我只当坐车坐得麻了,并未放在心上。
正准备再次站起,这时,进去通禀的内侍向我道:“夫人,咱们似乎来迟了一步,霍氏一干案犯已然离开天牢,押赴刑场。”
我闻之愕然,来迟了?怎么可能?不是说午时才行刑吗?这么快③üww。сōm就押走了?
下意识地问:“他们走了多久?现在什么时辰了?”
那守卫答道:“回夫人,已然走了有些时候,此刻距离午时,尚有半个时辰。”
我又是一怔,还有半个时辰就中午了?不相信地抬头望天,天空是一片茫茫的白,尽管没有太阳,却仍是白得刺目。不由得眼珠子酸胀,耳边内侍在请示:“夫人,现下该去何处?是回宫,还是赶去法场?半个时辰,应当还来得及。”
立时有个声音抢着下决断:“自然是法场了,还不赶紧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脑忽然迟钝了许多,等我反应过来,小沅已经上了车,把我往里推,不住地催促那驾车的内侍,“快,快呀!若是错过行刑的时辰,我唯你是问!”
内侍连忙答应着,跳上前座,长声吆喝,猛抽缰绳,马儿撒开四蹄,载着我们疾驰而去。
车厢内,坐在我旁边的小沅,把个手紧紧地攥在胸前,神神叨叨念个不停:“老天保佑,千万不能错过了,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着那帮人,人头落地,我要亲眼看着他们不得好死!
小沅的整个人陷入到了某种莫名的可怕的亢奋里,她的脸,在白到刺目的天光底下,闪出更加刺目的光,刺目到令我不敢正视。
今天两更。第二更中午上传。另外关于结文,应该会到月底。
火急火燎,赶到法场,对于我来说,还是错过了,但是对于小沅,却是不早不晚,时辰刚刚好。
那场地内外满满的都是人,木栏外面,里三层外三层是看热闹的,木栏里面,跪了一排一排,一眼竟然数不过来的,那是给人看热闹的。
马车尚未停稳当,小沅便急不可耐地跳下来,甚至脚底一滑,差点摔个跟头,她却一点也不在乎,反而借着那滑的冲势,跌跌撞撞地向前跑。
“小沅!”突然的不安,我跟着下车,想去把她追回来。追到了她,却只是徒劳地被她带着朝那人群深处挤去。
小沅拼命地将挡在身前的人往两边拔拉,居然就被她拔拉出一条路,经过一番人肉挤压,我们两个终于挤到了人群最里,靠近法场的栅栏边。
凑到近前才发现,那跪着等待行刑的人,比远远地在马车上看到的,还要多了许多,清一色的白囚衣,那数量多到壮观,只是这壮观未免叫人胆寒。
我早就知道,汉宣帝是下旨灭了霍光九族的,但直到现在,我才对这“九族”有一个真正的具体的概念。
那该是数以百计,还是数以千计?怎么会牵连这么多人?怎么会牵连这么多人?
我看到了霍夫人,她蓬着发髻,不复当初光鲜,还有淳于衍,原本已养得丰腴的脸颊,又凹陷了下去。还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打过一两次照面的,全然陌生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到白发苍苍,少到未及弱冠。
他们每一个人的旁边,都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那应该是郐子手吧。郐子手站得笔直,臂间钢刀也是竖得笔直,笔直到一丝不苟,就像那一个模子里复制出来的。
那些跪着的人,有的便在郐子手笔直的钢刀下,哀泣着;没有哀泣的,那面上的表情,却是比哀泣更撕心揪肺。
如果没有像我这样如此零距离地接近死亡,那大面积的几乎会蔓延到天尽头的一触及发转瞬将至的死亡,你是无法体会我究竟被这撕心揪肺压抑到了什么程度。
“还好还好,总算还来得及。”小沅喃喃地庆幸,庆幸并且兴奋,跃跃欲试着,要是可能的话,她会毫不犹豫翻过栅栏,夺过那钢刀,亲自动手。
她的兴奋和雀跃,加重了我内心的压抑,呼吸困难,像离了水的鱼。
这时,有人向高居台上的监斩官低语,监斩官抬头看了看天,又点了点头,拈起筒中的一只令牌,掷下,语声不大,却可震裂人心。
“时辰到,行刑!”
那一丝不苟的仿佛样板的郐子手们,立刻动了起来,一手握住刀柄,一手拿掉插在死囚犯后脖颈那块斩立决的木牌,将那磨到锋利水亮的大刀,高高地,高高地,举起。
我下意识地想捂住眼睛,却在捂住眼睛之前,感觉到了一个人的目光。
是霍显,霍光的后妻,霍成君的母亲。她看见了我,盯住了我,那目光像是从沉尸万年、阴魂不散的骷髅的眼眶里投射出来,死死地死死地钉在我的脸上,那眼神已不是怨毒,人世间没有一种怨能够怨过它,没有一种毒能够毒过它。
然后,钢刀,斩下,那镌刻如此怨毒眼光的头脸,与身体脱离,掉在地上,一蹦两蹦,滚落尘土。同时,血,从断开的地方,从脖子里,从兀自直立跪着的身体中,如喷泉,溅出。
今天两更结束。
知道什么叫做屠杀吗?知道什么叫做血流成河吗?
那就是,几百柄、几千柄铁环钢刀一齐砍下;那就是几百颗、几千颗头颅,先后与身体分开,掉在地上,蹦跳着。成百上千颗,不同的面孔,死也不能闭眼的恐惧怨毒凝固的,错乱地,没有秩序地,在落地的瞬间,蹦起。
人的脑袋,毕竟不是那皮球,软的皮肉包裹硬的头骨,没什么弹性,只蹦了一下半下,便骨碌骨碌滚了开去。那不见了脑袋的身躯,前后晃了晃,晃了晃,像个装满了沙土的麻袋,歪歪斜斜地仆倒在地。
也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霍光的儿子昔日的大司马霍禹,整个霍氏谋反案的罪首元凶,宣帝判他的,是腰斩之刑。所以,他,断成了两截,在腰的位置,白花花的肠子,哗啦啦地,从他的肚子里往外流,跟着泉涌的鲜血。
是的,那刀砍的断口,血,汩汩地流出,千百个无头的尸身,一起流着血,流出来的血,从高处往低处汇集,汇成小溪,千百条小溪蜿蜒着,向前延伸,壮大成河,河的面积还在不断扩大,最后整个广场上一片汪洋,红色的汪洋,汪洋一般的血浆。
那些无主的人头,便在这血海当中,飘飘悠悠地浮了起来,略略地动着,像是突然又活过来一样。恐怖和诡异随着那浓郁到浓冽的血腥味,在血海上空,漫延开来。漫延得如此之快,几乎是一下子便冲进了我的鼻腔,然后又一下子从鼻腔冲进胃里,搅着空的胃,搅出一阵一阵的干呕。
就在那无数人头砍落的同时,就在我觉得恐怖、诡异到干呕不止的同时,我身边的人,小沅,以及小沅身边的,那些普通的百姓们,他们,便像是引爆了兴奋点一样,鸡蛋、烂菜叶子,越过栅栏,满天地扔过去,于是血腥味里又加入了各种腐烂的气味,熏得人的神智不清了,彻底不可理喻了。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之间,死了这么多人,死得这样惨烈可怕,他们怎么还能高兴得起来,而且高兴到了疯狂,简直失了人的常性。
失了常性的人们,无意识地大声地叫着好,叫得扯出脖颈一条条的青筋,一个个,那眼睛,如同嗜血的恶狼,舔着嘴唇,急不可待地要分食那些死尸。在那嗜血的深处,是仇恨,比屠杀和血流成河更加恐怖、诡异的仇恨。
这些恶狼里,也包括了小沅,那秀美清丽的面容,竟也显出了恶狼一般的凶残,狂热的凶残。
她跟在人群里叫嚣:“好!杀得好!杀得好!”
他们的叫声充斥着我的耳朵,正如那血海、人头充斥着我的眼睛,血腥腐败充斥着我的嗅觉,这些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拉扯撞击我的神经,要把它扯断、撞碎,在我的脑子里,像过山车一样呼啸着,极速而来,冲到这一边,碰壁,再回头,极速而去,找不到出口,只能不停地辗转反复,不停冲击着我那心理承受的极限。
监斩官离去,郐子手退下,没有人去管这些尸体,因为汉宣帝的旨意是“斩,弃于市”。
隔离百姓的栅栏,被撤去了,那狂热人群,便从四面八方,涌向法场中心。
接下来的,这一幕,已经不能用血腥、诡异、恐怖来形容了,血腥、诡异、恐怖都过于静态了,描述不出眼前那几近人间地狱的癫狂。
那些死了的,不是鬼,这些活着的,才是真正的恶鬼,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间恶鬼,他们涌过去,践踏着、唾弃着那些无头尸身,那沾着污泥的鞋底,在血浆里踩来踩去,血溅起多高,溅湿了他们的裤脚。
他们在那一个个满是血污的人头里,寻找着他们的仇人,找到了,或者把那头,忿忿地踢出去老远。
或者,就像我看到的小沅那样,小沅把右脚抬起,那只套在木屐里的雪白素足,抬得老高,朝地下霍显的人头踩下去,重重地,霍显的那张脸,美丽的风韵犹存的脸,在临死时留下怨毒一瞥的脸,眼看就要被踩在小沅的木屐之下。
我没敢再往下看,我想我一定是在发抖,抖得连调头,都好像能把脖子扭断了一样。我不知道,我的视线,该朝哪个方向,左边,右边,前边,都是血,都是踢来踢去的人头,踩扁了的人脸,没了头的死尸,横七竖八。
往后退,我只能往后退,我要退回马车上去,我要把车门关得牢牢的,我要把这些疯狂都关在外面,关我的眼睛外面,我要好好地睡一觉,我要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疯了,他们都疯了,可我没疯,我没疯!
脚边,似碰到了什么阻碍,绊住了,来不及收脚,脚底软软绵绵的滞涩,低下头,差一点呕出了心肝脾胃,原来我踏到了一具无头男尸的胳膊。
紧紧地闭住嘴巴,生怕闭不住,拿双手用力地捂,没关系,没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脚下混乱着,越乱越错,我又踩到了一样物事,这次踏出的力道很大,我,我,我也像小沅似的,踩到了一颗人头,正中他的面庞五官。我不该再低头去看,可那只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条件反射地垂下眼帘,看见,我的右脚下,便像是踩烂了一只柿子似的,有一滩稀泥,血水肉泥,而我的脚面,拇指与食指的中间,沾了一颗,黑黑的小小的圆圆的东西,竟是,竟是,从那踩爆了的眼眶里,蹦出来的,那人的,眼珠子。
这章太血腥了,汗,如果倒了亲的胃口,我在这里说抱歉,我只是想突出那种气氛,以及女主受到的那种刺激,可能写过了。
后来,我不太记得,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尖叫,跳脚,像那疯病发作的精神患者。
没错,我也疯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疯了。可是,为什么,我疯得这样清醒,我清醒得记得每一个细节,那每一个足以让我疯狂一千次一万次的细节。那每一个小细节,互相联系着,在我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重演。
就算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那密闭的车厢里,就算马车远远地驶离了那个人间地狱,就算我回到了未央宫,阿满还有其他的宫女们在那常宁殿外迎接着我,她们每个人,都是红润的面颊,如花儿般鲜艳娇嫩,但是我看不到那鲜艳娇丽,我闻不到她们脂粉香气,我感觉不到活人的气息。
只有血,肮脏得混着大片尘土的血,满满的腐败气味的血腥,除了死亡,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疯狂。
推开所有人,挡在我面前所有的人,那些无法传递到我的世界的鲜艳美好,那统统蒙上了血腥气味的人和物,我要把他们推开,我要把他们阻隔在我的视线之外!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你开开门呀,夫人,夫人”
一大堆惶急的女声,交叠着在那门的外面,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