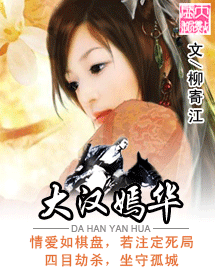大汉歌姬-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司马洛面色为之一僵,我戳到了他的痛处。好像我每次都能快、狠、准地命中司马洛的死**。
气氛随之凝重,我又开始后悔。好像我每次戳到司马洛痛处令他难堪之后,我都会后悔。
想着寻个什么话题,改善目前这气氛。陡然记起司马洛刚才那句话里,一个被我忽略了的地方。他说我“跳”入池中,而不是用跌,或者其他代表意外的动词。
不可思议地瞪着他,“你,你怎知我并非失足落水?”
司马洛倒是大度,或者他不想再与我起争执,或者单单只是我过份吃惊的样子极之搞笑,愉悦了他的心情。
总之他一改先前不快之色,语带揶揄地道:“姑娘怎么忘了?姑娘堕入水中之时,司马洛便在附近。还是我及时下水把姑娘你救了上来。”
我不由呆了一呆,几个月来拼命想忘记的那个画面,再一次浮上心头。
偏巧目光无巧不巧,又刚好落在司马洛的身上。以他的个头和我的个头,视线正对着司马洛的胸【炫~书~网】膛处,我在水下一度依偎过和眷恋过的地方
赶紧撇过眼去,浑身上下地不自在。
可能是我的不自在提醒了司马洛,令他也回想起了,此刻我脑子里的那一场景,便跟着不自在起来。
气氛由凝重转为尴尬。
我出声打破尴尬。
“奴婢还未谢过司马大人救命之恩。”
司马洛配合我的粉饰太平,刻意回避我想躲开的东西。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然后,巧舌如我,居然没词再接下去。而善言如司马洛,亦不知所措地沉默了。
依旧陷入尴尬,想躲开的,想回避的,仍是躲不开,避不了。
我低头看地,司马洛仰脸望天。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他低声吟了一句诗:“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我一惊,抬眼却见他望着那圆月,若有所感。不jintuo口而出:“那wan真的是你!”话一出口,便觉不对,我居然没对他用尊称。
司马洛不知是未曾注意,抑或是并不介意,他转而看我,却答非所问。
“比起别离歌》,我更喜欢子服的这支曲子。别离》虽凄婉缠mian,只是歌者却别有用心,不若此曲纯粹,似有超tuo世俗之仙韵。”
听起来像夸奖,但我却从他的夸奖中品出了一些别的什么,类似于不认同。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解释我的别有用心。“司马大人可知奴婢为何会去宣室为陛下唱那支别离歌?”
“……”
“只因陛下因李美人之死无心朝政,太皇太后终日担忧,曾言道但凡有人可开解陛下,必有重赏。奴婢献歌,为的不是陛下,而是太皇太后的赏赐。”
“赏赐?”司马洛一愣,继而满脸兴味地问道,“但不知子服想要的是何赏赐?竟比得到陛下的宠xing更为重要。”
“这个赏赐,是司马大人绝想不到的。”我故作神秘地一笑,揭晓谜底。
“太皇太后答应奴婢,只要奴婢劝得陛下临朝,便准奴婢离宫。”
司马洛面上陡然一震,大是诧异,诧异之后却是(炫)恍(书)然(网)大悟,由衷的佩服,带着些许难以置信。
“我早知子服不似贪慕虚荣之人,不想你却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你竟然以得到陛下赏识,作为出宫的条件?”说到此处,他忽地大笑出声,“原来天底下当真还有女子,视陛下如毒虫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见到他笑,见到他佩服我,心中所有的郁结登时一扫而空,像孩子得着赞赏似的雀跃并得意着。
雀跃完了得意完了,又暗自奇怪,见了鬼了,他司马洛是讨厌我也好,佩服我也罢,关我P事?我干嘛要浪费口水跟他解释,我干嘛要让他的情绪左右我的情绪?
郁闷!
司马洛倒是很开心,促狭地道:“子服,若是我将你宁可一直病着也不肯去未央宫的事告诉陛下,你说陛下会作何反应?陛下可是从未在女人身上吃过瘪。”
这一声“子服”是司马洛叫我叫得最亲切的一次,感觉像个老朋友似的。
我不慌不忙答道:“司马大人一定要如此么?莫要忘了,大人你也是共谋,你可是亲眼见我跳入池中,亲眼见我倒掉太医署开的药。届时,子服获罪,太人也逃不掉这纵容包庇之责。”
司马洛越发忍俊不jin,“子服,现在想起那两次你偷偷倒药的鬼祟模样,实在是有趣之极。”
我一愣,“两次?这么说来,前番在后院真的也是大人你了?怎会如此凑巧?连着两回都被你撞见?”
司马洛忽地收敛笑容,“其实——”
他拖长了音调,似难于启齿,面上现出些许忸怩,却极力掩饰那忸怩之色,剑眉蹙起,又松开,像为着自己不应该有的忸怩而好笑笑未笑,极快地看了我一眼。
“其实,说巧也不算巧。前回,我是寻了个由头,专程来看子服,只听说你久病不起,故而带了些专治风寒的草药。”
我不由心中一甜,似笑非笑,“想不到大人竟如此关心子服,倒叫奴婢有些受宠若惊了。”
司马洛立刻补充,“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云昭身边的人,凭我与云昭的交情,云昭不在了,我有责任代她对你多加照顾。”
听到云昭这两个字,忽然间心凉了,仿佛苏云昭正睁着她那双美丽而忧郁的眼睛哀怨地看着我,甜mi开始变得罪恶。
我不该的,苏云昭待我那般的好,我不该夺她的心上之人。
更何况,拥有倾城之貌、色艺双绝的苏云昭都没能拢住司马洛的心,我又如何、又凭什么做到苏云昭都没能做到事?
也许事实上有一大半正如司马洛所说,他不过因着愧疚,想弥补在我的身上,借此减轻对苏云昭的负罪感。
而我却还在沾沾自喜,像个多情幼稚的傻瓜,一个三十岁还玩暗恋游戏的大傻瓜。呸!
最近计划在改名,因为需要寄改名申明,所以还要迟几天,新的书名是大汉歌姬》,先报备一下。呵呵
正文 31。 (三十)不欢而散 字数:4293
耳边司马洛接着前句说道:“不想我送药未成,却撞见子服一个人抱着个罐子,出了屋子。我心里奇怪,便跟在后头。起先我并不知道,那里面便是你一直没喝的药。后来你失手摔了那瓦罐不慎划破了手掌,我本想现身,但是见你那般惊恐,我怕突然走出来会吓到你。后来你走了以后,我过去瞧了瞧,闻到了一股子药味,心里便有些明白了。”
我忽地想到一个可能,“莫非那些碎瓦瓷是大人你收拾的?”
司马洛点点头,“我想后院虽偏僻,但总有宫人打扫,瞧见这一片狼籍,总是不妥。”
“那后来呢?后来为何大人会无缘无故,深夜去了外面的林子?”
“说起来,倒真有些机缘巧合。那天傍晚回去以后,我前思后想,想你病体羸弱却不喝药的原因。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理由。其时,陛下便已不大再提起你,我总想找个机会告诉你,让你安心养病。刚好那日太皇太后寿辰,陛下为太后贺寿,于长乐宫中夜宴群臣。我中途借故离开,候在侧门处。其实也不过碰碰运气,并不期待子服会出现。想不到会真的等到了子服。”
说到这里,司马洛回头深深地望着我,“更想不到我会听到那样一支超凡tuo俗清雅别致的曲子。当真是起歌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用我的歌改个一字来赞美我,这司马洛连奉承人,都是这么地风雅自然、这么地不着痕迹。
我转过脸,不去接触他的目光,坚决不做傻瓜!
“大人你是听了一曲好歌,却把奴婢吓了个魂不附体。”
司马洛笑了起来,“这并非我本意,我在后面叫过子服的名字,只是你心慌意乱未曾听见罢了。”
我冷哼一声,意示不满。
好了,什么疑团都解开了,是时候拍拍pi股走人。省得待久了,我又犯傻。
“大人的连番好意,奴婢心领了。他日若有机会,定思回报。奴婢不宜耽搁太久,天色已晚,大人也该是时候出宫去了。奴婢就此别过大人。”
“子服——”
我站住脚,等着司马洛的下文,不诚想那位却还没想好他的下文。
“嗯——”犹豫片刻,他问,“但不知子服唱的那支曲子叫什么名字?”
我想了想,照实回答:“此歌叫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何意?”
我哪晓得水调歌头什么意思,只知道那是一个词牌名。反正北宋的事他,一个汉朝人也不会懂,索性外行蒙外行,“只是一个曲调名而已,为我家姑娘自创。”
这是今天第二次提起苏云昭,才让我记起了那件搁在心头很久的事,想来实在惭愧。
“请问大人,将我家姑娘葬在了何处?”
司马洛变得有些伤感,“我将云昭安葬在了长安城外,一处山青水秀之地,她生前最喜欢那里的风景。”
“司马大人带走姑娘尸身,难道那些内侍没向陛下禀报么?陛下有否怪罪大人?”
“陛下?”司马洛嘲弄地重复,面容讥诮,“陛下根本不知云昭已死。他根本忘了云昭的存在,内侍又怎会没事找事,去向他禀报?”
我问:“陛下心中没了姑娘,那司马大人呢?大人心中可还有姑娘的影子?”
司马大人骤然一惊,愣愣地看着我,“你为何这样问我?”
我不该问的,心中不是滋味,“是奴婢问得唐突,大人恕罪,奴婢告退。”
“子服——”
有完没完,敢情不让我走了是不是?我又止步,这回不用我等,司马洛已然准备好了他的下文。
“子服以后,不必在我面前自称奴婢。我并未将子服看作奴婢,子服日后,若有任何难处,只管来找我,司马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抬起脸斜眼看他,“大人如此看得起子服,是否也是瞧在苏姑娘的面上?”
司马洛不答,一迳拿他那勾魂眼,混乱我的思绪。
我眼观鼻,鼻观心,淡然道:“大人若想帮子服,便寻个事由,教训一下掖庭丞丁准,也算是为苏姑娘报了仇。要不是他,姑娘也不至于有病难医,拖成不治之症。”
“丁准?”司马洛不屑,继而恼恨,“那个小人,早晚我会惩治他。”
走了几步,我第三次停了下来,却不是司马洛第三次叫我,而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真有件私事,可能他司马洛能够帮得上忙。
刚才谱摆得太过了,这会子还真不容易放低姿态去求人,“呃,司马大人,说到难处,子服倒真有一事相求。”
司马洛洒然一笑,“我说过无论子服有何事相求,司马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切,讲得这般豪迈做什么?我才不会感动,感动得做回傻瓜。
“倒不需大人如此,只是一件小事。大人可认得,廷尉衙门里有一名叫做廉昌人的小吏?”
“廉昌人?”司马洛稍作沉吟,“似乎是有这么一个人。莫非他是子服的——”
聪明,单从同姓便猜出和我的关系。“不错,此人是子服的父亲,子服求大人的,便是请大人去一趟廉府,将我母亲接出府来,另寻一处宅院安置。”
司马洛立时骇然变色,仿佛我提出的,是个荒诞绝伦并且大逆不道的要求。
我再往深里一想,好像确实有点悖逆人伦的。我汉朝的娘是个有夫之妇,而我居然要求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把她带离夫家,这不是变相地教唆他you拐良家妇女吗?
得,条条大路通罗马,要想让我汉朝的娘过得舒心,也不只这一个方法。
“或者,大人可以令我父亲休掉他那两位如夫人,叫他善待我娘,永不纳妾。”
司马洛似有些明了,笑得无奈,丫的这小子好像很喜欢笑,仗着自己笑起来好看就乱放电么?
“子服未免高估了我的能耐,他人闺房之事,连陛下都管不了,我又如何插手干预?”
我拿他的话堵他,“司马大人不是说愿为子服赴汤蹈火,君子一诺千金,难道此事会难过赴汤蹈火么?”
司马洛没话回我,举白旗投降,“好吧,我尽力而为。”跟着又大发感慨,“云昭那般温和,怎会收了你这样一个古里古怪的丫头,净做些古里古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不喜欢他将我和苏云昭相提并论,这让我有自卑感。
“只不过,”司马洛忽地心情大好,目露算计之色,“我要是为子服办成了此事,子服该如何报答我?”
“谢?”我怔住,“大人不是说愿为子服赴汤蹈火么?如此还要报答?”
“那是当然,我只说赴汤蹈火,却没说是无条件的赴汤蹈火。”
长安第一辩才到底不是浪得虚名,我败下阵来,“大人要子服如何报答?”
“我要你在花前月下、风柔星灿之夜——再为我唱一次水调歌头。”
这家伙存心的,存心中间停了一大气,害我一时不察想歪了,还以为他要在什么花前什么月下什么什么我。
到了这一刻,我和司马洛这个黄昏之约,还算是愉快。尽管中间发生了一些不和谐,总算经过努力和磨合,再加上一点点老天的机缘,最终没演变成上次的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本来,我应该及时闪人,这样,我和司马洛下次见面还可以开开心心的,如老友重逢。
司马洛这种人,做【炫】情【书】人【网】不行,没安全感,做朋友却还是个上上之选。
可我却偏偏又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说了句不该说的话。
这个问题入宫以后我还常常拿出来琢磨,百思不得其解,总是不了了之。那就是——司马洛当日明明对苏云昭有情,却拒绝苏云昭的理由。
犹豫了很久,最后,我还是问了出来。我想如果人死了有鬼魂,那么苏云昭的鬼魂应该也很想知道那个答案。
便和先前我问他,心中有否还有苏云昭的影子一般,司马洛的表情错综复杂,甚至想四两拨千斤,糊弄我。
“那日,子服在门外,不是听得一清二楚么?为何还来问我?”
呃?倒打一靶,怪我偷听?没事,能打的强不过能说的,能说的强不过脸皮厚的。
我索性干干脆脆承认,“那日,子服确实在门外听见大人和苏姑娘的谈话,但是子服不以为那是大人真心之语。”
司马洛居然摇头否认,他居然认认真真地告诉我:“不,子服错了,那确实是我的真心之语。司马洛浪dang之人,从来只会令身边女子伤心落泪、郁郁而终,云昭若跟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