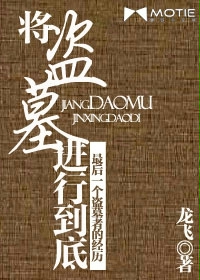噩梦婚姻进行曲-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识他怎样都不会相信我。果然,菲德马上嘲讽到:“那你是哪样的人?”
我一时无语,陷入到百口难辩的困境。我也想跟他吼:“我什么错事也没做过!”可说啥都没人信的时候,倒不如省省力气,什么也别说。
“妈的,你可真狠——你怎么能这么狠!”他咬牙切齿地说着,手上的动作更粗暴起来,揪着我衣服使劲着又摇又晃,几乎把我拆散了架。“你疯了啊!”我又疑又惧,却无法令发狂的菲德歇手。他把我胳膊一拧,就轻易地把我反剪过去,紧接着,结实的身体自背后覆上,死死搂住了我。
强硬地在我两侧的耳后、颈边上上下下、啃噬样地反复亲吻,手指在前面一一解开衬衣纽扣,慢慢探进手去,在胸前来回地揉搓玩弄。
额头抵在围墙粗糙的沙砾墙面上,我屈辱地粗声喘息。菲德半褪了我上衣,在我赤裸的肩膀上狠狠的、发泄般一口口毒辣地咬下,我痛得几乎惨叫出声,身体忍不住阵阵地发抖,却每每倔强地咬着牙默默承受。而当他扳了我下巴索吻时,我还尝到他嘴里浓重的铁锈味。
为了我,跟最铁的哥们反目成仇,并且对我背叛他的事深信不疑,他一定恨透了我吧……模糊地这么想着,菲德却突然趴我肩头上一动不动,觉出他贴在我脖颈的脸庞一片潮湿,刹那间,我心上象被人狠狠捅了刀似的,痛得抽搐不已。
“对不起,我太失态了。”菲德将我轻轻推开了。接着,他转身离开,径直向操场出口走去。
看着那无比孤寂的背影,在冷冷的路灯下,拖着越来越长、越来越模糊的影子,离我越行越远,我有种想哭的伤感……有一种从心底深处涌上的液体,有一种迅速泛滥开来的隐痛泛出海洋的咸味,它有着海洋冰冷的温度和冰冷的蓝色,正在慢慢淹没我的五官。
那节课是物理,复习基本概念,讲解基本题型。
我根本没打算听讲,所以一直心不在焉在嚼口香糖,手指上则转着杆圆珠笔。
“啪”,一粉笔头重重砸我桌上。收回飘至外太空的思绪,我一抬眼,正撞上物理老头气愤得快要发抖的面孔。“这是要中考的学生该有的学习态度吗,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
搁以前,老头早把我轰外头凉快了,今儿却不知犯了哪门子邪,唠唠叨叨的,历数起我这三年来的劣迹斑斑来。我忍不住失笑,背往后面桌子上一靠,拿出懒洋洋的劲头来,还忒没礼貌地打断他:“老师您要不痛快尽可让我出去,我决无二话。您这没完没了的,哪儿是个年头?该不是您老的更年期还没结束吧!”
下面爆发出一阵恶意的轰笑声,接着被黑板擦拍在讲台上的震天巨响嘎然打住了。物理老头怒气冲冲地过来,我赶紧配合他自觉地起立,然后脸上,先左后右,各挨一记大课本。
摆出无所谓态度,我向上吹口气,拂动眼睛上方长且细碎的刘海,还冲物理老头笑笑:“对不起了老师,看把您给气的。”
“出去,操场上跑六圈!”物理老头仍不解恨,指着门外头跟我怒吼。
等我跑完,呼哧呼哧地回到教室门口喊报告,浑身上下的衣服都已经塌透了。物理老头眼皮没撩一下,只从鼻孔里冷哼声,说:“你外头等下课吧!”
过了十分钟的样子,下课铃声终于欢快地响起……
老师前脚走,林如后脚跑我跟前。他对我端详了又端详,揣测了又揣测的,最后讽刺到:“大侠你厉害,吃啥药了这么动物凶猛,看把老师气的,快犯高血压了。”
我没说话,我也知道自己太过分,可覆水难收,我总不能驾着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吧,所以,只好默默忏悔了。
课间,从班主任的办公室挨过“批斗”出来,经过高中部教学楼时,看见了菲德。
穿着白衬衣的他,卷着半截袖子,正散漫地站在几个男生中间,表情严肃,还透着股凶狠劲。我一怔,停住了脚步。同时,他也看见了我,就冷漠地一扭头,装没看见。
有些事发生了,无论对与错,都注定了我跟他回不到从前。心上的伤痕是无法修补的,若是漠视那裂缝的存在,任凭岁月来淡化伤痛,填补那隔阂留下的空白,是否就能顺利地继续下去……
第30节
我痛恨,我痛恨这种“死”得不明不白的窝囊感觉。
而那阵子,马上就高考的头两个星期,菲德又拉了人在千佛山后面跟外校的一帮混混干架。我没亲眼看见,据席侃形容:当时打得相当惨烈,甚至有黑社会的参与了斗殴,还动了家伙械斗,直可用刀光棍影、血流成河来形容。最后,有人被砍断了脚筋,还有人挨了刀子,就连菲德也未能全身以退,挂了重彩。还有,李冰替菲德挡了一闷棍,当时脑袋就开了铺,血流满面,送到医院一检查:轻微脑震荡外加视力受损。
一听说菲德挂了重彩,我这脑子里“轰”的声,被炸得满地创痍,立刻跑去菲德教室,却被告之他请了长期病假,高考前都不会来了。又跑到他租住的房子,大门紧闭,墙上还糊了张房东新张出的租屋广告。
结果,直到高一开学,我也没见过菲德一面。他象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无处觅寻他的踪迹。深夜,我常蜷缩在床铺的一角偷偷流泪。青春流逝,我觉得心在一天天死去,梦的光辉渐渐熄灭……思想如条漆黑的河,在身体四周缓缓流淌,河面上漂满了揉碎的浮萍,而两岸就是青草漫溯、莺歌燕舞,却与我无关。
开学不久是情人节。那天放学,在校门口,我竟看见了众多花痴中,手捧大束红玫瑰的陈非。
听说,陈非如愿地考上体育学院,而菲德和李冰都考上了本市的重点大学。而最风光的,就要属考上艺术学院的邵兵,他一进校就被有钱有势的公子哥给包了,每天豪车接送,要多气派有多气派。
和我一照面,陈非就阳光灿烂地笑了。他快速穿过人群,潇洒地站在我面前。立刻,我就被那浓烈的花香熏得皱起了眉头。
“情人节快乐!”他向我递过花束,“三十三朵玫瑰,代表三生三世的爱。”
我退后一步,冷漠地转过了头。眼波流转之间,满街头都是红艳艳的玫瑰、毛茸茸的可爱玩具,可心却拒绝感受这浪漫和温馨。
“你来做什么。”我生硬地咬着那几个字。说老实话,无论是菲德、李冰、邵兵,还或者是他,我都不想见到,他们皆是我不愿碰触的过去,有着我伤感的阴影。
“我喜欢你,也从没放弃过你。”陈非用着认真的口吻说,“朝歌,既然你跟菲德散了,就跟我重新开始吧!我一定会对你加倍的爱护,真的,我发誓!”
用新的恋情替代旧的恋情吗?可惜,我不需要。我需要的仅仅是时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它可以让爱的变成恨,热的变成冷,美的变成丑,真的变成假,而恨的变成冷淡和决绝。
“我不喜欢你,这辈子也不会喜欢你!你死心吧!”我说着跨上自行车,骑进熙攘人流中。无缘无故的,嘴角却挑起了一弯弧度,是嘲笑着自己,还是痴心妄想的陈非,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不再是以前的朝歌,过去与我一刀两切。
真做到一刀两切了吗?不,没有。
高一那年的寒假,钟离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见我。听他那口气简直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我隐隐觉得肯定有大事发生,就痛快地答应了。
地点选在学校旁边的护城河公园。没想到,才上初三的钟离一开口,竟告诉我他怀孕了。我当时就毛了,不可置信地瞪着他,又惊又疑,最后颓然地一屁股坐在花坛沿儿上。
“是哪个混蛋干的,我他妈废了他!”压抑着胸中涌动的怒火,我低声道。
钟离刚开始不说话,只站在我跟前默默地哭,任由着大颗大颗的泪水“啪嗒啪嗒”往下落。我又问他几遍,他才告诉我,那人是李冰。
“操,你怎么还和那家伙有联系!?”我火了,李冰是大学生,你一初中生,你跟他玩,玩不死你!
“我不是暗恋李哥吗,就经常打电话给他,可他根本不怎么搭理我。情人节那天,李哥喝大了,他醉醺醺地跑到校门口,蹲在树底下发酒疯,正好给我碰到。我问他,他说他要等你出来。我就跟他说你考到别的学校去了,他听了好久都没说一句话,还哭得忒伤心。再后来,我把他送回宿舍……”
顿在那儿,钟离露出痛苦的神色。过好半天,他才稳住情绪,喃喃说道:“宿舍里没人,都出去过情人节去了。他那样子太不让人放心,我就没舍得走,他错把我当成了你时,我也没拒绝。完事,他酒醒了,看见是我马上火了,还让我滚出去……”
“师哥,你不知道,最近这段日子我吐得忒厉害,就硬着头皮买了试纸……结果……”
象给块石头生生地噎住,我啥也说不出。
“师哥,我该怎么办啊?”钟离眼里闪着泪光,无助地问我。我瞧出他意思来了,操,这倒霉事你想起师哥我来了,可我要是见死不救是不是就太没人性了!
“李冰知道这事不?”
“他知道。”
“知道?!”我倒惊讶得差点合不拢嘴了——知道你不找他,你找我,是个啥意思哩!
“他说他很忙,他不管,他还说我讹他来着——因为那天我由着他信我就是师哥你,他觉得自己受骗了。”
既然后悔就别做酒后乱性的事啊!?始乱终弃,与畜生又有何异……我冷冷地笑笑,心里却慢慢打定下主意。然后,我就大力拍着钟离的肩膀安慰他:“你放心,这事师哥我管定了!”
ps: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现在病好多了。下面写的这两章也不知道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不。其实,我写第3部的本意,就不想让这一对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在时间长河里不能化解的误会和遗憾,只那么一层纸,只要他们有人肯主动前进一步,幸福就可以唾手可得,可这两人偏偏都是硬脾气。
第31节
怎样帮钟离,我仔细想过:第一步骤就是立刻、马上去做人流,越晚越是不妙……
杵在玻璃窗上印着“安全无痛人流”文字的门诊外,钟离脸色惨白着,说什么也不敢踏进一步。而我,情形绝比他好不到哪儿去——腿肚子直发抖,上下牙都想打架来着。要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拼命装镇静,这会儿瘫在门口的先是我也保不齐。
“你知道后果的!现在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虚张声势着吓唬钟离,我的手心里,满满的却都是冷汗。
“我还不如死了的好!”到最后,钟离竟恐惧得撒腿开跑。速度之快,兔子都比不过他。“死小子!”
傻傻地望着他绝去的身影,我独站在那条小街的当中,彻底毛爪——没辄了。
舅舅家的表姐读大二,是医学院的本科生。前几天,她打电话跟高三学生的老姐说:他们系忙着搬家,入党积极分子们每晚上都扛个人腿什么的在教学楼间走来走去的;她还说做解剖还是瘦子好,胖子人油太多,每回都得拿把勺子往外舀,完事洗手忒费劲,打几遍肥皂也去不了那油腻劲;另外,胳肢死人,死人也会咧嘴笑来着;最后了,她还问老姐要看解剖时拍的照片不。结果,老姐被吓得吱吱叫,晚上睡觉非跟老妈挤一床不可。
怪不得都说学医的变态,这么恶心恐怖的事,他们竟拿着当有趣哩……
我很想抢过电话问表姐咋个流产法,可我真就开不了口。
晚上十一点,坐书桌旁写作业的我正想着:要不要通过老姐咨询一下表姐……说曹操曹操就到——老姐抱着被子、枕头,闪身窜进了我卧室。
“妈照顾姥姥去了,晚上咱姐俩挤挤。”老姐大言不惭地说着爬上我床,把我的寝具一股脑丢在木地板上。我皱皱眉头,斜视她一眼,她也无所谓,摸起我床上随身听的耳塞戴上,闭目养神地听起音乐来。
做了长久的思想斗争,腹稿也酝酿、修改了好几遍,我终于鼓足勇气,厚起脸皮——“姐。”
老姐闭着眼点点头:“嗯哼。”
“问你个事儿。”
“啥事,说!”老姐痛快地揪掉只耳塞,这是打算洗耳恭听了。
“流产……”
我这才刚说俩字,老姐便花容失色,惊诧地瞪圆了眼睛。她也不分个青红皂白,不管个前因后果的,对着我就是一通猛烈“轰炸”:“朝歌,你死了你死了,你彻底死了!怀孕是好玩的啊,你那个男朋友菲德咋这不小心呢!做那事时要戴套子可是再常识不过的常识了!笨,真笨,笨死了!猪都比你俩聪明!”
闻听此言,我不由得瞠目结舌:靠,难道我高一就怀孕还流产的事就这么来的——这也太他妈荒诞了!眨眨眼,我忒想解释来着,可转念一想——怎么着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何必再找个垫背的,就硬把话咽了回去。
“吃药吧,我听一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