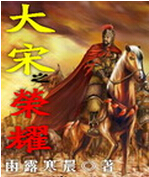你的万丈荣耀-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我抱紧他的时候我的生命缺了那一块的地方终于有被填满的趋势,即使是一种趋势,也足够让我满足到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忍不住感叹。
和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以往走过的路都变成全新的路径。我这么酸溜溜的说法的意思是,我和他在一起,能让我变得不像是以前的吴燃。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早就有这种忍不住的趋势,但在他和吴尘科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我这种微不可见的改动真的不值一提。我在他们随时可以漏出来的幸福里挣扎,忘了世间所有的变化。
其实我吴燃的世界真小,又有搞笑人生这必不可少这一因素。
就过去有过的经验,美国的街道每个区都有几分差异。但在今天脚下踩着的街道差异大到竟然让我在握着肖天铭的手的时候想到了现在相安无事的苏浙。
我和他终于算是认真的分了次手,就是在我到他家——那栋房子还是他的,在那之后,我看着他喝完一杯完整的牛奶,我收起我心脏里有些轻微的动摇,在这细小的缝隙造成更大影响之前我坚定的语气很平淡的和他聊起最近的近况。
在我们之间大有更趋祥和的趋势之前,我对他装作不经意的一提,“天铭上个月刚到美国。”
其实在外我对任何人都没这么叫过肖天铭,我总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要大张旗鼓的宣扬出去,那其实没什么意思。要让我和当年的吴尘科那样和肖天铭在聚会的时候用各种纠缠到暧昧人眼的面部表情来表演些什么,就没有在一起最初的意义。
更何况,大家应该还记得,对于演戏,我应该是比他们两更为合适的戏子。
苏浙当时的表情和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个男女皆可时的表情可以一拼,他的脸部尽量的维持着表面的稳定,但嘴角的抽搐和之间的颤抖却掩藏不了他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他骂出来会更好,至少我是能够接受他的破口大骂,和什么狗屁形象没关系,该大骂大哭的时候女人就别憋着,利索的哭出来没有什么值得怪罪的地方。
但没有,苏浙是谁啊,他是那个和我吵架眼泪都在眼眶里打了不知道几个转都还能收回去的女英雄,他怎么会让他自己陷于这种没有礼节、没有风度的境地,苏浙敛了敛神色,“我们真的就没可能了?”
聪明。
苏浙,至少是在和我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你是足够聪明的女人,所以才能把我这种心没在你身上的浪子锁得有点紧。当然,也是我愿意,我两之间的感情唯一对等的就是这种和利益等价的交换。
我看着他,没有回答。
这时候是个男人就应该把主动权给他,即使是我说‘我们之间完了’,但分手这两个字要当真的说还是要由女方来,我几个月前的预防针应该打的卓有成效。苏浙,在你了解我的同时我也在了解你,说出那两个字,快,别辜负我对你的希望,你明白的。
“好,”苏浙的笑声干脆的响起,“分手了做朋友总是可以?”
我微微的展开笑容,“当然。”
我满腔都是对人性自以为是的掌控,我自己无比骄傲而又卑微的认为,我在上帝老头儿和自然叔统治的小块土地边上终于有了我自己的一块疆土,虽不说万里江山这么美妙的存在,我能有个边边角角便是成功的开始。
但事实往往都会像那些沾沾自喜的人证明,用一个有一个鲜血淋漓的铁证如山摆在面前,告诉我,你真心想得太多,生活就是该用一种恰到好处的白痴眼光来看,这样你才能活得美妙。
那是被心甘情愿统治的蝼蚁,我虽然是个渺小的人类,但在还能挣扎的时候,也要试试拼尽全力的放纵。
我是在苏浙用冷静自制的目光把我送出门的时候忽然回到我到明海的第一年。
这一年的故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因为没有说的必要性,但是我在那时候竟然无法阻挡的想到了那个没有必要被记录下来的事情。
去上小学一年级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人的一次。吴忠国——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他当时为什么要自己送我去学校,随便找个人不就行了,多大点事。
但是当时我认为,是他亲自把我从我安静而孤独的小岛里接出来,然后送到这个满是人头的世界里。这个人挤人的拥堵世界没有我夜晚安静的海啸声,没有我有回音的海贝,没有我温暖干燥的小木屋,没有我在那座被人抛弃但又被人珍惜的小岛上的一切。
我站在比六岁的我高上不知道多少的成年人人群中。我没有傻逼的仰望他们——这动作太蠢了。
当时我正忙着我自己的事业。
我慢慢的把我那时候瘦而细的手腕从吴忠国手里抽出来,一点一点的抽出来,如果我一下用力肯定敌不过一个中年男人巅峰的力道——我小时候就知道一点这种作战时候的策略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行动。
在我终于费劲了心思从吴忠国宽大的手掌里溜出来后,我扭身背着他就开始狂奔。这是我一个人的逃亡,只有我一个人。曾经把我带到这条逃亡路上的人都死了,而未来要真的下定决心和我一起逃亡的肖天铭还没有来临之前,我在这条宽阔到让我觉得永远都逃不走的路上只有一个人,我撒开脚丫狂奔,这是我的世界,这是我一个人的逃亡。
可是我忘记了,吴忠国他不仅有比我要有力的胳膊、手掌,他还有比我更长跑的更快的腿,他把我拎在手里——他左手抓着我后背的衣领,将我的双脚带离地面,这让我在瞬间感受到了一种先前从未有过的惶恐,后来我知道这是害怕被再次抛弃掉。
但好在,就是在吴忠国把我提起来的时候,我的灵魂在一起高高在上的注视那个满脸惶恐但仍要咬牙坚持的孩子身上,他用他故作悲天悯人的目光温柔的注视着我,就像我日后注视无数路人那样,他温柔的看着我,他的视线变成温柔的羽毛扫过我的眼角,湿润的心脏这时候开始结冰,咔嚓咔嚓的响声,一寸一寸的布满我当时和小手掌般大小的心脏。
我听到我的命运□□,我听到我自己的誓言。
从今以后,我吴燃再也不要把命运放在让别人决定的手上。
很荣幸,在我初三毕业到明海第一的高中而拒绝了吴忠国要我入伍之后的事情,就是吴家二公子变得很穷,很穷。没什么事,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惶恐。
直到我站在苏浙家的大门前,他细长且白嫩的手指按在门把上,他温柔的视线——他是真的温柔,目送我离开的背影。在我忍不住回头找到他的视线的时候我再次听到耳边的轰隆声和心底漫开的巨大惶恐。
我仅仅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但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作者有话要说:
☆、第 15 章
当时的我不知道,而现在站在街头手里握着肖天铭的吴燃也不知道,我心脏只是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种钝痛的抽了抽,像是被人用刺刀狠狠的刺过来而无法躲开那般痛苦。
美国的圣诞节能够像中国的春节那般,在空气里燃烧这种数的清看得见的喜庆,而后打开他们的盒子,在这个世界还没结束之前,让这种一年一度的拯救来的更为虚无缥缈。
我是说,这个吴燃他还是不知道他即将要面临的会是什么。
他得在和他怀里的小年轻一番好好的温存之后的第二日才会得到消息:苏浙自杀,成功。
这时候站在街头上演着凡人普通爱情的我只是按着脑海里那句话说出口,然后在轻不可见的羞涩之中,和撞在我怀里的人紧紧的抱在一起,而后任我莫名其妙的情绪继续蔓延,直到把我吞噬得干净。
我把肖天铭领进我自己先前买下的屋子里,转过头来问他,我的视线终于也不知道要落在哪里,“要不要先洗个澡?”
说完我再次暗暗咬下舌尖,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好的话题。
幸好,肖天铭只是揉了揉胃,笑着说:“还是先吃东西吧,好饿。”
我转身去叫外卖,虽然这时候我应该给他做一餐让他这辈子就算是头发花白、牙齿掉光了都还忍不住回忆的时候带着笑的午饭,但是先前来自灵魂深处给我百枪不入的心脏那阵拉扯让我还是恍惚着不知何感。
其实说来惭愧。我吴燃这种人虽然有点缺少感情,但并不意味着我一辈子都要在感情这种东西里面醉生梦死,我的世界理应有比这种欢爱更为重要的东西,如果不说是更重要,那他们至少要能排的上号。
从目前看来,倒是说感情这回事说的更多。有时候,不经意间就说了全部的秘密,也许就像我现在这样,我把我的事业和我的感情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但只要是情感上一点点温柔,都能让我在这种温柔里获得更多的罪孽清偿。
吃完饭的这个下午我和肖天铭在住处逛了逛。
真浪漫,我还没有试过和同性去做这种原始的调情手段。但肖天铭显的很满足,他一路都在说话,偶尔的停顿仅仅是为了让他说到冒火的嗓子润点水。
在他终于对我生活地方的物理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夜幕也刚好拉开帷幕。
我看着他拿着我的衣服走进浴室。我该承认,那时候,看着他年轻而挺拔的背影,我竟然有点紧张,就和昨晚入睡今早等他那时候那种带着期待的紧张。我把卧室上面的灯关掉,开了床头暖黄的台灯。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允许自己有这种期待,所有的期待都是为了后面更深一层的失望,但很高兴的是,肖天铭出来之前我就让这一切终结。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你衣服忘在外面。”
——真是拙劣的借口。
肖天铭的笑声响起来。在浴室里回音荡荡,而后传到我四周,“你够了啊。”
我像是泄气般的嘲笑我自己,早几年我还对这个世界里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嚣张的扬起我的爪牙说,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事,一般我都能做成功。而现在我就在肖天铭干净的笑声里被清空了欲望,我敲了两下门,“洗快点,小心着凉。”
原来我吴燃也有这么关心别人的时候。这是好事。
这个晚上是我难得的能够和一个人就光温柔的抱在一起,竟然什么败坏道德风俗的事情都没做——其实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肖天铭还没成年。他比我还要成熟冷静的告诉我那是他后面的第一次。意思就是这个小未成年其实已经把我煎的半焦的油条大哥给玩了。
好说的玩意儿。
这个冬天来临之后的夜晚是我和肖天铭在真的跨越一切之前难得的温存,我们的拥抱直接从夏天跨越到了冬天。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苏浙最喜欢的是秋天,这个季节的女人可以不用穿很多衣服,而且他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护肤品来维持干燥季节里他一个人的百分百水润。
我说过,这个晚上得发生一件好事,只不过他是一件有效期为八个小时的好事。而且据大家所知,好事一般都不太长久,或者说,其实他们还是挺想长久的,不过总有更多的事情和借口让他们长久不起来。
由此他们总得换上一点新的东西来把我身边的故事重新组装。
就算我心里隐约做好什么东西即将来临的准备,但任谁一大清早的接到贺牧装了弹夹的电话心情都没法稳着,还好我是吴燃。
“怎么了?”他的呼吸声沉重到我在国外都能听到,该感叹技术的进步还是他贺牧呼吸功能的退化?
“告诉你一件事。”
“说。”
“苏浙死了。”
贺牧,其实你可以把那件事的奠基感觉删掉,直接来后面的这句话,我受得了,这没什么大不了,我的下唇在刹那间受到我牙尖的锐利。我对我自己、对贺牧说,十分的笃定,这没什么大不了,你大可以放肆的来。
我的声音冷静的不像话,就像我双唇上渐渐蔓延的铁锈味道,鲜美绝伦,“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中午被他公司的人发现送往医院,抢救无效。”
我听见我固执的声音,一边又一边,苏浙,别让我用恨你的方式记住你一辈子,这不值得,你活得好好的就胜过我们之间所有只有输、永远都没有赢的战争,“具体时间。”
贺牧叹了一口气,“割腕的时间大概估计在上午十点。”
是了,就是我给苏浙打了一个‘朋友’的电话,我在那刻,在我这辈子极少有过的紧张和欢喜下迫切的想要找个人分享那时候我的心情,我竟然像是瞎了聋了般选择了苏浙。那时候我就算随便在通讯录里挑个人——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中文,我都可以随便嚷嚷几句然后再他们的莫名其妙里挂断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为什么是苏浙。我听见我内心那个人举着刀的质问,为什么是苏浙,为什么偏偏是苏浙。吴燃,你选择了结的人,为什么要是这个爱你到这般绝望境地的女人。
我对贺牧说话的时候竟然还能把持我疯狂边缘的冷静,“他在哪家医院?”我的声音真冷静,没了那份做作的温柔听上去舒服多了,“他没有家人,葬礼让我来办。”
贺牧的声音刹那间也有了难堪的意味,“我就是他的家人。”
作者有话要说:
☆、第 16 章
我听见我从胸膛上升来的呜咽,我听见我自己一声响过一声打在我脸上的耳光,“不,贺牧,你得知道,只有我是,你不是。”
这是一个不应该由我提起来的传记。
苏浙四岁来的美国。他是和她妈妈一起外嫁到美国来,当时我和苏浙站在我房间外的阳台边上,他递给我一杯味道极美的香槟,好味道,正是庆祝一个故事要活下来的好时机。
苏浙当时新修了一个利索的刘海,我不过是不经意的夸了一句,有味道,就让他的情绪在大起大落之后和我开始回忆往昔。
我知道他只是想找个让他足够相信或是足够深爱的人来讲述这么一件普通的往事,我甚至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那时候他以为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结婚。
我说过,苏浙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胜过我千百倍的存在,二十七的他对那时候不过二十一、来美国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