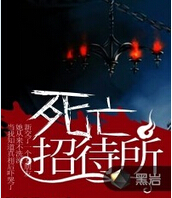死亡的真谛-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排想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场所公开他们的关系的。邦德很快从意识到M还有性生活这一事实所带来的惊讶中恢复过来。他突然发现他从这一情境中获得了乐趣。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新闻界将用什么样的言辞来描绘英国友善大使跟秘密情报处处长的约会。然而,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们也是人,就跟任何别的人一样。他们又都离了婚。邦德不太肯定,但他想哈钦森一定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邦德并不认识麦威利。邓肯。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很适合担当一个智力比他高得多的人的助手之类的角色。邦德想像得出,要是他老板愿意的话,邓肯会跑着去替哈钦森倒满咖啡杯的。
晚餐上主要的菜肴是烤牛排、刚上市的土豆和新鲜豌豆。邦德一直打量着M和哈钦森。他俩显然已深深坠入爱河,哈钦森时不时地在M耳边说上一两句话,M听后总是眉开眼笑。在某个时刻,邦德敢打赌,她一定在哈钦森的大腿内侧拧了一把,因为他突然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接着他俩就笑出声来。邦德朝迈尔斯爵士瞥了一眼,他也在盯着那一对儿。他一直皱着眉头,神情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
喝过咖啡后,男人们回到了藏书室。迈尔斯爵士拿出里斯瓦牌雪茄,一种邦德挺喜欢抽的牌子。闲话了一阵后,他挪到迈尔斯爵士身边。
“怎么样,詹姆斯?晚饭吃得还好吗?”他问道。
“很好,先生,非常出色。我得表扬一下戴维森。”
“噢,看在上帝份上,别再叫我‘先生’了,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遍了。”
“积习难改嘛,迈尔斯先生。”
“你没有回答我第一个问题。你还好吗?”
“很好,我想。我们遇到了一些难题。眼下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的,我也听说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听起来很糟糕。一点都没进展?”
“现在还没有。希腊国家情报局眼下正做着大部分调查工作。我们有一些调查员也在塞浦路斯调查情况。也许我会再回到那里工作一阵。我们得等待,静以观变。”
“你跟M相处得怎么样?”
邦德犹豫了一下,微笑着说:“她不是你,先生。”
“这并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相处得很好,迈尔斯。她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的看法也许并不一致,但我尊重她。”
“啊,要是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她在选择男人的问题上正在犯致命的错误。”
这使邦德感到很惊讶。“哦?”
迈尔斯爵士摇了摇头,露出一副刚刚嚼到一粒沙子似的表情。“一个卑鄙的人。”
“是吗?我还以为阿尔弗雷德。哈钦森是整个伦敦最受人爱戴的人呢。他在国会里春风得意,跟首相的关系也很好。”
迈尔斯爵士不吭声。
“难道不是吗?”
“这个人欺骗他的前妻,他是个撒谎者,一个吹牛大王。”
“我想,这正好说明我对政治懂得很少。事实是,他在我眼里显得很有魅力。很显然,M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就在你我两人之间说说而已。”迈尔斯爵士声音粗哑地笑着说。“世界友善大使,真可笑。一个天大的玩笑。”
“何以见得?”
“我知道他的几件家事。但我什么也没说,忘了它吧。”
“你非常了解他吗?”
“其实并不。我们在布兰德玩过几回桥牌。他输牌时总是大发脾气。他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你认识的,就是那个长着刀疤的德国人。”
“德勒克斯吗?”
“正是。哦,请别在意。我只是不喜欢哈钦森身上的某些东西罢了。就是这样。请忘了我所说的话。”
一瞬间,邦德仿佛捕捉到了迈尔斯爵士口气中的一丝嫉妒情绪。难道他也被新的M吸引住了,所以对她选择了别人深感不快?邦德立刻抛弃了这个荒唐的想法。
他们的谈话被M的到来打断了。她的脑袋出现在门廊里,朝邦德和迈尔斯爵士点点头。“噢,你在这儿呢,詹姆斯。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对不起,迈尔斯爵士。”
“当然可以,亲爱的,”迈尔斯和蔼可亲地说。
邦德跟她出了这间屋子,来到哈钦森所在的房间,他正站在迈尔斯爵士新近画的一幅水彩画面前欣赏着呢。
“这老头子有出色的天赋捕捉光线和阴影,不是吗?”哈钦森说,又眯着眼凑近画布。
“詹姆斯,”M开口说话了,“阿尔弗雷德有些信息,也许对塞浦路斯的案于有用。”
“真的吗?”
“明天上午10点钟请到我办公室来。这个时间行吗,阿尔弗雷德?”她问道。
“行,亲爱的,”他会心地一笑说。“那敢情好。”
“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告诉我们呢?”邦德问。
“我亲爱的,”哈钦森说,“我们正在这儿享受光阴呢,不是吗?看在k 帝份上,让我们别在这儿谈论公事吧。我还想再来一杯。要我带点儿什么吗?”
“谢谢你,不必了。”邦德说。迈尔斯爵士是对的。这个人身上有种令人作呕的东西。“那么,10点钟,”他说。他朝M点点头,然后走开了。
邦德步入大厅,想找戴维森。今晚他接触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很惊讶地发现,大厅里只有海伦娜一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正在一只玻璃烟灰缸里揪灭烟头。邦德曾看见她跟别的情报处人员聊天,但他不愿加入其中。但眼下既然只有她一个人……
“什么事,海伦娜?公共汽车这儿不停。”
她微笑了。“你好,詹姆斯。我正在想,今晚你会不会来跟我聊天。”
“我很想来着,但总是没有机会。介意出去走走吗?”
“天气有点儿冷,而已很潮湿,不是吗?”
“我们可以穿上外套。来吧,让我们找找看。”
几分钟以后,他们已经穿上外套,很快走出了屋子。夜晚的空气很冷,天空乌云密布。邦德点燃了两支烟,把其中一支递给海伦娜。他们绕屋来到一块凹陷的空地上。一个大大的、带有丘比特雕像的喷泉池位于空地正中央,但现在喷泉已经关闭了。
“我在这儿感到有些失落,”她说,“他们事实上并不是我的伙伴。”
“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也不是我的伙伴,你能相信吗?”
“是的,我会相信的。”她说。“你不像其他办公室里的人,詹姆斯。”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一点都不像。”
“我想你是在夸奖我吧,”他说。
她无意中露出一个微笑。
从屋子后面的窗户里映出的光线照在这片空地上。他凝视着她那鹅卵型的脸蛋、棕色的短发和大大的蓝眼睛。她其实很美。她回视着他的注视,最后说道:“现在想做什么?”
“我想吻你。”他说。
她的目光闪烁着光芒。“你总是直截了当的,”她说。
“总是,”他说着,俯身向前吻她。她伸出双臂来拥抱他,并且张开嘴,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几秒钟后,他俩分开了,但邦德的脸仍贴着她的脸。他感到一颗雨滴打在他的前额上。
“天下雨了,”她轻声说。
他靠近她,又开始吻她,这一次,她更加热烈地回应他。雨点开始大起来。
最后,她轻轻地把他推开,气喘吁吁地说:“我知道这不是性爱的前奏,不过我想指出,你是我的上司,詹姆斯。”
他的双手一直拥住她的双肩。他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们……我不该这么做。”
“我们最好还是进屋吧,不然要湿透了。”
天空响过一阵雷声,雨开始下大了。邦德挽住她的身子跑到屋前。一到前门,她就笑出声来。他们在屋檐下站了一会儿。现在,一阵尴尬的寂静笼罩着他俩。
“我看到你时正想离开,”他终于说。
“现在雨下大了,你得等等再走。你不能在这么大的雨中把车子开回去。”
“不,我现在要走。我们明天再见。”
他在她的肩头拧了一把,说:“把我忘了吧。”说着,他就走进雨中。海伦娜望着他离开,喃喃地说:“我不怪你。”
邦德向过道尽头他那辆本特利车走去,听凭雨水浇在他身上。他为刚才发生的事诅咒自己。他明白卷进与自己办公室里的女人的爱情之中意味着什么。要是她没有那该死的吸引力就好了!是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促使他去引诱他遇到的每一个可爱的女人?昙花一现的爱情固然有其美妙之处,邦德也总不乏拈花惹草的经历,但它们总不能满足邦德那神奇的需求。难道他追求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情——真正的爱情——以弥补他的空虚?苦涩的答案却是:每当他允许自己真正地爱上一个人时,他总会在烈火中自焚。他心灵的创伤实在已经太深了。他坐进车子,冒着大雨返回伦敦。每当他反思自己孤独而又不幸的生活时,邦德身上黑暗的一面总会紧紧地攫住他!他本来希望大雨会冲刷掉阴郁的心清,但现在他已经把它当做一个老朋友来拥抱了。
第四章 胆大妄为
急切的电话铃把邦德从沉睡中惊醒。荧光数字钟显示2 点37分。他打开灯,拿起白色的话筒,但电话铃仍响个不停。邦德这才意识到,是红色话筒在响,他的肾上腺素猛地冲了上来。红色话筒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会响起。
“邦德。”他对着话筒说。
“詹姆斯,法典第60条。”这是比尔。特纳。
“我在听着。”
“M的命令。”特纳说了地址和门牌号码。“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荷兰公园大道过去,是一幢叫帕克大楼的房子。”
特纳挂上了电话,邦德从床上一跃而起。“法典第60条”意味着事件涉及特别的安全级数。换句话说,邦德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谨慎。
邦德花了十分钟到达荷兰公园,一个充满了肯辛顿西部边缘色彩的地区。这个地区是因为荷兰大厦——一幢有四百年历史的、纯粹为了款待国王和宫廷而建造的大楼——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小镇上的屋子在各种各样的街道和广场四周拔地而起。许多内阁成员和政府精英都住在这一地区。
帕克大楼是一溜长长的三层楼的棕色和红色砖墙楼房的总称。一条安全隔离带阻止了这里的交通,但眼下,在其中一幢大楼面前似乎有许多活动正在进行。一辆救护车就停在眼前,它的灯还在不停地闪烁。一辆警车和两辆没有标志的15科的车子也停在大楼前。邦德跨出本特利,朝人群中走去。他向一名宪兵出示过证件,后者把邦德带到大楼前门。
他在大楼前门遇到了比尔。特纳。警察的隔离带在大门外数英尺的地方延伸出去,以阻止好奇的邻居向大楼内窥探。
“詹姆斯,进来吧,”特纳说。“M在这里。”
“出了什么事,比尔?”
“是哈钦森,他死了。”
“什么?”
特纳靠近邦德,压低嗓门说:“这是他的公寓。M正在这里跟他过夜。她快要发疯了。”
“有什么进展没有?”
“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我给你打了电话后,已打电话通知了麦威利。邓肯。他正在路上。”特纳让邦德进屋去。15科的司法鉴定专家正在拍照和检查现场。M在起居室里,穿着一身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缎子睡袍。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脸色苍白,惊恐不安。当她抬起脸来的时候,邦德能发现她实在沮丧之极,不仅因为她心爱的人死了,而且也因为让她的雇员们看到这种处境。
邦德在她身旁单腿跪了下来,抓起她的手。“你还好吗,夫人?”他轻声问。
M点点头,抑制住自己的抽泣。“谢谢你能来,詹姆斯。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我感到如此……出乖露丑。”
“别在意这些,夫人。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摇着头,浑身颤抖着。“我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分钟之前他还好好的,接着就……”她闭上了双眼,试图控制住自己。
邦德站起来说:“我进去看一眼,夫人。我们过会儿再谈。”
他跟着特纳走进了卧室。
邦德见过许多目不忍睹的惨状和凶杀现场,这一次也不例外。死亡使这个本来很温暖的房间充满了阴森森的感觉。这房间用橡木做护墙板,里面有一张像国王的御床一样奢侈的大床和大量华丽的家具。阿尔弗雷德。哈钦森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如果不是他的眼睛瞪得老大,恐惧地冻僵在那里,人们一定会以为他睡着了。尸体上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迹象表明曾使用过暴力。他看上去好像是心脏病发作的受害人。在这样一种状态,阿尔弗雷德。哈钦森当然已不再是邦德数小时之前碰到的那个杰出的友善大使了。现在他只是一具用粉笔勾下轮廓的普普通通的尸体而已。
“是心肌梗塞?”邦德问法医道。法医正坐在床边记着笔记。一个来自……15科的检查专家正在用一架宝丽来广角镜5SLR一次成像照相机,拍下尸体多角度的聚焦照片。
“看上去有点像,”医生说。“当然,我们要做尸体解剖检查。我不认为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是什么意思?”
“哈钦森死于心脏病和肾脏衰竭,嘿!可他的身体健康得很呐。听过莫德莱太太的陈述,再经过检查他的尸体,我的意见是,他是被谋杀的。”
“怎么个谋杀法?”
“某种毒药。最有可能是神经毒素,一种能使心脏停止跳动,使呼吸系统窒息的物质。一旦进入血管,这种东西就没法清除。它的作用非常快,但不是太快,我想。受害人在几分钟内会极其痛苦。”
“尸体上会留下什么痕迹吗?”
“在他右大腿的外侧有一道可疑的挫伤痕。看见这小小的红印子吗?”医生指着哈钦森上腿部的一块圆形的挫痕。“起初我还以为这只是一块丘疹,但进一步的检查表明,他曾被一只针筒注射过。”
邦德又看了看尸体。负责人走进了卧室。
“是邦德长官吗?”
“是的。”
“我是霍华德侦探。我们已准备好,可以搬运尸体了,要是你同意的话。”
“你仔细检查过他的私人物品没有?”邦德问。
“我们刚刚检查完。我可以请你跟莫德莱夫人谈谈吗?我没法从她那里问出什么东西来。”邦德点点头,走出了卧室。他发现M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既没有走动,也没有喝咖啡。他在她身旁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