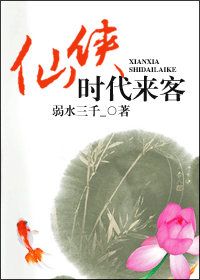巴巴罗萨来客-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次晋见开始时,气氛相当不妙。如果说,斯捷帕科夫将军急于晋见总统,他显然并不知道总统是多么急于想见他。几乎有一个小时,这个肩负俄罗斯各种问题的重担的人一直在斥责着斯捷帕科夫,像重机枪似的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将这些“正义天平”成员抓起来?为什么毫无进展?将军同志曾答应总统,不,是向总统保证真的沃龙佐夫在俄罗斯,而且在妥善关押之中。那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形势?这些毫无意义的屠杀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上帝知道,他曾将可怜的小尼古拉·切尔努什(他喜爱地叫她尼古拉申卡)当作女儿看待。这种事太可怕了,必须制止。将军同志,这种事什么时候能结束?
总统气急败坏,已经到了极限。这个国家每天都面临着新的经济灾难,他不知道部队效忠于政府的时间还有多久,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他都受到威胁,都在挨批评。他不是超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格鲁吉亚都有新问题出现,不用说其他地区了。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在巴格达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解。成千名美、英、法、意和沙特阿拉伯的部队盘踞在科威特边境,而1 月15 日的最后期限已逐渐逼近。难道斯捷帕科夫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血腥战争可能在中东爆发?这场冲突可能就是那预期了很久的火星,会使中东陷入火海。最终,可能是阿拉伯人与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甚至可能是阿拉伯人相互间的战争。苏联战斗部队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训练的。斯捷帕科夫将军没有看到战争计划的制定者们已经花了几个月在为这样的事件制订计划和战斗序列吗?但是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苏联的势力范围已经形成新的秩序。俄罗斯正在同美国做交易。在整个西方盟国、北约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长期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当作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杠杆。
总统发火说,“现在我们不要这个。哪怕我们做一点儿小事,只要能被人解释为反美,我们就会失去我竭尽全力从华盛顿取得的援助。”
斯捷帕科夫是克里姆林宫的老手了。他看到过有权势的人上台又下台。
在年青时,他甚至参加过一次宫廷政变。那是在可怜的老勃列日涅夫时代。
虽然名义上勃列日涅夫仍是苏维埃帝国的领导人,却陷入了老糊涂的境地,使他周围的人颇为尴尬,只能将他当作傀儡来看待。
以前,他也曾受责骂,这就像耳旁风一样。斯捷帕科夫对总统同志的怒斥并不在意,只将需要作出清楚答复的地方记住。手握大权的人可以长篇大论地说个不停,但总还有个限度,单方面的怒吼总有到头的时候。
因此,鲍里·斯捷帕科夫等到这一场风暴过去后才开口说话。他明确地告诉总统他是怎样看待“正义天平”的,这事应该怎样去应付。
“鲍里,你刚才应该径直将你的意见告诉我,就可以节约时间了。现在我去与基洛夫格勒联系……”。
“别,别。您应该特别清楚这件事不应该公开出来。还是我将您的命令用书面写下来,然后我亲自去交给别尔津将军。这样最保险了。”
这样,在总统办公室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电子窃听器也不能渗入总统办公室),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捷帕科夫口述了命令,由总统签署。
这时已很晚了。斯捷帕科夫需要睡眠。他驱车回到别墅。如果他们早上走得早,到午饭时就能将命令交给别尔津将军,第二天晚上,行动就能迅速展开。他认为事情正顺利地进行着。
他们在一起的短短几天里,尼娜·比比科娃几乎成了詹姆斯·邦德的妻子。白天他们肩并肩地在摄影现场工作,中午和晚上工作结束后就在像古老的修道院餐厅的饭堂里吃饭。从第一天的早晨开始他们就常常与彼特·纳特科维茨和他们的向导娜塔莎在一张擦得很干净的长桌上用餐。金发的娜塔莎腿很长,好像一直伸展到肚脐那里。
娜塔莎没有把自己的姓告诉他们,但邦德不必特别聪明也能知道她和彼特·纳特科维茨这时正在成为“一回事”。他希望纳特科维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摩萨德的任何军官,特别是有纳特科维茨这样经历的军官,肯定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饭堂所提供给他们的食品是不一般的,因为他们是孤立地处在被雪和冰包围的无法通行的森林中的。它的特味菜是蔬菜燉驯鹿肉,头两次还很鲜美,后来就迅速走下坡路。不过菜谱还有熏鱼、许多黑面包和大量的格瓦斯——农民们家庭自制的啤酒。
每天晚上,尼娜和邦德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去,洗淋浴并悄悄地讨论白天所见所闻。第三天晚上,他们在9 点钟就倦极上床,马上就睡着了,虽然后来尼娜弄醒了邦德,干许多妻子会拒绝干的事。他们幸福和满足地又进入梦乡,一个没有索比堡幽灵们的梦境。
邦德猛地惊醒了,他的手慢慢伸出去抓住那用手掌捂住他的嘴的手腕。
他正待更快更用力地扭那手腕时,他没有用力挣扎,只是扭住那个手腕。发现是娜塔莎想悄悄地叫他起来。
他一面仍然抓住这女孩的手腕,一面撑起一只胳膊,在黑暗中观望,想要弄明白她的意图。她灵活、熟练,另一只手无声而准确地打着手势,像在与某个古怪的人联系。
她的意思是叫醒尼娜并跟着我。很安全,但是要赶快。
尼娜不费劲就醒了,而且马上进入待命状态,这是只有医生、护士、战士和特殊情报部门受过训练的战地军官才能做到的。邦德的双脚刚着地,她就无声无息地在走动了,一面系上她那毛巾布袍。
娜塔莎仍用手势向他们打招呼,警告他们不要弄出声响来。走廊空无一人,那里有一种神圣的宁静气氛,似乎整个木制建筑已被巨大的毯子裹得严严实实。这种感觉非常鲜明,以致在极短的时间里,邦德还以为他们遭到了雪崩。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房子被雪盖着,然后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奇怪的感觉仍在脑海中滞留,提醒他正处于古老的神圣地方,祈祷和信仰已渗入到土地、树林、石头或房架中,永远被禁锢着。
娜培莎打手势叫他们贴近墙面,在经过的每个门口都暂停一会儿,确保
室内对外面的情况什么都听不到。他们知道这些房间里住的是“证人”,不过除了第一天早晨站在电梯附近的三个人外,他们对其他任何客人都只在摄影棚和饭堂里见过面。
在他们到达电梯以前,向导推开了一扇门,门上标有国际通用的出口标志,就是一个小人在楼梯上向下跑。邦德始终认为这标志着上去像一个原始人正在“向上开”的自动扶梯上向下冲。
在门的另一边,有楼梯可以上下,也是木头装饰的。他想象这可以焚烧得很旺。他第一次感到这整个建筑物在夏天可以成为死亡的陷阱,因为太阳会把木头烤成干的易燃物。
他们爬上一层楼梯,通过顶端的门进入一个走廊,这走廊与他们从房间出来穿过的走廊一模一样。这时,娜塔莎向他们发出信号,要他们走得快些。
她越过一排电梯,轻轻打开另一扇门,门上用俄文、法文、德文、英文和阿拉伯文写着:“非公用,不得入内。”
他们进入了一间小的空荡荡的办公室。百叶窗拉了下来,唯一的家具是板条箱和包装箱,随便扔在柔软的绒毛地毯上。一盏装有绿色玻璃灯罩的铜制读书用灯在一个角落的包装箱上亮着。彼特·纳特科维茨坐在旁边的板条箱上,两条腿悬空晃动着,脸红红地。门一关上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皱着眉头看着邦德。
娜塔莎问:“他们还没有来?”
“亲爱的,如果他们已经来了,那一定就是躲在这些箱子里。塔辛卡,他们还没有到。”然后他又将注意力放回到尼娜和邦德身上。“詹姆斯,对不起在子夜将你们弄起来。娜塔莎自从我们到了这里就一直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告诉他们,寝室里都有窃听器,但造这房子的人还没有安上录像设备。“看来我们有必要被窃听,但不必被监视。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年人了①。”他以逗乐的姿态拍了拍大腿,“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有足够的人来监视窃听设备,但金科玉律是……”
“假设他们正在窃听你说的话。”邦德补充说。
① 不必被严密监视。——译者
纳特科维茨点头说,“当然,这房间没有窃听设备,这是我们抵达后第一次能无拘束地谈话。”
“你完全肯定吗?”邦德深抱怀疑地打量着这房间。他对在没有经过检查的地方谈话抱有怀疑态度。他常常告诉这一行里的人,他宁愿用俄罗斯人只在露天和在无法使用定向扩音器处谈话的办法。”
纳特科维茨愉快地转动着眼睛。“我完全肯定,百分之三百地肯定,但对你只有一百五十。”
“娜塔莎呢?”邦德问她是否忠实可靠。
纳特科维茨的脸冷了下来,眼神也突然变得严肃了。“如果我告诉你她没有问题,你应该相信我。老实对你说吧,她那天晚上在莫斯科出现时——在他们要我们睡一大觉以前——我是不相信我的眼睛的。她是和我在一起的,你该懂我的意思吧。”
邦德看起来吃了一惊,甚至有些害怕。“摩萨德已打入俄国了吗?”
纳特科维茨将头歪向左侧,似乎是为了强调他讲的话。“当然。西方媒体说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冷战结束后已成了过时的恐惧,他们的脑袋始终离不开北约与苏联在欧洲的角斗。但是,詹姆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错了。
甚至摩萨德也一如既往紧盯着伏尔加河。不这样做就太危险了。娜塔莎和一些其他人在这里已经多年。当他们在70 年代还是孩子时,我们就将他们安插到这里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被安插到这里,看看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真的,我……”他在听到来自门外的声音时,突然停住了。
邦德像一只猫一样轻轻地贴着墙跳到门的铰链处,右手捏成拳头,拇指缩在掌中,食指和小指的关节略向外伸,手臂弯成直角成L 状,身体摆出打斗的架势。
娜塔莎则在另一边紧贴着墙,紧张地做好一切准备。纳特科维茨和尼娜一动也不动。这时门把轻轻地转动,门外一个声音轻悄悄地说道,“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
尼娜吸了一口气,这声音似乎充满了整个房间,此时两个高高的身影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当尼娜说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开场白时,声音都变了。然后,她纵身投入一对老人的怀抱中,他们默默无声地站在门边。
三个人搂在一起,手臂互相环抱,成了一个紧紧的人圈——爱与安慰的结合。
邦德向前跨了一步,但纳特科维茨从板条箱旁溜过来,制止了他。这三个人紧紧贴在一起有几分钟。当他们分开时,面颊上都被泪水浸湿了。
这老人仍然有着老军官的风采,背直得像块木板,头发整洁但已成铁灰色。胡须已经剃掉,皮肤像一张老旧、无人照料的皮革,但双眼仍保留着多年前为国家服务时的热忱。
那位妇人却未能像她丈夫那样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美丽漆黑的头发已不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头短而银白的头发,虽仍有光泽,却已略见稀疏了。
她的那双手已是老妇人的手,长有老年斑,皮肤松弛。嘴边有着皱纹,双眼道出了自从离开舒适的伦敦后所经历的艰辛生活。这些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但当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却是出奇的年轻。埃梅拉尔德·莱西说,“詹姆斯,我估计你们以为我们是叛徒,是吧?我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已很长时间了。”
“顽固不化的叛徒。”迈克尔·布鲁克斯仍带着微笑说。在以前,人们说布鲁克斯能以他的微笑打动蝎子。
邦德摇摇头说,“不。”他走近他们。“不,我知道你们是胡斯卡尔。
我知道已有一段时间了。”他转向尼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你的父母还活着。我昨晚对你这样说时,你没有追问我,但你看起来有点害怕。”
布鲁克斯伸出手去抚摸他女儿的肩头,“这是因为她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胡斯卡尔这个名字可追溯到11 世纪。当时英国受丹麦人统治,缴纳着极不公正的税金,即丹麦金。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集体意识中仍在引起痛苦的因素,它促使英国人想出许多办法来绕过目前的税法。
多年来,英国人忍受着北欧海盗的入侵,这种入侵毁掉了整个整个的社区。但是英国人在许多代国王(如艾西尔雷德和爱德蒙·艾恩塞德)的领导下坚持战斗。直到1016 年,英国最终被丹麦王克努特所征服。
克努特对王国的军事结构作了某些改革,包括建立一种“地方军”(胡斯卡尔)的组织,这是职业民团,配有巨大的由两人同使的丹麦斧,随时准备与来自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突袭进行战斗。
也就是这种武器才使为迈克尔·布鲁克斯和埃梅拉尔德·莱西选择代号的人叫他们为胡斯卡尔,因为他们是对莫斯科政权的一次新的双人进攻。
随着60 年代中期第一批英国叛徒的丑闻使特工人员的效率和士气受到打击,邦德的情报局计划了一次快速反击。迈克尔·布鲁克斯长期以来一直与出色的密码专家埃梅拉尔德·莱西有联系。这时情报局叫他走,散布足够的暗示说,他受到了怀疑。这些暗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布鲁克斯断绝了与单位的一切联系,只有埃梅拉尔德除外。他还向驻苏联大使馆中被怀疑与克格勃有关系的人说了一些暖味的话。然后,他就坐等鱼儿上钩。终于,克格勃咬钩了,他也就失踪了。事实上,克格勃只将他带到丹麦,在那里,有经验的审讯官对他进行了他们所谓的“深入分析”。用普通语言来说,就是他们要挤干他,但布鲁克斯在离开单位以前受到很详细的指示。他熟记了一些看起来是第一流情报和与主要情报单位之间联系的情报。莫斯科中心对布鲁克斯那么轻易地就说出情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