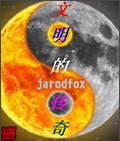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vorausicht”或“Vorsicht”。因此,毕从他个人关心的事物中所挑出的这个姓,实际上恰是同一时期里我经常想到的姓,这是他并不知道的事。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情况清楚些了。但我认为,如果分析阐明了毕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的话,我们会对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会洞察它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十一点钟时,我等待赫尔。毕来访,但他未来。然后我去拜访安东。
冯。费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①。
我很惊奇地发现,赫尔。毕就住在同一公寓的另一层楼中。后来,关于这事我对毕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到他府上拜访过他;但我确切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在谈到“Hervon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正在VolksuniverAsitat②讲授英文课程的佛洛英德。爱特里格FreundOtorego是我的女儿吗?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这是他第一次将我的姓Freud(弗洛伊德)误为Freund——如同我已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员工习惯于误称的那样。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讲给我一个梦,他被该梦惊醒,认为这是一个十足的“Alptraum(恶梦)”。他
①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英译注。
②系“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理解的“成|人教育”。——英译注。
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恶梦”是什么词,当别人问及此词时,他竟误以为是“amare′snest”(即:牝马之窝),当然这是很荒谬的,“amare′snest”指某种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而“Alptraum”则应译为“nighmare”(恶梦),这一联想中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同为英文。我当时想起了约一个月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我与毕正坐在房间里时,我在伦敦的亲密朋友欧内斯特。琼斯博士不期而至,我和琼斯已很久没见面了。
我示意琼斯到隔壁房间去,等我给毕完成诊疗再谈。
()
但毕马上从挂在候诊室的照片上认出了琼斯,甚至表示希望我把他介绍给琼斯。琼斯是一本论恶梦(Alptraum)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毕当时是否知道该书,他忌讳阅读精神分析的著作。
下面,我想开始研究从有关毕的联想背景和动机中可得到的分析结果。
“Forsyte(福尔塞)”或“Forsyth(福尔西斯)”这个姓对于毕和我具有相同的意义,我之熟悉这个名字完全归因于他,不同平常的事情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那位医生的到来,这个姓在另一种含义上对我来说变得富有意义了,但在这之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它引入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此外,这个姓在精神分析疗程中出现的方式,与这件事本身一样令人感兴趣。例如,他还说:“我正好想起了Forsyte(福尔赛)这个您所熟悉的小说中的姓。“
他不曾提及这一出处,却能将这个姓引入他自己的经历中,并因此提出了它;这是一件早就有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发生的事。他当时说的确实是:“我也是一个Forsyth(福西斯),这是那姑娘对我的称呼。“我们不会弄错,这句话所表达的忌妒的需要和自我贬低二者兼而有之的心情。但如果将这句话用下述方式补充完整,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了:“您的心思竟然完全用在这个新来者身上,这伤害了我的感情。请返回来注意我吧,我毕竟也是个Forsyth(福西斯)——尽管实际上如那姑娘所说的,我只是一个HervonVorsicht(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一联想的线索,又回到以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能引起同样的忌妒心。
“几天前您访问了我的公寓——不是去看我,而是看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这种想法使他把“Freund(弗洛伊德)”这个姓误为“Freund”。
出自讲演提纲的FueundOtorego(弗洛伊德。爱特里格)这个姓名必定会在此出现,因为她作为英文教师提供了明显的联想。尔后,回忆中又出现了几周前的另一位来访者。对这位来访者,他无疑也是心怀忌妒的,但却深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琼斯博士能够写出论恶梦的专著,而他自己充其量不过能做这样的梦罢了。他之提到弄错“amare′snest”的意思是与此相关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反正我不是真正的英国人,如同我不是真正的Forsyth(福西斯)一样。”
我现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说成是不合适或不明智的;我曾预先告诉过他:一旦外国学生或病人回到维也纳,我对他的分析和接触便可能结束。
事实上,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但至此我们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对同一时期中提出的三个孕育于相同动机的联想做出了解释。而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即:没有思维传递能否形成这三个联想?这个问题在这三个联想的每一个中都出现了,因为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毕能否知道福西斯医生刚刚对我进行了首次拜访?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里所访问的那个人的姓吗?他知道琼斯博士写了一本论述恶梦的专著吗?倘若都不能,那么,他联想中所显示的难道仅仅是我关于这些事的了解吗?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维传递的结论,就取决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Freund(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①。
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Freund)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K。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friend〔Freund〕。”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①德文词“Freund”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1919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HervonVorsicht”甚感惊讶。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
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
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假定赫尔。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告终了!他说不定就是刚从教授那里回来的哩。“
我不可能再推进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
我们又落得个“没有证实”的结局。
但我应该承认,这个实例倾向于肯定思维传递现象。
此外,在分析的情形中,经历过上述“神秘”事件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赫伦。多伊特施(HeleneDeutsch)于1926年发表了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这些神秘事件受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所决定的情况。
B我确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的态度,使你们很不满意。你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个这样一种人的例子:这种人作为科学家终身做着令人尊敬的工作,然而到了晚年却变得低能、轻信和虔信宗教。“我知道这类人中有一些伟人,但不应将我归于此类。至少我还没有变成宗教狂,我也希望自己还没有陷于轻信。如果一个人在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尊重事实,避免与其发生令人难堪的冲突,那么他在晚年时就仍应时刻准备尊重新的事实。
无疑,你们希望我能够坚持一种温和的有神论信念,并且毫不留情地否定一切神秘事物。但是我不能曲意逢迎,而且我还要劝你们对思维传递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持更为宽容的态度。
你们不应当忘记,我在此论述这些问题,不过是在尽可能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它们。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时,我也曾感到一种担心,以为它们使我们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威胁:如果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实的,恐怕科学宇宙观就注定会被唯灵论或玄秘论所取代了①。但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想,如果我们以为科学没有能力吸收和重新产生神秘主义断言中的某些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东西,那表明我们的科学宇宙观还不十分信任科学的力量。尤其就我们所说的思维传递现象而言,它实际上看来有助于我们把科学的(或者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那些很难把握的心灵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人的心灵活动使另一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心灵活动。
联结这两个心灵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
①弗洛伊德逝世后问世的《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的引言部分,对这些思想有详细的阐述。——英译注。
灵感应的这一端,一个心灵活动转化为该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该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灵活动。这种转化无疑类似于别的转化过程,例如打电话时听和说之间的那种转化。试想一下,要是我们能够掌握这种精神活动的物理等价物,那该会怎样地了不起呵!在我看来,由精神分析把无意识插入了物理性事物和以前被称为“精神的”事物之间,从而可能已经为将上述转化过程假设为心灵感应铺平了道路。只要我们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当然,目前还只能在想象中进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不了解在一个大的昆虫社会中,共同的意图是怎样产生的吧。
我们由此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种系进化的过程中,它被更好的、借助于被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取代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可能存留在幕后,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情绪激动的民众中),还会表现出来。
这一切猜测固然还不能肯定,并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不必害怕它。
如果心灵感应这种事物是一种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它很难证实,我们仍可以假设它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当我们能够表明它尤其存在于儿童的心灵生活中时,它是可能符合我们的预期目的的。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儿童经常感受到的焦虑:自己的所有思想不跟父母说他们也都知道——这与成年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服惊人的相似,而且也许就是后者的起源。不久前,一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多萝蒂。伯林翰(DorothyBurlingham)在一篇关于儿童分析与母亲的文章中(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