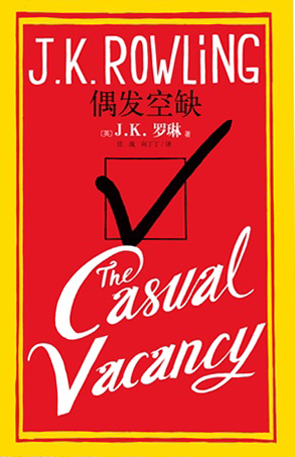偶发空缺-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莉之流的下怀吗?),她身边站着矮脚鸡一样的特莎·沃尔,身穿灰色外套,纽扣处绷得紧紧的。
玛丽·菲尔布拉泽领着孩子们沿着小道走向教堂。玛丽脸色极度苍白,看上去瘦了好几磅。六天能轻这么多吗?她一手牵着双胞胎里的一个,另一只手臂环住小儿子的肩膀。最大的弗格斯跟在后面。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柔软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亲戚们跟在玛丽和孩子们身后,整个队伍跨过门槛,好像被昏暗的教堂吞噬。
众人马上也都朝门口拥去,一时间竟堵塞住了,好不尴尬。莫里森一家跟贾瓦德一家挤在了一起。
“你先请,贾瓦德先生,老爷,你先请……”霍华德嗓音隆隆地说,还伸出一条胳膊,护佑医生头一个走。他又利用自己的庞大身躯挡住其他人,自己跟着维克拉姆走了进去,两家人都跟在后面。
圣弥格尔及众圣徒教堂的走廊铺着长长的品蓝色地毯。穹顶上金星闪耀,铜箔反射出顶灯的光芒。彩色玻璃窗花色繁复,令人惊叹。正殿中央,诵读使徒书信的一侧,圣弥格尔从最大的一扇窗户探身望向下界,肩膀两侧生出天蓝色的翅膀。他一手高举宝剑,一手紧握两把金尺。一只穿便鞋的脚踩在身躯挣扎、肩生蝙翼的撒旦背上,撒旦浑身黑灰,拼命想要站起身来。圣人的表情自在平静。
霍华德走到和圣弥格尔平行处,停下了脚步,示意家人坐进左边的长凳。维克拉姆则右转坐在对面。莫里森一家和莫琳鱼贯而入落位坐好,霍华德还在品蓝色地毯上稳立不动,等帕明德走过身边时,对她说:
“太可怕了,这个。巴里。真是令人震惊。”
“是的。”她回答,露出嫌恶他的表情。
“我一直觉得这种长袍子看上去很舒服,是不是?”他朝她的纱丽点点头,又加上一句。
她不回答,而是在贾斯万身边坐下。霍华德便也落座,像一个巨大的塞子,把家人牢牢封在里面,万夫莫开。
雪莉双目肃穆地盯着膝头,双手合掌,状似祈祷。其实她正侧耳聆听霍华德和帕明德关于纱丽的几句对话。雪莉和帕格镇其他一些人一样,对于牧师老宅的命运颇感可惜。这幢宅子多年以前是修给高教会派教区牧师住的,牧师蓄着络腮胡子,还有一班围裙浆得笔挺的仆人,现在这里居然住进了一家子印度教徒(雪莉从来搞不清贾瓦德一家到底信什么教)。她想,要是她和霍华德去庙里或者清真寺——或者贾瓦德一家做礼拜的其他什么地方,一定会被要求遮住脑袋,脱掉鞋子,还有别的各种把戏,否则别人就会抗议。可是帕明德却可以罩着纱丽大摇大摆地上教堂来。她又不是没有正常的衣服,平时每天上班不都穿着吗?如此的双重标准令雪莉义愤填膺。那女人就没想对他们的宗教表现出一点敬意,说远一点,对菲尔布拉泽也是。她不是应该很喜欢菲尔布拉泽的吗?
雪莉松开两掌,抬起头来,注意力转向身边走过的人群,以及献给巴里的花束有多少、有多大。有些花束在圣体护栏前高高垒起。雪莉认出议会送的那一束,那是她和霍华德组织筹款买的,传统样式的一大束花,扎成圆圆的一圈,花都是蓝色和白色,这正是帕格镇纹章的颜色。他们的花和其他所有的花圈一样,在一束扎成真桨大小的花桨面前黯然失色。花桨是女子划艇队送的。
苏克文达从座位上扭头寻找劳伦坐在哪儿,花桨就是她那会花艺的妈妈扎的。她想跟劳伦做个手势,表示自己看到了花桨,并且很喜欢。可是人群太密了,实在找不到劳伦的踪影。苏克文达虽然很悲痛,可是看到大家落座时纷纷侧目,示意彼此看那花桨,心里还是生出一股自豪。八名队员里有五个凑了钱。劳伦告诉苏克文达她吃午饭时找到克里斯塔尔·威登,并且只身面对她那一群坐在报刊亭旁矮墙上抽烟的狐朋狗友,任凭他们奚落讥笑。她问克里斯塔尔要不要也凑个份子。“好,我也凑一份,没问题。”克里斯塔尔是这样说的。可是她到底也没给钱,所以卡片上没有她的名字。苏克文达也没看见克里斯塔尔来出席葬礼。
苏克文达的内心像铅块一样沉重,但左臂隐隐作痛,每动一下,还总袭来一阵针刺般的感觉,疼痛反而抵消了内心的悲伤。何况穿着黑色正装、眼露凶光的肥仔·沃尔离得很远。两家人在墓园里短暂相遇过,他连瞧也没瞧她。大概是两方父母都在,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就像有时候安德鲁·普莱斯在场,他也会有所收敛一样。
昨晚夜深时分,不知名的网上敌人给她发来的是一张黑白图片,上面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裸体小孩,浑身都是柔软的黑色毛发。她早上为参加葬礼梳洗穿衣时才看到,赶紧删除。
上一次开心,是什么时候?她记得仿佛已是前世。那时还没有任何人对她嗤之以鼻,她就坐在这座教堂里,好几年都无忧无虑。圣诞节、复活节,还有丰收节,她满心欢喜地唱起赞美诗。她一直喜欢圣弥格尔,喜欢他前拉斐尔派的秀气俊美脸庞,喜欢他金色的卷发……可是今天早上,她第一次从他身上看出了不同。看着他脚踩拼命挣扎的黑色魔鬼,她觉得他若无其事的平静表情里藏着阴险自大。
长凳已经坐满了。运气欠佳的悼唁者还在往里走,灰尘弥漫的空气里因为有了他们压低的交谈、回响的脚步和衣服窸窣声,而显得稍微有了生气,他们走到教堂最后边,站在左面的墙角。有些人心存侥幸,踮脚眺望走道两边,看看长凳上会不会偶尔还空着一两个位子。霍华德稳如泰山、纹丝不动,直到雪莉拍拍他肩头,低声说:“奥布里和茱莉亚!”
霍华德一听此言,立马转过身体,挥舞着葬礼仪式安排单招呼弗雷夫妇。他们踏着走道地毯步履轻快地走来。奥布里高高瘦瘦,开始有了些秃顶的迹象,穿着黑色西装,茱莉浅红色的头发挽在脑后,盘成一个假髻。霍华德吩咐家人起身,往里挪了几个位子,好让弗雷夫妇坐得宽敞舒服。他们微笑着对他表示感谢。
萨曼莎夹在迈尔斯和莫琳中间,挤得要命。她感到莫琳尖尖的髋骨直戳进她的肉里,另一边,迈尔斯裤兜里的钥匙也硌得她生疼。她很恼火,想为自己争取一厘米的空间,可是不管迈尔斯还是莫琳也都无处可退。她只好双目直直看向前方,报复似的想维克拉姆。上次见面已是几个月以前,他的英俊迷人却没有消减一分。他在人群中是那么耀眼,帅气得无懈可击,有些傻气,让人忍不住想笑。他的双腿修长,肩膀宽阔,衬衫扎进裤腰里,腹部平坦,配上睫毛浓密的黑眼睛,和帕格镇其他男人相比,他简直就像一个神。迈尔斯前倾着身子跟茱莉亚·弗雷低声说笑,钥匙扎得萨曼莎大腿生疼,她幻想维克拉姆撕开她身上的藏青色裹裙。想象中,她没有穿配套的贴身背心,深深的峡谷暴露无遗……
调音器吱吱嘎嘎响起来,人群安静了,只余衣裳摩擦的窸窣声。人们纷纷转过头去。棺材正沿走道抬来。
抬棺人搭配得很有问题,简直有些喜剧效果:巴里的两个哥哥身材都只有五英尺六英寸,可是后面的科林·沃尔却足有六英尺两英寸,所以棺材后部明显比前部高得多。棺材也不是用磨光的桃花心木做的,而是用柳条编成的。
这不就是个野餐篮吗?霍华德心想,觉得简直荒唐。
柳条篮子经过时,许多人脸上都掠过惊奇的神情。不过有些人已经提前知道棺材会是这样了。玛丽告诉特莎(特莎又告诉了帕明德)材料是长子弗格斯选的。他觉得柳条好,因为是可持续性的林木,生长迅速,所以对环境比较有利。弗格斯对一切绿色的、生态环保的东西都抱有极大的热情。
比起大多数英国人用来盛放尸体的结实木棺,帕明德更喜欢这个柳条筐,喜欢得多。她的祖母总是有一种出自迷信的害怕,怕灵魂被困在沉重牢固的东西里,英国人用钉子把棺盖钉实的做法,总让她感到心痛。抬棺人把棺材放在铺了锦缎的停棺架上后便退下了,巴里的儿子、哥哥、姐夫都回第一排坐下,科林一个人步履跌撞地回到家人中间去。
有两秒钟,加文举棋不定。帕明德看出来,他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唯一的选择好像是在三百人的注视下沿着走道原路返回。不过一定是玛丽做了个手势给他,所以他一闪身,脸绯红,钻到第一排巴里母亲身边坐下。帕明德一共只跟加文说过一次话,还是给他做衣原体治疗的时候。打那以后他再也没跟她面对面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
听上去,牧师似乎并没有细究自己口中吐出字句的意义,而只是在斟酌吟诵的腔调,仿如歌唱,韵律分明。帕明德对他的风格已经稔熟,因为和圣托马斯小学其他家长一起参加了好多年圣诞颂歌会。尽管熟悉,她面对头顶上那脸庞雪白、俯视众人的战士般的圣人仍然极不自在,还有教堂里四处的黑色木头、硬座长凳、镶着宝石的金色十字架、异域风格的布道坛,以及挽歌的旋律,这一切都让她感觉凄冷不安。
于是她不再听牧师自我沉醉的嗡嗡声,转而再一次回想起父亲。她曾经透过厨房窗户看见他,仰面躺着,一旁她的收音机在兔笼顶上奏着音乐。她和母亲、姐姐逛服装店的时候,父亲也会这样一躺就是两个小时。她似乎还能感觉到摇父亲时,隔着热乎乎的衬衫触到的他的肩膀:“爹地,爹地。”
达山的骨灰,他们撒进了伯明翰那条悲伤的小河——里河。帕明德还记得灰蒙蒙的河面,在六月多云的那一天。灰白的粉末如雪花一般从身边飘走。
管风琴发出低沉的琴声,音乐响起。她和大家一同起立。一眼看到尼安和西沃恩的后脑勺,姐妹俩都长着泛红的金色头发。达山离开他们时,她也是这个年纪。帕明德心里涌起一股温柔的感情与一阵剧痛,还有一种复杂的渴望,她想握起她们的手说,她都懂,都懂,都能体会……
天已破晓,就像第一个清晨……
加文听到这一排有人在以高音歌唱:是巴里的小儿子,他还没到变声期。他知道这首圣歌是德克兰选的。这又是玛丽挑出来与他分享的葬礼可怕细节之一。
他觉得葬礼比他之前所想的还要可怕,简直就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倘若棺材是木质的,那还好一点。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能感觉到那轻飘飘的柳条匣里巴里的尸体,实在恐怖。他身体的重量让人心惊。抬棺走过走道时那些自以为是、目不转睛的观众啊,他们到底懂不懂他肩上扛着什么?
接下来是另一个胆战心惊的时刻:他意识到没人给他预留座位,所以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原路折返,没入站在后排的人群……然而他却受到召唤,不得不去第一排就座,大有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这就像坐在过山车的头一排,每个突然转弯、大幅倾斜,受到的冲击都是首当其冲。
他坐在那儿,离西沃恩的向日葵只有一尺之遥。向日葵的脑袋足有一口炖锅盖儿那么大,躺在一大捧苍兰和萱草中间。他心里希望凯跟他一起来了。这想法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可却是实实在在的。倘若有人跟他一起,给他留一个座位,就能给他莫大的安慰。他之前哪里想到独自一人来出席,会是这样一副如同私生子般的可怜模样。
圣歌终了。巴里的哥哥走上前去致辞。加文想不通他怎能说得出话,巴里的尸体可就躺在面前,在那一棵向日葵(从一颗葵花籽种起,长了好几个月)底下啊。他也想不通玛丽怎能那样安静地坐着,头微微弯下,似乎在注视交错放在膝上的手。加文心里暗自导演台上人的演讲,免得被哀歌的情绪浸透。
他就要讲巴里遇见玛丽的故事了,只等说完小时候这一段儿……快乐的童年,玩耍作乐,没错,没错……来吧,往下讲……
之后人们还要把巴里再搬上车,送到亚维尔,安葬在那里的墓地,因为圣弥格尔及众圣徒教堂小小的墓园二十年前就满了。加文想象着再度在众人的注目下把那柳条棺材放进坟墓里。跟那相比,扛着棺材进出教堂就简直算不上什么了……
双胞胎里的一个哭起来了。加文用眼睛的余光看见玛丽伸出手来握住女儿的手。
快点说吧,无论是出于什么该死的理由,快点说。
“我想,说巴里是一个了解自己心灵的人,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巴里的哥哥用沙哑的嗓子说。他讲到巴里小时候淘气的故事时,已经赚取了几次笑声。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很紧张。“他二十四岁时,我带他去利物浦参加无女伴周末晚会。刚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就离开宿营地奔赴酒吧。吧台后站着老板的女儿,还是个学生,金发碧眼,非常美丽,她是星期六晚上来酒吧给父亲帮忙的。结果巴里一整晚都靠在吧台那儿,跟她找话聊,聊得她父亲都使唤不动她,差点要发火。巴里还假装不认识角落里那一帮小混混。”
台下稀稀疏疏有人笑。玛丽的头垂得更低,一手拉着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回到帐篷里,他就告诉我他要娶那个姑娘。我心想,等等,喝醉的难道不是我吗?”听众中又传来几声笑。“第二天晚上巴里又把我们拖进了那个酒吧。等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明信片寄给那姑娘,告诉她下个周末他会再去。一年之后他们结婚了,巴里是个识宝的人,我相信只要认识这对夫妻的人都同意。后来他们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弗格斯、尼安、西沃恩和德克兰……”
加文仔细调整自己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尽量对巴里哥哥的话充耳不闻。他琢磨着,假如死的是自己,他的哥哥会怎么发表悼词呢?他没有巴里那样的运气,感情经历说不成一个如此美好的故事,从来没有走进酒吧就发现一个完美的太太人选站在吧台后面,金发碧眼,温柔微笑,还准备给他倒上一扎啤酒。没有。他曾经有过丽莎,可丽莎从来不觉得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