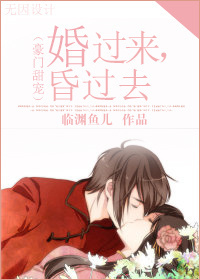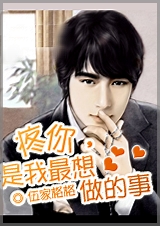过去的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绿灯亮了,这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走过马路,拖着苦难深重的躯体,眼含热泪,继续去寻找那隐藏在城市背后僻静的一隅。
C
不知从那一年开始,总之是在结婚以后,他开始注意所有的女人,开始对所有的女人产生兴趣,欲望和冲动, 所有的女人都能构成对他的吸引。 他知道,自己的审美观在下降,甚至完全失去了审美观,而变成了一个雄的动物。而在从前,他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女性美的崇拜者,一个浪漫谛克的小男孩。远远的欣赏一个个美好的女子,犹如欣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独自的做梦幻想。纯情少女们在闪光的雾霭之上隐现。平常的女孩从不曾进入他的视野,参加熟人的婚礼,他总是不无遗憾的想,他们怎么能那样心满意足的娶一个并不出众的姑娘。一个个姑娘在他的身边擦肩而过,他毫不惋惜。但他终于恋爱了,那个姑娘从厕所出来,他走进去,发现便池上一条染血的卫生纸,一汪残留的微黄尿液。顿感一种穿透肺腑的嫌恶和恶心,一种深深的绝望,觉得万念俱灰,人生了无生趣,没有意思,不值得活。但后来他还是结了婚,他知道了不管多美的女人都是女人。女人不是天使,不是女神,不是圣母玛丽亚;不是含羞带怯的小脸儿,散发着玫瑰的芬芳。她们也是人,是女人,比男人更虚伪,更放荡,更愚蠢,更肮脏。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风华绝代,明眸皓齿,都是那些酸男人的自作多情。你看到了她们迷人的脸蛋,诱人的腰身,却没有看到他们胸脯上的一块狗癣,屁眼儿里的一朵痔疮。他在心里恶毒的作践着女人,但却仍然迷恋着她们散发着异味的肉体。他不放过一次寻欢作乐的机会,他觉得每一次的寻欢作乐,都是白得,占便宜,是死之前又多了一次享受。自从他第一次把女人压在身下,他就感到了灵魂的深深堕落和肉体的丑恶卑微,他要更深的堕落下去,直到死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梦非梦
梦非梦
秋禾忘了点儿什么,他感觉到自己忘了点什么,可一时又想不起。他只记得昨天夜里死了一个人,他要赶去参加葬礼。其实也不是什么葬礼,只不过是送去几刀烧纸,跪在棺前磕个头,或者领受死者儿女一个大礼。但多数人只是去送纸,倒并不一定非得磕头。但秋禾今天决定在死者棺前磕个头,死者生前是他爱戴的一个老人。
临出门时,秋禾拿了些钱揣在兜里。他要先到小卖部去买纸。路上,天有些阴,但不是很阴的样子,有没有太阳,秋禾没在意。一阵小风刮过,旋着,卷起半尺多高的一柱黄尘,在秋禾脚前一米多远的地方移动着。像是为秋禾在前面引路的顽皮小孩,使他觉得又惊异又有趣。并不快走,惟恐踏灭了它。但它却拐向了路边,消失在了旁边的沟里。
路上,秋禾遇到一个人,拿着一杆秤,卖的什么秋禾没看清。他问了一句,那个人却像没有听见,头也没抬,低声嘟哝着什么。秋禾看着他有点面熟,直到到了小卖部,才记起这是他中学的一个同学。
小卖部里没有几个人,秋禾都认识,他无意中说起刚才遇到的那个同学,屋里的人都惊愕的看着他。秋禾并没往心里去。他买了纸,但在掏钱时,发现兜里除了一只空烟盒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没有抽烟的习惯,兜里不会存有抽完的烟盒,临从家里出来时,明明放进去的是钱。怪事,他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小卖部的姑娘说你没带钱,就先把纸拿走吧。秋禾把纸按在柜台上,说:先放在这儿。
出了小卖部,急匆匆的往回赶,走了一段。秋禾发现自己走错了路 ,绕了一个圈子。路上他又碰到了那个中学时的同学,仍然手里拿着盘秤,低头自言自语着什么。
家里的门洞开着,母亲端坐在屋内,慈祥,和蔼,可亲。给你五爷送几张纸,别忘了给你五爷磕个头。这声音熟悉而又陌生,似在那里听过。思忖着,在抬头时,发现屋里仍是空空,母亲已经不见。
秋禾把钱仔仔细细的数了一遍,揣进兜里。向屋外走了几步,又把钱掏出来,数了一遍。天气如此晴好,阳光灿灿的照着,不大不小的风扫过空荡荡的大地,略有些凉。远处横着三两个村庄,遮住了地平线。秋禾觉得离第一次出门已经年代久远了,恍如隔世。小卖店里自己没有拿走的黄纸,想来已经朽烂变糟不复存在了。
秋禾漫无目的的走出村子,道上没有一个人,新犁的大地如黑色的浪涌。白杨林里有几片残留的黄叶从行列中飞出,飘向大地,一切都很平凡朴素。有一首歌或是一种旋律从心头升起,秋禾觉得身边有了很多人,一支望不见头尾的队伍,在行进。悲壮雄浑,发出一种整体的共鸣。渐渐的,这种声音开始清晰具体,秋禾听见有人在哭,他发现哭的是自己,他已站在了一座坟前。远处道上有一个孩子甩着一根树条走过,旁边的林带发出低吟。母亲已经在五年前死去,而五爷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第一个离去者。那种场景,气氛,化为一种氛围,成为他心头永久的笼罩。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很多人在村子里永久消失,倒下,便不再站起,排列成一条虚无的栅栏,伸向过去,伸向时间深处。
秋禾打了一个寒颤,他已经站很久了。他想起自己那个同学就是五爷的孙子,他在市场上卖菜时被流氓杀害,已在半个月前火化。秋禾更清醒了,昨夜死去的那个老人,其实是自己的一个梦,原来自己这半天来一直游荡在梦境中。可仔细回忆又有些怀疑,掏了一下衣兜,自己放进去的钱还在。远处的村庄,黑色的大地也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回到村里,秋禾到小卖店看了看,见那沓黄纸还在,放在柜台上,一切都是真的。但秋禾马上又疑惑起来,他想起两次碰到的那个同学。莫非人真有灵魂,只是在平常状态下看不见,只有在特异情形下,比如在梦游中,才能看见。
天有些阴,没有太阳,走着,一阵小风刮过,旋起一股半尺高的黄尘,在前面两三米的地方移动着,像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顽皮小孩。秋禾蓦然想起,自己已经忘了忘了点什么,双重遗忘。他要振作起来,重新搜索那已经疲累的记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金色秋天
金色秋天
眼前的玉米铺子一直向远处延伸,连成一片。矮壮粗实的金龙戳在驼背的父亲旁边,漫不经心的扒着玉米。驼背的父亲扒得极快,看也不他看一眼,仿佛以此来让金龙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懒惰,金龙也不看父亲,仍然不慌不忙的干自己的,拿起一根玉米秆,便直起腰,慢慢的扒。并不看玉米,眼睛四处张望着。他扔得很准,从未把一穗玉米扔到车厢外。而父亲不是把玉米扔到车厢上弹回来,掉到玉米铺子旁边,就是扔到车厢的另一边。金龙觉得父亲很可笑,看着父亲的驼背,他想来点小幽默。说别人扒玉米得弯腰,还是你好,不用弯腰,又省事,又省力,天生一副扒玉米的好身材。隔着未放倒的玉米地,另一边传来女人的说笑声,不是还响起一个男人的吆牛声,金龙极想过去看看。他的手的动作开始快起来,父亲扒完一铺子,他也能扒完。过了一会儿,金龙发现父亲慢下来,便也不再快扒,又恢复到漫不经心的状态。但父亲马上又快起来。他发现自己慢时,父亲就快扒,自己快时,父亲反而慢下来。他还发现父亲偷偷瞟着他,在自己没有撵着他干时,就不时投来又厌恶,又恼怒,又蔑视,又无可奈何的一瞥。金龙从心里瞧不起父亲,又觉得他可怜。
拉着车的牛从铺里拽出玉米杆来,并不吃叶,只把玉米棒子吞到嘴里,咀嚼着。嘴角泛出白白的泡沫。“吃,妈的,就会吃, 胀肚胀死你。”驼背的父亲愤愤地骂着。但牛又变戏法似的,把一穗玉米弄到了嘴里。驼子两步窜过去,左手死死抠住牛的鼻子,右手从牛嘴里,拽出了那穗沾满牛的唾液的玉米,扔到车上。牛不满的喷了两下鼻子,低下头,啃起了垄台上的一株稗草。金龙到旁边几步远的玉米地里拉屎,完事往出走时,踩到了一卷染血的卫生纸。金龙骂了一句脏话,把卫生纸踢到一边。这时,玉米叶哗哗一响,一个年轻女人钻进来,没看见金龙。解开裤带,就急急地蹲下来,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尿击声。金龙蹲下来,什么也没看见。在地上爬了几步,隔着枯黄的玉米叶子,终于看到了小半个雪白的屁股。二十七岁的金龙身子抽搐了几下,档间的阳物胀大坚挺起来。
“你这个畜牲。”驼背的父亲忽然对牛恶狠狠的骂了一句,随后便不再吭声了。金龙等着父亲骂第二句,他好接下去。他只说一句:我是畜牲,你是什么?但父亲好象猜到了他的心里,没有给他说这句话的机会。整个下午,金龙都心事重重,脑子里老出现那半个雪白的屁股。
地离家只有一里多地的样子,先是一段土路,然后便是平坦的沙石路。道上车辆来往着,有的车上拉着未扒皮的玉米,就坐在车上扒,任牛自己走去,抛下一路雪白的玉米叶,被风吹进沟里。而空着的车辆便在颠簸中发哐哐的声响。
金龙把车赶到自家的场院里,把车停好,车胶用一根粗木棒掩住,又给牛扔了一捆玉米秆。母亲也在场院中,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左手,好像一枚长不开的小小的馒头,熟练的协助右手把玉米装进筐,然后再倒进早已搭好的栈子里。母亲干得十分认真,没有一刻停歇,好像要永无休止的干下去。没有几根头发的秃顶晒得褐红,显得四周的花白头发格外刺目。金龙发狠的卸着玉米,二尺勾几次深深的刨进车铺板里。他气喘吁吁,汗水淋漓,觉得自己苦难深重,可悲可怜,是这个世界上的最不幸的人。卸完玉米,金龙一屁股坐在玉米堆上,裂开嘴,哭起来。哭得悲悲戚戚,动感伤情,泪水顺着黄黑色的大脸流下来,滔滔不绝,汪洋恣肆。母亲瘦小的脸上现出悲戚和苦愁,拎筐的手蓦然显得不堪其重。温顺的花牛在一旁若无其事的嚼着玉米叶子,平静的场院因了这呜呜啕啕的哭声,而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西天的太阳已经金黄,金龙的影子在玉米堆上起伏,显得古怪而夸张。大门外拉玉米的人在车上大声打着招呼,吆牛,声音远去。
金龙的哭声渐渐停止,从玉米堆上站起来,抹着眼泪,拿起鞭子,歪歪斜斜的赶起牛车,向院外走去。
母亲一下子瘫坐下来,全身没有一点力气。那只废手腕部开始疼痛,他觉得里面的肌肉全都绷紧拉伤,再也不会好起来。他用另一只手把它按在腿上,揉着,疼痛扩散开来,减轻了些许。心上某种温柔的东西开始滋溢,盈满了空落落的胸膛。场院上的玉米欣悦起来,一堆挨着一堆,低洼处投下一小片阴影,被夕阳照着的一面,显得更加金黄。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场院静谧而扩展,有庄稼的香气在空气中溢盈。秋天的黄昏仍然很温暖。房顶上冒出的炊烟在村子四周漫成白色的雾霭,空气中又有了点柴草的馨香。母亲看着渐渐模糊下去的场院,内心一片清虚静明,身上轻松没有一点乏累。那颗明亮的星又准时地在白杨林的右前方出现,村里响起一个男人叫牛声。
几天的时间,庄稼都已经割倒,大地豁然开阔,现出一片黄白色的苍凉。中午的时光依然很热,树叶绿得更浓,有一点风也是暖烘烘的,让人感觉不到秋天。金龙快快乐乐地走在路上,吹着口哨,心绪渐渐抚平。刚才,他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照例不是他的对手,使出老办法,从家里把他赶出来。金龙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现在要找的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地方。
村东头有一家小卖店,金龙进去时,卖店的姑娘正自己打着台球。金龙站在一边看,姑娘并不理他,仍打自己的。“太薄了,真臭。”金龙在一边扳不住。姑娘抬起身,把杆柱在地上,不悦的说:“你来,别在旁边说大话。” “你当我会输给你。”金龙说着就去拿台球杆。 姑娘拦住他,说:“先说赌什么。”金龙说:“你输了,给我一盒烟。我输了,买你一盒烟。”姑娘说:“那可不行,你输了,得买两盒烟。”金龙说:“中,反正我也不会输。”把球从洞里拿出来,重新开局。金龙要的是花瓣。他的技术并不比姑娘差,但今天连输两台,第三台总算扳回了一局。金龙连说晦气,便要走。姑娘并不客气,拽住他的衣领子,从衣袋里翻出钱,数数。回到柜台,拿出两盒烟扔到台球案上,便不再理他。
回到家里,父亲的火气还没有消,又赶他走。金龙便又出来,在外面转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志气,怎么就不能一走了之。好歹他也是快三十的人了,就这么让人撵来撵去,也太没个人样儿了。有什么了不起,也许走到别处去,倒能混出个样儿来。自己从前咋就没想到。金龙的心像开了一扇门,宽敞明亮的阳光射进来,他觉得又兴奋又欢喜。
金龙一路走着,二十里的路没觉出怎样累,就到了镇上。镇上的人比乡下多,金龙逛完了市场,又到百货大楼,在这个柜台前呆一回儿,那个柜台前站一下,多半个下午就过去了。金龙的肚子有些饿,兜里除了在卖店买的那里两盒烟,剩下的钱只能买一个面包,或两袋方便面。天快黑了,金龙不知道今晚该怎样度过,他想到了回家,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家,他是再不想回了。
来到车站,候车室里只有十几个人,长椅上空空落落,金龙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不一会儿,便昏昏睡去。醒来时,候车室里的灯已经亮起,里面已经有了半屋子的人,吵闹着,一种被遗弃,被抛弃,被忘记的凄凉感觉爬上心头。从今以后他就将在这前途未卜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金龙在镇上游荡了三天,被赶来的母亲找了回去。此时他正想搭上去省城的火车,离开镇子。母亲风尘仆仆的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