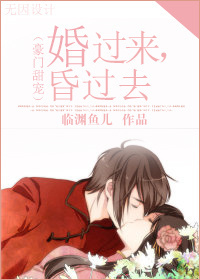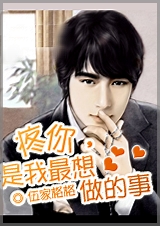过去的事-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计不再回到土地上。在相持几年之后,哥哥嫂子终于没能说服侄子们回来,在对将来老境的预期中,他们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只好变卖了房子土地,搬到了两个侄子所在的城市,离开了故乡。这一次或许是永远的定居。
路遇
路遇
我在车站遇到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时,他正站在公共汽车下,央求“那个兄弟”把他送到车站去。他也是坐这趟公共汽车来的,几个下车的人从他身旁匆匆忙忙的走过去。我走过他身旁时却不好意思走开了。
我攥着他的手,小心的走向车站,我怕他跌倒,给自己惹来意外的麻烦。到了候车室,把老人安顿到椅子上坐下。他拿出一只搪瓷缸,要我给他打点开水,我照做了。此时我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老人。他面目清瘦,两只眼睛全瘪了,像所有的盲人一样显出一副倾听的样子。黑色的衣裤,干净整洁,连脚上的鞋子都是黑的。老人不停的和我说着话,好像唯恐我走开,他又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把他领上车。老人说他出门总会有人照顾的,十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肯帮他,就什么都解决了,何况他遇到的不只十个人。老人的言谈很从容,语调平和而沉稳,使我内心增加了几分敬意。
老人不到三十岁就失明了,起初是白内障,还能看见东西,后来外省来了一个江湖郎中,说能把罩在眼上的那层蒙子剥去,结果完全弄瞎了他的眼睛。我问他开始时是不是很难受。他说死的心都有。可一寻思自己一死。老婆孩子谁养活,就硬挺着活过来了。以后他跟人学算命,知道自己就是这个命,八字早算好了。我说您真的信命。老人的语调还是那样平静,我信,眼睛都没了,信命会好受些。停顿了一下,老人又接着说下去。我有五个儿子,可我现在自己过,老儿子前年不孝顺,被我赶出去了。其实我也不是真心赶他走,可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就和老人分心眼儿了。赶他他就出去了,自己买了两间草房,让他回来都不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守着四间瓦房,闷了,就把门一锁,出来给人算卦,也没人管我。说不定哪一天,我死在了外边都没有人知道,我就是孤老头的命。我看了看老人,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他这样平静?
我们还想再说下去,可开始检票了,老人站起来,把手递给我,我拉着老人枯瘦的手,向检票口走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记忆中的小屋
记忆中的小屋
那在记忆中是一个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房子,墙是土的,房盖也是土的,开着门和窗,门和窗就好像是在四四方方的盒子上掏的两个洞。一个说不上多大年纪的疯男人就住在里面。疯男人曾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当兵走的时候曾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可从部队回来时就不正常了,终至于完全疯了。疯子有一根拐杖,三尺多长,光溜溜的,一头包着胶皮,出屋时总拿在手里,但他并不常出屋。生产队专门派了一个人给他做饭,说是做饭,其实永远是玉米面饼子。做饭的也是一个老头,廋小,一脸的麻坑,终身未娶,住在生产队里,做着放牛倌。麻子放牛极其不负责任,把牛撒出去就不大管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就经常把牛赶到屯外的沟里,骑牛消遣。有时他发现牛不见了,就到处乱找,可很少发现我们。除了骑牛,我们还玩其他一些游戏,当然什么游戏都有玩够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索然无味,就会有人提议去打韩八路。韩八路就是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疯子,姓韩,八路是我们给起的名字。
我们边走边说笑,散兵游勇般向那个小屋进发。离老远便停下来,有胆大的便主动请缨,去小屋侦察,趴窗观察一会儿,回来说在屋,众人就拣起土块噼噼啪啪向小屋发起攻击。打一阵之后,就见窗内伸出一支“长枪”,大家都知道这是疯子经常拿在手里的拐杖,众人一阵哄笑跑开。离老远看那支长枪抖动着,同时听见疯子在屋内发出嗒嗒的响声。大家更开心了,重新发起进攻,这次的进攻更加猛烈,疯子的长枪缩了回去。众人小心的靠近,靠到窗前,看见疯子猫在炕上的被里,淘气鬼们又往被上扔土块,打一下,被里的人就蠕动一下,同时发出一声叫骂。有时疯子也抓起一件东西打出来,落在地上却是一块玉米面饼子。可有一次扔出来的却是一把菜刀。这种恶作剧后来因为学校的干预而停止了,再后来疯子就死了。那个侍候他的麻子住进了这个小屋,在有一天麻子也死了,这个小屋再没有人住,终于坍塌,再不见了踪迹,只在记忆中存留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儿子初中毕业了,十六岁的小伙子,一米七八的个头,整天在家里晃。没毕业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并没把心思太放在他身上。反正他的学习并不太好,我对他也不抱太大希望,就是学习好我也不抱太大希望。现在的大学生有都是,什么东西一多了就贬值,他就是考上了大学也未必能出人头地,别说出人头地,可能连工作都不好找。我邻居家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上一家酒店当了服务员,邻居提起来就叹气。说白花那么多钱供他上大学了,早知今日还不如让她早早回家,还能帮家里干几年活计。我说她要念你能不让她念嘛,你要不让她念,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还不记恨你一辈子。邻居说也是。儿子不用我操这个心,要不是我硬逼着,他连初中都不想上了。所以,即使在他上学时,我也不用担心他用我的钱打水漂,那个操纵器在我的手里,但我也不能让他过早的离开学校,虽然读大学未必就成大用。但没有文化也一定不行,至少得够平时用。所以,儿子当初不想上初中,我连屁都没有让他放第二个,告诉他不但要去念,而且还不能去混,得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来,小心你的一身皮。我不能露出让他混完初中的意思,他要是知道我的这个意思,就更混上加混了。本来我想得挺简单,他初中一毕业,就跟我在家种地,我也用不着受那么大的累了。可现在他回到家,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在家就呆不住,就整天和几个半大小子出去溜达,有时连吃饭都不回来。更有甚者,还有时好几天都见不着他的影儿。回来一问,说上某某同学家去了。我当然不会全信,如果他在外面交上了坏人,还不把一生都耽误了。除了学坏的担心,我也不想再让儿子像我一样在家种地,他得你我更有出息,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个想法是他从学校回来以后产生的。我开始羡慕村里那些考上大学研究生的人家。村里前几年还出过一个医学博士,一个日本留学生。人家现在都在南方有钱的大城市工作,一个月挣五六千元的工资,而我的儿子却在家里无所事事,学会了抽烟喝酒,在卖店赊东西,在朋友和同学家聚会,吃请或请吃。他在学业上为我剩下了一笔钱,可现在回到家,对我血汗的蚕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能再让他这样在家混下去了,别人的儿子有大出息,我的儿子至少得比他老子有出息。我通过熟人关系,让他到了一个私人汽车修理部去学技术,可他干了不到两个月,就说什么也不去了。说在那里一干就是半夜,一忙连饭都不让吃了,一天就吃两顿饭,除了白菜土豆罗卜就没有别的。我当然不会再让儿子去遭罪。又把他送到了省城一个大技校,一年的费用加起来有七八千,出来包分配。这回儿子满意了,学得很用心,说学校条件如何好,吃得好住的好,课程也轻松。我觉得这一步走对了,盼望着将来他能凭自己的手艺吃饭。学习一年后,儿子被分配一家叫做鸿运达的汽车修配厂,工资一百五十元。儿子回家不象原来那么兴奋了,说修配厂和技校完全是两回事,在技校时是又干净又不累,到了修配厂就开始干活了,还时常挨师傅说。没活时也不让呆着,让拿着扳手来回走,不显得生意冷落,再次露出不愿干的念头。我先是把它臭骂一顿,然后,和他讲道理,说你现在技术还没学成,学成了也会像师傅那样挣高工资,也会有人敬着。那时候你也会带徒弟,脏活累活让他们干,也让他们没事儿时来回在前面走。但问题的关键是你得把技术学成了,怎样学成哪,就是得靠住,不愿学也得学,技术学好了,就有出头之日了,就不用回家干农活了。也在城里住下来,像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厕所厨房都在屋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过上神仙日子。可儿子终于还是离开了,是和其他两个学徒工一起离开的。他们以为一离开就会找到工作,可问遍了所有汽车修理的地方,都没有人收留他们。有的地方不是不缺人,可人家得有熟人介绍,不用生人。另两个孩子见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只有儿子留下来,在城里打起了零工,帮人装货卸货,不到一个月,终于坚持不住,回来了。我没有过多的责备他,又托亲戚给他找工作。结果儿子又去了一个更往北的城市,在那呆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能用他所长的工作。就在那里做了保安。但哪个地方太冷,儿子冬天里手脚都冻了,再加上这保安当下去也没什么出息。我就让他回来了,折腾了几年,他的年龄也不算太小了,我就张罗着给他订了亲。绕了一圈,经过了种种努力,儿子终于什么也没干成,最后还是回到农村,走了我的老路。不过这也没什么,儿子还是好儿子,是好儿子我就应该欣慰。
久远的马嘶
久远的马嘶
生产队是秋小时常去的地方,一个很大的院子,土围墙,院中有一个很大的粪坑,坑沿上矗着一个山一样的粪堆。一溜北房,进门左边是一个大灶台,一口大铁锅坐在上面,经常冒着热腾腾的白气。右边是仓库,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在秋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开过,秋从来没有试图猜想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那扇厚重的木门阻遏了他的想象。绕过高高的灶台,进了西屋,一溜长长的土炕铺在眼前,炕上铺着高粱秸编就的席子,席子已变成了褐黑色,有的地方已经磨破,露出土的炕面。西墙上方高挂着字体黑大标语,横贯整个墙面。相对的东面墙上并排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也是悬在最高处。只有毛主席让秋看着顺眼,其他的几个人怎么看怎么别扭,但秋知道他们都是好人,这让秋不自觉地抑制着对他们的反感。靠北面墙戳着一张破旧的黄油写字桌,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小方纸块,上面排列着人名和数字,秋知道那是社员的出工表,父亲和姐姐们的名字都在上面。除了北房,生产队的院里还盖有东西厢房,西厢房南面两间是栓牲口的地方,一长溜的食槽,槽上方一道光溜溜的横杆,系着缰绳,一到中午卸犁时,里面就是一片很响亮地咀嚼声。牲口棚的隔壁两间是磨房,里面摆置这一盘大碾和一盘小磨,磨道用青石铺成,经过长年累月的踩踏,光滑如境面。磨米拉磨时,就会传出如岁月一样悠长的响声。东厢房比西厢房略小一些,是装饲草的地方,秋经常看见一个精廋老头和两个壮汉在里面轧草。两个壮汉擎起巨大的铡刀,又奋力压下,秋总是担心干廋老头的手会被两个壮汉轧去,可干廋老头一点都不怕,和两个壮汉配合得滴水不漏,刚好在铡刀抬至最高点时,把草入进去。他们不象在轧草,好象在表演一种具有很高技巧的艺术,让秋着迷…
秋从小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很少和别的孩子疯,只愿意自己一个人玩耍。生产队的两个饲养员从不让别的孩子进生产队的院子,怕他们偷东西,弄坏农具,打破玻璃,被牲口伤着。但从不赶秋,他们知道秋不会惹祸,都喜欢他,有时还炒一把豆子给他吃。在童年的很多岁月里,秋都是在生产队度过的,那里有着他甜蜜温馨的童年回忆。
后来,秋上了学,就很少去队里了。再后来,他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毕业后又定居在大城市里,经历和感受着时代的迁变和时间的推移。有许多东西都改变了,被永远定格在了过去的时间里。秋在一个政府机关工作,算是一个小小的官员,每天和各种人和事周旋。但他每年春节都要回家,有一次同人说起小时候在生产队时的一些趣事,但人们已记不起他小时候都做过一些什么了,而他还以为人们一定会记得一个经常去生产队的孩子。
回到城里,秋到档案馆找出二十年前的报纸,尘封的记忆打开了,一切都带着过去时间的印记。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一切都进入了永劫,不再回归。这天夜里,秋做了一个梦,他又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院,看到了高高的谷仓,听见了久违的驴叫马嘶,嗅到了院里特有的畜粪微腥的气息
失学以后
失学以后
秋并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有些散漫,只酷爱数学而荒废了其他科目。老师对他已完全失望,所以,并不十分管教他。数学老师允许他上课不听讲,埋头做课外的难题。其他的老师似乎也似乎默认了他的这一癖好,对秋在下面做数学题也抱着同样的放任态度,并不加以制止。所以,秋每次考试时,除了数学,其他科目都不及格。秋也并不十分放在心上。如是,到了高三,秋才开始有了一些紧迫感,意识到了某种东西的必然来临。但他并未丝毫改变自己放任的习惯,只怀着留恋的心境过度着在校的每一天。他把自己的眷恋和爱投注到学校的每件事物上,如同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
经过种种努力,秋还是没能复读。他又回到了那片旷野上,满目的旷野,满目的季节,没有人,只有自己独立在时间的风中。秋只看到和感到一种东西,那就是时间,它的不可避免的来临和不可避免地过去。他不会停留在某处,它会走,把你留恋,热爱,不愿割舍的一切,变成不堪回首的过去。失学对于秋来说,与其说是某种际遇的改变,不如说是某种时空概念的改变,时空由静止的时空变成了变化的时空,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每一分钟都在分解,崩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