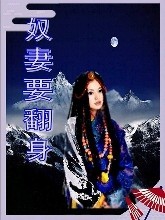沉重的肉身-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爱的男人Zuo爱。 这只是薇娥丽卡的生命感觉。个体热情有各种各样的散发形式,有的人喜欢玩体育,整天在体育场绕着圈子跑,丝毫不觉得枯燥;有的人喜欢整天在屋子里钻研故纸,一点不觉得闷;有的人喜欢养一大群孩子;有的人喜欢为一个逻辑命题翻来覆去地想……可是,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造化的偶然结果,造化并不可能依照个体灵魂的意愿来设计和造就这灵魂所需要的身体,因为个体灵魂是这一个身体在被造化的过程中才形成的。身体由自然的偶然造化决定,而身体的影子来自天堂的偶然,结果,一个人的身体和自己的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非常脆弱。如果一个想当运动员的人身体天生就好,能经得起专业性的强化训练,只是这个人的身体与自身的影子碰巧相合而已。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自己的身体体质不是那么碰巧吻合,一个身体被造作出来时,上帝并没有插手。寻求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平衡是个体生命的在世负担,这负担不是社会的任何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个体热情要得以实现,必须经过漫长的专业化训练,这是生命感觉的社会演化——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结果。专业化寻求一个人的身体与自己的影子的最佳平衡,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行为。但专业理性并不无条件地认可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中的个体灵魂,而是认可个体热情中的身体体质:运动员需要有超出想象的肌体,舞蹈家需要有恰到好处的体型,经济师需要有古灵精怪的智力,演奏家需要有纤长而又丰满的手指。如果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实现这一热情所要求的身体体质没有达到一致,专业训练的理性化制度就会拒绝让这个人接受专业训练。灵魂的价值偏好不可能训练出来,身体也不可能随意训练成个体灵魂所需要的样子,一切都取决于身体是否有刚好与个体灵魂相符的底子,而这种相符是过于偶然的事。如果我想当钢琴家,但手指五短三粗或瘦骨嶙峋,我再有多高的要当钢琴家的热情,音乐学院也不会要我。这就差不多等于宣判了我的个体热情的死刑,只有另外制造一个生命热情出来。 现代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完全开放了,个体热情的现实可能性无限制地增多,产生出无尽的可能性诱惑。但是,人的自然身体体质并没有随着个体灵魂的想象空间的扩大而增质。身体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理想,而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能够为每个人实现自己的个体热情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 在人民民主社会,个体的生命热情是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的决定了的,个体没有决定自己的个体热情的机会,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有一个由意识形态政党规定的国家热情或民族热情,人民伦理对个体的身体体质的要求并不苛刻。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设计是,要为千差万别的个体热情提供各种可能实现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如此个体伦理成为个体自由的民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开放了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因为个人幸福有个体灵魂差异,而且个体热情的想象一旦更少地受到社会条件的约束——自由社会为了个人幸福致力减少这样的约束,实现想象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可能性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性的否定的增加。可是,个体的生命热情遇到的在体性限制不仅是个体自由的制度设计无法克服的,而且在个体热情的偶在性开放之后更加显得是限制。个体自由的社会一方面在最大可能地减少个人的生命热情实现的社会条件的人为限制,另一方面却在增加无法解决的偶然的身体造化的欠缺。当某个幸福还是一个人不可想象的尤物时,这个人不会意识到自身获得这个幸福所欠缺的。人身的欠缺随着想象的增加而增加,个体幸福的偶在性的增长,必然导致个体的在世负担的加重。 薇娥丽卡天生有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可以上行到很高的音区,这是她可以进音乐学院的身体条件。不过,薇娥丽卡的身体并不适合唱歌,尤其不适合唱她喜欢的女高音咏叹调。咏叹调不单单需要甜润而又尖锐的嗓音,还需要足够的身体体积来支撑咏叹的气韵。薇娥丽卡的身体尽管漂亮得不可思议——应该丰满的地方毫不迟疑,应该精细的地方绝不吝惜,但对于唱咏叹调来说,确实过于单薄了。由于身体的单薄,薇娥丽卡在唱歌时常常感到中气不足,心脏负担格外沉重,而薇娥丽卡的心脏偏偏天生不好,承受力极弱,练唱时每每唱到高音区,就感到心力衰竭的晕眩。她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诉薇娥丽卡,她的心脏天生不适合唱歌,尤其是唱高音。 薇娥丽卡遇到的自己生命的在世负担,就是身体的单薄同唱歌的个体热情的不平衡。薇娥丽卡随身带着一根鞋带,练唱时拿在手里,一旦感到心力不支,两手就拼命朝两个方向拉这根鞋带,好像这鞋带就是系住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那根细线。生命热情与身体的体质之间出现的在体上的不平衡,令薇娥丽卡感到心里刻下了一道尖利的伤痛。 &
薇娥丽卡怎样体知自己的已死?
《迈向天堂之歌》是克拉科夫的作曲家Preissner用中世纪的旋律风格给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诗句谱写的一部女高音交响曲,独唱部分对歌手要求极高,有几个音符好像正向天堂那边飘逸而去,音区很高,又要保持甜润,不能干涩。薇娥丽卡很喜欢Pressner写的这部女高音交响曲,觉得这歌声就是自己的生命呼吸。她希望能担任独唱歌手,尽管自己的身体难以负担唱这只歌中的那几个高音符。 Preissner请薇娥丽卡去家里试唱。薇娥丽卡表现在高音区的音色令Preissner非常满意,他没有注意到,薇娥丽卡唱到那几个高音符的时候,正在拼命拉手上的鞋带。 《迈向天堂之歌》交响曲在克拉科夫一个中古时代的地窖式教堂里举行首演,当年异教徒——其实是异族——入侵,克拉科夫人为了保护自己集体的灵魂,把教堂建到地下去了。那天,Preissner亲自指挥首演,交响乐队的演奏十分投入,给薇娥丽卡伴唱的女中音和合唱队把迈向天堂的情氛铺展得很好。薇娥丽卡女妖一般的歌声美轮美奂,呼唤般地缓缓进入,正要启航驶向天堂。突然,薇娥丽卡的歌声像一只洁白的海雁被雷电击中,直直落入大海的波涛。 刚刚唱完那几个高音符,一阵突发的心绞痛令薇娥丽卡感到越来越不能有自己的身体,剎那间瘫倒在舞台上,死了。 为了那几个要命的高音符,薇娥丽卡耗尽了身体的心力。 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时,巴黎的薇娥丽卡正在那张“像剧院里的舞台”的大床上与男朋友Zuo爱。 身体在死,影子在生,或者影子在死,身体在生。 基斯洛夫斯基采取交互主体的电影叙事视角,来切入同一个身体的下葬和Zuo爱。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下葬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仰视镜头:躺在墓|穴中的薇娥丽卡用干涩的双眼看着一锹锹泥土覆盖在自己身上——我的身体正在被埋葬;巴黎的薇娥丽卡Zuo爱的场景用的是主观俯视镜头,躺在那张大床上的薇娥丽卡微闭着湿润的双眼,潜心感受一阵阵性感滋润的蔓延——我的身体正在进入生机的高潮。下葬泥土下落的干涩沙沙声与肌肤之欢中性感滋润的湿润呻吟准时切换,两个主观镜头联结了薇娥丽卡的两个身体感觉,基斯洛夫斯基充满质感地切入同一个身体对自身的死感。 下葬与Zuo爱连接的是生与死、性感与死感的迎面相撞,两个生存的本然对手的迎面相逢。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伦理思想是从探讨个体体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开始的。然而,尽管有不少大思想家为此费了好多脑筋,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结果是不了了之。据有的大思想家说,一个人只能通过预感自己的死或体察别人的死来感知自己的死;有的大思想家则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但预感自己的死——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预感的死——也还不是体知自己的已死。生感与死感不可能完全重迭,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中共在。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我所能体会到的至多是我在属于自己的个体生命时间中的向死(西美尔)或在死(海德格尔),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已死。只有我自己的身体才能体知自己的已死,而我已死的身体并没有体知这回事,我的身体感觉不可能是一个对已死的身体的感觉,因为已死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感觉。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令迄今的大思想家们在一个人如何体知自己的死感这一关键问题上无法移动半步:“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通过体察别人的死来体知自己的死,就更隔了一层。至于说一个人的在世处身情绪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死的感知,这种说法不可谓不高明,可是,个体化的处身情绪中的死感毕竟不是纯粹的已死感,而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在死情状有所了悟的生感。 为什么现代的大思想家们非要想搞清楚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搞清楚的属己的死感?按伊壁鸠鲁的那句话,自己的死感简直就是方的圆一类的语词组合。 现代人产生要直接了解自己的已死的愿望,是由于现代人的灵魂已经身体化—— 现代人的灵魂是自己身体的灵魂。在从前的人的生活感觉中,对自己的死并不是 那么身体化地敏感,因为个体的灵魂不在个体身上,或者说不在自己身体的灵魂 。从前的人的灵魂要么是智慧理性化的,要么是受宗法习俗支配的,总之是由超 个体的观念来支配的。个人灵魂的这种非身体化,正是为了抑制个人的身体感觉 ,让人的身体感觉不要过于敏感。伊壁鸠鲁甚至劝人有一种感觉的理性,它可以 调节各种身体感觉,使之不要过于敏感:“理性使我们如此完备地得到生命所能 得到的一切快乐,以致我们没有必要把永恒纳入我们的欲望之中。” 无论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观念还是由宗法习俗的观念来支配生命感觉,个体的死亡感觉都被非身体化了。个体生命的死与某个超个体的不死观念联结在一起,个体的死是超个体的宇宙、历史、天国、家族用来缝合个体偶在裂缝的针线。在宗法习俗的生命感觉中,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因宗教的来世承诺(天堂、轮回)而变得轻省——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们觉得,死后的生命更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归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这样的宏伟设想和超然想象。个体的现世生命的完结,恰是另一个更美妙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觉中,自己身体的死感则被智慧理性的现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鸠鲁是这样说的: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为这个缘故,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于人生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了解到终止生存并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 现代之后的人拒绝了智慧理性化的和宗法习俗的超个体灵魂,不让它们骗走自己的身体,不让它们管束身体的死感和性感,对死的惊惧感觉就随着个体灵魂的归来而身体化了。这当然是就近代启蒙的伦理感觉的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在个体灵魂还没有回到个体身上的地方,死感都还不是那么身体化地敏感。比如,人民民主的伦理国家用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来代替从前宗法习俗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个人的死感仍然还没有身体化地敏感起来,还没有变成觉醒了的个人身体感觉的尖锐穿透力。当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被理性化的世界设想和实证性的生命规划勾销以后,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就不再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而是由自己的身体单独来负担,一个人就不再可能明智地无视自己死后的虚无,个体身体的死就成了个体灵魂的在世重负。这样一来,认识自己的死,就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大要务,它决定了一个人与自己的个体热情的关系和自己身体的在世与他人的关系。 基斯洛夫斯基本来和昆德拉面临相同的困难: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去获得其身体的在体之感。解决了这一难题,就有可能解决一个人怎么可能体会到自己的已死这一难题。通过主观镜头的眼睛——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与巴黎的薇娥丽卡的眼睛的视界连结,薇娥丽卡的灵魂亲眼目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之死。就这样,基斯洛夫斯基潜入了薇娥丽卡的身体,去触摸她对自己已死的身体感觉,解决了二十世纪诸多大思想家一直没有能解答的难题:怎么体知自己的死。
薇娥丽卡性感的忧郁
在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中,个人自身的死感回到了自己身上,不再借居在身体之外的观念或智慧中。就在身体化的死感通过灵魂身体化回到个体人身上时,性感一同回到了个体人身上。当个人的身体在世是由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来负担的时候,个人的性感与死感一样不身体化地敏感。个人人身离开了超然世界的宏伟设想或宇宙性的智慧理性,个体灵魂才随个体人身的生成而生成,并开始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身体的爱欲。从前,不仅个体自己身体的死,而且自己身体的爱欲也是由宗教的来世承诺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