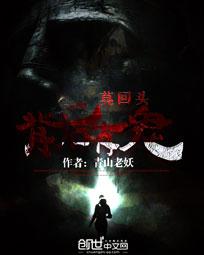月光的尽头-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填写领取人手机的时候,心月不免有些勉强,有一种隐私被强行征纳的感觉,却也无可奈何。
好在填完之后就没有别的事,心月客气地向幸淳道谢道别,就离开了工商局。
回到公司楼下时,心月意外地看见了郑琪。
看着他快步走近,她掩不住讶异:“你怎么在这儿?”
郑琪强捺着局促,望着她的眼睛:“今天我休息,可以等你一起吃晚饭吗?”
心月愣了一下,一时答不上来。
郑琪便又补了一句:“我在上海没什么朋友,我”
接下来他要说什么已经不重要,心月暗暗叹了口气:“约我吃饭的话,打电话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跑到这里来的。”
郑琪的紧张顿时缓和了许多:“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就过来逛逛。”
像是为了弥补什么,他赶紧催她:“你快去上班吧,我就在对街的茶餐厅等你,你不用着急,下班想去哪里吃饭,慢慢想好告诉我。”
心月回到电脑前,看见Skype上有欣悦的留言:“晚上我做三杯鸡哦,一起?”
心月抱歉:“郑琪约我吃晚饭,不然你跟我们一起?”
欣悦却之不及:“老大,电灯泡做半次就足够啦。”说罢又补充一句:“说实在的,这个郑琪师傅是不是你的追求者里条件最差的一个呀?”
心月本能地维护郑琪:“不要乱讲,他其实人很好。”
郑琪的确人很好,好到有时候竟不知如何表达他对她的好。譬如这天晚上吃饭时,他就忽然说了一句:“心月,我知道我没有江攸明好,但我肯定也不会有他那么坏。”
心月垂着眼,筷子慢了下来。
她和江攸明后来究竟出了什么事,其实她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高考的那两天,她神情恍惚,大家刚开始还以为她是太紧张或身体不适,直到高考后她成绩奇差被调剂到三本、以及江攸明突然出国的消息接踵而来,大家才自觉恍然——
原来江攸明抛弃了她,而且显然还很不地道地选在她高考前把这个消息告知,以至她惊痛交加之中考场失利。
对于这种推测,心月的不置一词被大家当作默认。
此刻听见郑琪这句话,心月依然没说什么,只提醒道:“郑琪,在我面前还是不要提那个人比较好。”
郑琪“哦”了一声,笨拙地道歉,脸上掠过一抹惆怅。
其实听见那句话,心月的触动并没有那么多,相比之下,她倒更感念于郑琪的痴心。那时他明明知道她和江攸明在一起,却还是爱她。
而她是怎么和江攸明在一起的呢?
很多事情,一直一直地拒绝再去想起,年深日久,自己也以为自己忘了,可如果真的去想,却发现脑子不过像是一台放久了未再开动的机器,只是少了清油的润滑,转得慢一点,并未坏掉,该有的功能都还有,该走的步骤,还是会一步一步走下来,好的坏的,想要的不想要的,都不会错过。
从辩论赛开始前一个月,到辩论赛开始后一个月,心月和江攸明日日相见,虽然大多数日子里每天的相处也不过是一个晚上而已,却因为强度太大而给人一种朝朝暮暮的错觉。在积少成多的接触次数与时间中,尽管江攸明还是那副不好接近的样子,几个人仍然不可避免地慢慢熟了起来。
刚开始被单独留下开小灶的时候,心月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些窃喜和兴奋,又忍不住紧张而沮丧。她觉得,江攸明这么做的意思,是认为她到底还是四个人当中水平最低的吧?
为了改变他的这种看法,又或者是为了让他自认留下她开小灶的决定着实英明,因而应当继续下去,她更加下功夫,每次讨论时脑子都转得更勤快,以便和他一对一的时候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和高水准的问题,让他知道她其实是比他所以为的还要有头脑有思想的女孩。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太过用功的缘故,有一天午睡起来,心月就觉得眼睛疼。刚开始还好,眨动转动的时候才疼,后来慢慢地,没有动作时也疼。到了晚饭之后与辩论队继续集训时,心月疼得连睁眼都困难了,直到这时才终于有个师姐发现了她的异样:“心月,你怎么了?”
心月尴尬地看了看停下讨论朝自己望过来的所有人:“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很疼。”
有个师兄凑过来仔细看了看她:“血丝很重耶,心月你好像小白兔,难道是红眼病?”
江攸明当机立断:“你们先自己讨论一下,再想想这个模拟辩题双方分别还有什么更好的思路,我带心月去医院。”
因为是附中,离大学校园很近,心月所在的中学并没有自己的医务室,师生们平常身体若有不适,只要不是大问题,就都是去的大学的校医院。江攸明拉着心月走到教室外面,叮嘱她:“把眼睛闭上,我牵着你走。”
心月听见自己狂烈得不像话的心跳,一下一下回音俨然地敲在胸口。她不敢不听他的话,依言闭上眼睛,可又担心自己看不见路会出洋相。极度的担心盖过了闭眼所带来的舒适感,她无法自持地又把眼睛睁开了。
江攸明很快察觉,低声责备她:“怎么?不信任我?”
没等她回答,他一把将她拽进怀里,一手紧紧搂着她的肩膀,另一手遮住她的眼睛:“放心,我不会让你摔跤的。”
心月身不由己地几乎是半挂在他身上,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她能从他紧紧贴着自己的紧张的肌肉中感到他很是用了几分力气,基本上是将她抱下去的。她慌乱地跟随着他的步伐,生怕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会令他误解自己不愿意这样,或太愿意这样。她的呼吸也高高悬在半空里动弹不得,原本心里那些只是规规矩矩按部就班的眷念,从这个夜晚开始,彻底乱了方寸。
她就这样方寸大乱地跟着他不知走了多久。他一直没有说话,她便也无从开口,这好像是因为他们俩之间的话题从来都只有辩论赛,而如今她身体有恙,再谈正事便嫌残忍,于是只好无话可说。
一股诡异的尴尬在他们俩之间绷张到极限,仿佛一条被两组正在较劲的拔河队员死死拉着的无辜的绳子。
拔河总有决胜负的时点,要么就是那条可怜的绳子被拉断。
而这个时点是在一个招呼声中来临的:“哟,明子,这小妹妹是?”
心月觉得自己的心都堵到了喉咙口,却听见江攸明嗤笑了一声:“打你的水去,少罗嗦!”
那男生果然不再追问,嘻嘻哈哈地走远,留下好几声高低不同的口哨。
接下来,又来了好几个打招呼的人,无不被江攸明毫无内容地打发了过去。
心月的心一上一下的,不知该当作何感想,却又不自量力地非要作出某种感想不可。
他不肯解释我是谁,是不便解释,还是我根本不够资格被解释?
好不容易周围的人声重新疏落下来,心月才听见江攸明说了一句有内容的话:“刚才经过我们宿舍楼下,好多人都刚吃完饭洗过澡,正准备去上课或者上自习。”
心月怔了一下,才敢确定他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
她想了想,有些不自信地顺着他的话问了一句:“那你晚上需要上课或者上自习吗?去指导我们会不会很耽误学习?”
这句话一出口,心月就懊悔得浑身发烫。她也未免表现得太嫩了!
生平第一次,她为自己开口闭口就提到学习而感到无地自容。
果然,江攸明似乎笑了一下:“不逃课的大学生不是真正的大学生。”
心月正没面子得想要推开他的手满地找洞,却听他又说了一句:“况且给你们辅导也是我的正事,你们校领导跟我们系主任打过招呼了的,没事。”
心月觉得宽慰而轻松了很多。
在校医院,医生翻开心月的眼皮看了一下,说是有些发炎,没什么大碍,很快地开了支诺氟沙星滴眼液。江攸明替她把药取了回来,当场就替她滴了一次。
这还是心月第一次滴眼药水,当看到一个异物迫近眼球,尽管知道是有益的眼药水,她还是条件反射地迅速闭上眼睛,脸上顿时滑开一道水凉。
江攸明的手指轻轻替她揩掉那滴眼药水。与心月心中战战兢兢的预期相反,他没有骂她,只体谅地道:“别怕,这药水滴进去会很清凉的,决不会疼。”
说着,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将她的一只眼睛撑开一点。
一旦同他发生碰触,心月就会无能为力地定身,而他冰凉的手指落在她发热的肌肤上,也有一种奇异的镇定效果。
于是,这一回,那滴眼药水准确地落在了她的眼睛里。
心月记住了水滴与眼球发生冲撞时的感觉,也记住了他专注望到她眼睛里的表情。
那一刻,心月心里无限失落:刚才师兄说我的眼睛红得像小白兔,一定是很丑的吧?一定不会再有那种两秒钟就能电倒一个人的效果。
为什么偏偏是在这种时候,和他靠得这么近、并且为他所凝注?
☆、6
那天晚上从校医院出来后,江攸明仍旧命令心月闭上眼睛,搂着她回到学校,并且直接将她送回宿舍。
而那支诺氟沙星滴眼液着实有效,心月当晚睡前又滴了一次,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就已经不疼了,可以照常上课,照常参加辩论队的集训。
辩论队组成的时候,心月的高一下学期才刚刚开始,到了比赛期间,已是春暖花开。
自从那个晚上之后,江攸明和心月再单独相处时,虽然很难说已成了朋友,却也亲近了许多,讨论的语气都轻松了一些。有一天江攸明对心月说的第一句话甚至与辩论赛无关,而是极其放松的一句:“心月,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很困。”
心月心里一跳,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句话似乎什么内容都没有,可又似乎有着一种什么话都比不上的亲密意味
她定了定神,才强作自然地笑答:“应该是因为春天来了吧。”
江攸明倒像来了精神:“噢?为什么?不是应该刚好反过来,春天来了人就精神抖擞起来的吗?”
心月赧然一笑:“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这样的说法,说春天里万物开始复苏生长,不免争夺空气中的养份,于是僧多肉少,就反而让人恹恹的没了精神。”
江攸明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唔,明白啦,有道理!”
心月很确定那并不是他们俩之间的第一次相视而笑,可之前种种的记忆就在这一笑之间统统被抹煞,她从此就记住了这一次,只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次。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又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天真烂漫,简直有几分孩子气,英俊得气势汹汹的脸上头一回没了逼人之势,只是一派单纯的快乐。
十几岁时的爱情,多么简单善感而易动。只是如此区区两件小事,就让心月对江攸明原本朦朦胧胧的感觉霎时间变得汹涌澎湃起来。
她开始无可抑制地想他,每分每秒,时时刻刻,如同歌里所唱的那样,每一道呼吸的气息里,每一次眨眼的瞬间里。白天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扰,思念变得艰难而坎坷,总是被分割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令她痛苦不堪,因而最幸福的时刻,是每晚躺在床上,入睡之前,心里满满的全是他,睡着之后,梦里就会见到他。
人在不关心某件东西的时候,就会几乎察觉不到关于这件东西的任何信息;而一旦开始关心,就会讶异地发现,原来满世界都充塞着有关它的一切!
譬如,在过去的十五年半里,心月从未听说过的一些事情,此时都一古脑蜂拥而来。她听说了如果你连续梦见一个人三次,就说明你爱上了这个人;但是很快又听说当你梦见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未必是你在想念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在想念你。
无论哪种说法是对的,无疑都是在证明和鼓励着心月的爱情。
然而太浓烈的思念总是夹杂着痛苦在里面的,事实上,最强烈的幸福也必须要有痛苦的辅助,有多大的痛,就能衬托出多大的幸福,令人珍惜得心碎的幸福。
例如,心月从未试过像现在这样盼望长大盼望得心焦,心焦到绝望。和所有暗恋的人一样,她不相信江攸明也会爱她,同时又担心他不会爱她,更担心他不会爱她是因为她太小,因为他等不及她长大。
而在更细微而具体的方面,她还为了每晚跟他道别之后又要等上整整一个白天才能再见而怅惘,更为了辩论赛结束之后或许就不再有机会常常见到他而心痛得快要死去。
这些忧愁全都与时间有关,于是在心月的思念里,时间像一把极钝的刀子,在她的肌肤上一下一下慢慢地锯。
因为这么痛苦,心月有时候就会想要少爱他一点,少想他一点。在张小娴的《流波上的舞》里,女主角曾经尝试在睡觉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以期找到一个不那么思念男主角的睡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
已经是被证明失败了的尝试,走投无路的心月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模仿,试图突破前人的失败。她甚至勇敢地在睡前将双手压在心口,据说这样就会做噩梦,而她先前也曾有过做噩梦的夜晚,醒来时的确发现自己的双手不知何时压在了胸前。
噩梦里总是充斥着鬼怪野兽,决不会有王子。
然而噩梦虽然如期而至,却依然是关于他。心月梦见和爸爸在机场候机,遇见了江攸明。他和一个娇小甜美的女孩在一起,同行的还有那女孩的父母,他是要前往岳父岳母家,和未婚妻举行婚礼。
那种如刀割般的痛,慢慢渗彻整个身体。
那是心月十五年多的生命中最为漫长、也是最为迅速的两个月。
两个月后,辩论赛结束,心月他们辩论队之摘取桂冠令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