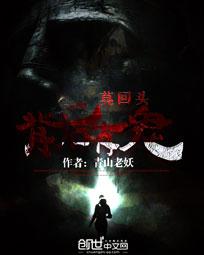月光的尽头-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那以后,每晚睡觉,他都会从心月身后轻拥住她,手掌小心地抚在她的肚子上,同她一起感受么么的一举一动。
这天半夜,心月再度被拱起的么么折腾得迷迷糊糊醒来。尚未来得及动弹,章允超已率先有了反应。他轻轻滑了下去,贴上她的腰侧,一边替她揉着肚子一边悄声道:“么么快回去,别这么顶妈妈,一会儿把妈妈吵醒了。要对妈妈好,不然等你出来看爸爸怎么收拾你!”
☆、42
虽然章允超说了这盆玫瑰是心月的花,要心月当花匠,可他还是出尔反尔地自己亲力亲为,每天都是他去浇花,心月只微笑地静静在一旁看。他们将它放在落地窗旁,早上阿姨把窗帘拉开,下午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呼吸到许多阳光。两日后的这天,阳光极好,气温也回升了一些,玫瑰的心情也就特别地好,一朵一朵大大小小地都开了。
而不久之后,就是中秋节了。
这是心月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虽然她早已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亲人可思念的。多伦多华人云集,这种传统佳节的气氛倒是浓厚。章允超让阿姨去唐人街买了各式口味的月饼回来,晚上也做了比平常更为丰盛的一顿晚餐。
饭后天已黑透,待月亮升上天幕,他们俩便穿上外套出去。月亮仿佛是随着他们的脚步一级一级攀至中天的,看起来小小一枚,像鸽子蛋的蛋黄。这附近并没什么高楼,所以估计在哪儿看都一样,没有参照,月亮总是小的。
心月忽然记起来,那次长途旅行回来的路上,开过一天夜车,他们在高速公路上看见旷野里的月亮,硕大如盘,极不真实,像是好莱坞做出来的布景。当时章允超还自嘲道:“这什么意思?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不知那是什么道理。
他们俩路过一张长椅时,章允超坐了下来,心月刚要坐在他旁边,却被他拉到腿上:“别凉着。”
他们俩默默无言地相拥而坐,看那些带着几个孩子几条狗的幸福家庭在跟前或笑或跳忽快忽慢地走过。
章允超忽然就开了口:“我心目中的幸福家庭,就是三个孩子两条狗。”
对于这个话题,心月不知如何回应,便顺着刚才在自己心里萦绕的对那次旅行的回忆说道:“那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要把世界上所有有意思的地方都走一走,还要把世界上所有好玩的地方都细细玩遍。”
她以为话题已被成功带开,不料章允超竟微笑着接过话茬:“好,你只管好好想要做什么,我来负责操心怎么去实现好了。”
心月又噎在了当场,他却越发从容地深入:“这样也好,不能两个人都只想过程嘛,不然就会变成无事忙穷劳碌;也不能两个人都只想结果,不然就会变成水中月镜中花,所以我们俩这样子,就是绝配!”
心月觉得这样的谈话自欺欺人得滑稽而气人,可却又管不住了自己,心里居然顺着两个人的话题,渺渺依依地升起《你的眼睛》里那些断断续续的歌词——
爱你,忘了苏醒,我情愿闭上眼睛
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浮不定
如果和他一起,带着三个孩子两条狗,把世界上所有有意思的地方都走一走、所有好玩的地方都细细玩遍,那是不是这世间最幸福的飘浮不定?
或者,如果真能如此,根本也就不是一种飘浮不定了,因为心里必是平安静好,而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啊。
想到这里,心月凛了一下,回过神来,不由苦苦地失了一笑。
已经不是白日了,怎么还会发白日梦?而如果你甚至不是我的今生,就算此生此世长睡在白日梦里不肯醒来,难道你又会是我的来生么?
那天晚上他们看了很久很久的月亮,直到夜气渐渐凉了下来,令章允超觉得心月不再抵受得住,才抱起她慢慢走回了家。
此时她的身子已然有些沉了。
秋意渐深的多伦多,常常整日整日地没有太阳。这个雪季开始的第一天,章允超早晨起来发现下雪了,便告诉了心月,于是心月再也睡不着,起床披衣下楼去。她先前一直在南方生活,下雪总是罕见,于是怎么也看不够,索性装样子地捧着本书坐在玫瑰旁的地毯上,看一会儿玫瑰,又看一会儿窗外静静的雪落。
那一刻突然有一种荒谬的错觉,觉得自己是个很幸福的小妻子。
她没有告诉章允超,其实她后来偷偷上网查过花语。花语说,粉色的玫瑰代表温柔的爱,白色的玫瑰代表高贵的爱。
然而她确信,章允超选这两种颜色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好看、她也会喜欢而已吧。
章允超轻悄地走过来,也坐在地毯上,紧贴着她,揽住她的肩,让她舒服地靠在他身上。他也望着落地窗前盛放在一大幅雪落图景前的玫瑰,声音愉快地憧憬:“等春天来了,院子里的雪都化净的时候,咱们把它种到土壤里去,那样或许它能活得长一些吧?也许能永远活下去呢?”
心月无以作答。她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要说这样的话,关于未来,甚至是关于与永远有关的未来。他那天就说过要把玫瑰种成一片森林,如今竟真的提到了“永远”这个词。
可他拿什么来跟她说“永远”?
而且,春天来临的时候,她应该也已经不在这里了。预产期是十二月份,她想不出在生下么么之后,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个所谓的家里。
然而对于章允超的所有这些不着边际的提议,她既不能苟同,却也不知如何,无法出言反驳。她慢慢地想起为什么那天收到玫瑰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冒出“除了你,不会再有人这么爱我”那样荒唐的念头,那是小女生的浅薄与虚荣,只因为他毕竟是唯一一个送过玫瑰给她的男人。心月始终是那种令人感到难以企及的女孩,即便后来有人忍不住豁出去表白,却也只是一种卑微的尝试,不敢倾尽全力抛出所有赌注去痛痛快快争取一番,只因为笃定自己只有一败涂地的结局。
而心月就难免因此而觉得自己其实不过是那种普普通通不大起眼的女生,所以不大有人追。
可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那个唯一送她玫瑰的人会一辈子给她送玫瑰,只给她送玫瑰,她也就不比那些有许多人追的女生更不幸福,不是吗?
雪季一旦开始,便日日地总要下一会儿雪,再没停过。对这样的景致,心月每每倚在窗前,怎么也看不够。每天早晨,院子里堆着的雪往往高过台阶,木篱上也积着都是。有一只松鼠是章宅的常客,秋天时它积极贴膘,将自己养成了只大胖子,然而才到这会儿就已经迅速苗条下来,而每当它从木篱上走过,院子里就会下一阵小雪。
这让心月想起《冰河世纪》里的那只松鼠,暗笑原来编剧安排一只松鼠来引发一切剧烈的地壳运动是颇有事实根据的情节啊。她将相机备在手边,每看到任何让自己觉得有趣的事物便会拍下来,想着将来可以带着么么看图说话,给她讲她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所看到过却不能记得的这趣味无穷的点点滴滴。
孕妇的记性果然很差,这个念头每次冒起,心月都会黯然失落地意识到那一天根本就不会来,而这样天天记录下一些不能给别人看、将来于自己而言也是不堪回首的往昔,又是何苦?可每一个下一次来临,她就又会忘记,兴奋地抄起手边的相机追捉那些奇妙的瞬间,然后落落的醒悟周而复始。
十一月下旬的这几日,天气突然回暖,屋顶上的积雪融化滴落,于是屋檐下垂挂起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冰凌。章允超一早就打电话找工人来清除,岂料此时有此需要的人家实在太多,而且毕竟是西方国家,本来人就少,工人的维权意识还颇强,决不肯加班,所以连找了好几家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需两三日以后才能派得出人手来。
于是章允超每天都要叮嘱心月好几次,趁着天气好每天出门透透气没问题,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先把门推开,确定没有坠落物之后,再快一点出去,以免被坠落的冰刺砸到。同样的叮嘱当然还要耳提面命地交代给阿姨,因为他不在家的时候,陪心月出门的任务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这样过了几天,也都平安无事,还没等到工人来,连日暖阳就把上一轮积雪化净了。然而紧接着又一轮积雪卷土重来,甚至益发来势汹汹,一夜之间爽爽快快将一切恢复原状,而由于气温骤降,冰凌倒是不见了。
于是大家都认为,前几天的危险已经解除了。
这天早晨,章允超带心月去医院产检。此时她已满了36周,产检的频率上升至每周一次,无论天气多么恶劣。
刚推门出来,章允超猛然惊觉有什么极为不对的动静近在耳边。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目眦俱裂地发现一具半人大小的雪块从屋顶上飞扑直下,正正朝着心月的头顶!
他大吼一声,连忙搂住心月闪到一旁,将将与那团落雪擦肩而过,只听匝地有声,惊心动魄!
然而雪一直在下,刚刚扫过的廊前此时又薄薄地覆上了一层雪末,最是溜滑。两个人虽然都穿着防滑的靴子,奈何刚才章允超的闪避动作太急切太不计后果,又因为搀着心月而重心不稳,避开雪块的同时就要往地上滑倒——
偏偏此时,心月发现第二团沉重的雪块朝着章允超凌空击来!
她什么也来不及想,尖厉地大叫一声“允超”,就奋力把他推向一边。刚刚看他离开危险地带,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觉得头上猛一记钝痛,眼前呼啦啦黑了下来。
然后是冰凉,劈头盖脸的冰凉,比兜头挨了一桶冷水还要坚硬而刺骨得多。这冰凉唤醒并锐化了她的所有知觉,她渐渐感到自己正坐在一个硬邦邦的什物上——是地面吗?臀骨痛得刺心,髋骨也震得又痛又麻,不过这一切都无法与另一个地方的疼痛相比——
肚子痛好痛!好痛!!
心月觉得自己全身的神经和细胞都在声嘶力竭地挣扎,可同样痛得发麻的脑子里嗡嗡的什么也听不见,于是也无法判断自己有没有喊出声来。腿间似乎有温热的液体缓缓淌出,浓重的腥味升腾到冰冷的空气里。
她感到自己被用力搂在一个怀里,有人手忙脚乱地拨开留在她头上和身上的什么残块,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操着变了调破了音的英语状若疯狂地叫救护车。她使了半天劲才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却朦朦胧胧的什么也看不清,彻骨的疲累迅速涌来,迫她重新合上眼帘,向昏睡投降。然而腹部不断传来的剧痛令她无法完全睡熟,她渺渺茫茫地记起——么么、么么、么么
不,么么!!!
我的孩子,千万不能有事啊!!!
心月庆幸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人是和她同心同德的。当她感觉世界摇摇晃晃地笼入一片略带汽油和药水味的温暖时,她听见有一个声音在野兽般地咆哮:“母亲必须没事,孩子也必须保住!”
他反来复去地将这句话怒吼着强调了好几遍之后,声音突然软弱而滞涩下来:“孩子也必须保住,否则我还拿什么来把她留在我身边”
☆、43
几个月来心月一直勤于运动,再加上毕竟年轻,以及后来摔的那一跤所带来的剧烈震动,她才刚被推入产房孩子就生下来了。
万幸,母女平安!
由于心月还需治疗头部遭受雪块击打的伤,她比一般的产妇多住了几天院。不过她恢复得还算快,产后次日的晚上就被奶水胀醒,可以自己喂么么了。
心月无法描述将这小小的人儿抱在胸前喂她吃奶时的那种感觉。她怎么也看不够女儿张大柔软的小嘴尽力含住她整个奶…头的样子,刚刚还睁着眼皱着脸愤怒抗议着饥饿的表情迅速被安抚,还原成一枚玲珑粉嫩的鹅蛋,眼睛闭成两条平滑的长弧,腮帮子和小脖子一耸一耸地美美吞咽,小得近乎半透明的手掌宣示所有权般地抱着她的半爿胸脯,那种这世上最亲密的相连相依的感觉,令她直恨不能将自己的整颗心也化作奶汁喂入她小小的身体里去。
章允超告诉心月,么么一出生就睁着和妈妈一样又大又亮的眼睛,一脸水灵灵的聪明样儿,一根拇指放在嘴巴里一个劲地吮,一副吃不够的小馋猫相。虽然只是这么简单的描述,心月却怎么也听不腻,总是央他多讲几遍,再多讲几遍,更恨自己当时不能清醒着亲眼看到这么难能可贵的一幕。
章允超也抱歉且无奈:“谁想得到你会突然出事早产?本来都打算好了你生么么那天我会带着DV去拍的。”
这句话让心月重新默然。拍那个做什么?将来给谁看?
每次护士抱着么么来给心月喂奶,都要循例问一句:“你姓什么?”
这是核对的意思,以免抱错了孩子,虽然她笃定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她和么么身上,且不说这到底是白人产妇更多的医院,纯黄种的孩子很难被认错,光说她的么么一出生就肖似父母的漂亮轮廓与五官,就不太可能同大多数还难看得很的婴儿混淆。
不过既然有问,就要有答。心月总是很诚恳地回答:“Jiang。”
婴儿名牌上的姓氏写的是“Zhang”,不过在加拿大人听来,这两个字的发音非常接近,以为是同一个姓,所以从未出过问题。然而这天忽然换了个华裔护士,是懂中文的,听了心月的回答就觉得不对,凑过来一看心月床头的名牌,所写的姓氏果然同婴儿的姓氏不一样。
护士莫名了一会儿,忽然恍然大悟:“你结婚了吗?”
心月顿时尴尬。
北美女人多数婚后会改随夫姓,一家人都是同一个姓氏,所以每次出现这种母亲和孩子不同姓的情况,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母亲是个单身妈妈。
不幸的是,虽然对于绝大多数华人——尤其是新移民家庭来说并非如此,可心月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