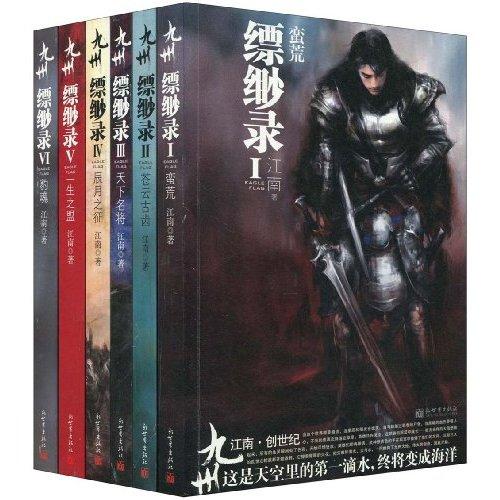九州·缥缈录 iv-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轻声说:“我们这样的人,太卑贱。就算是死了,也不会被人记住,活在这乱世里,都是多余的。公主是千金之体,很多人都关心你的,要和关心你的人多说话。”
“别了。”她转身出门,瞬息不见。
姬野慢慢地睁开眼睛,下午的阳光很温暖,从门窗透进来,极远的地方,有人击鼓报时。他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午睡刚刚醒来。他在半梦半醒的时候听见身边沙沙地响,他睁眼看见一身宽袍的女人坐在他的床边,咬着线头,正在缝补。
阳光太耀眼,他看不清女人的脸。但是他觉得很安心,闭上眼睛想要再睡一会儿。
门外有人走动,沙沙的脚步声。
姬野再次睁开眼睛说:“我很害怕,门外有很多人。”
女人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指尖挠着他的头皮,像是梳子刮过那样,让他觉得麻麻的很舒服。可他还是害怕,他看不清门外那些人的样子,可他觉得那些人每一次经过门口,都把鬼祟的目光投进来。
女人低低地哼出一首歌儿哄他睡觉,姬野不懂她的歌词,可是她的声音让人安心。姬野蜷缩起来偎依在她身边,闻着女人身上衣服洗干净的皂荚味,他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了一只小小的老鼠,蜷得极小,躲在女人宽袍下。
那是一个全世界人都找不到他的地方。
门外走动的那些人开始低声说话了,他们三三五五地聚成一团,悄声议论,他们偶尔把冷冷的目光投向这边。姬野躲在女人宽懊下,可是他依然能够感觉到。
“我很派他,他们有很多人。”姬野再次说。
“外面从来都有很多人,”女人安安静静地说,“你却只有你自己,要自己活下去。每个人都一样的啊。”
“那你呢?”姬野抓着女人的袍角。
“我和你在一起。永远都在一起。”女人说。
“为什么?你说每个人都只有自己。”
“我不同,你是我的一切。”女人这么说着,轻快地唱着歌儿,“生下来是小老鼠,迎风长成男子汉”
歌声悠扬,姬野觉得自己的心又安静下来了。这种感觉真的好啊,有个人,你是她的一切。她会为你做任何事,保护你,爱你,不论回报,也无需理由,不管何时何地。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们不需要寻找也不需要相逢,她和你之间的联系是世界诞生的时候注定的规律,永远都在一起
无需理由。
“我能看一下你的脸么?”姬野怯生生地问,“我总也看不到。”
女人笑着:“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只要你想看”
女人把姬野抱了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坐着,轻轻把面前垂下的长发理开。姬野看到她的脸了,她的脸色苍白,笑容温暖,眼睛里缓缓流下两行鲜血。她是枯槁的,没有任何生气,眼睛里空无一物,唯有那笑容,像是刻画在嘴边的,从不改变分毫。
姬野想起来了,她死了。
“你能喊我一声么?”女人说。
姬野点了点头,他太久不喊她了,于是在心里悄悄地喊了两声练习。而后他轻声说:“妈妈”
女人僵硬的脸忽然变得生动起来,她双眼流下的血流得更快了,像是泪水,她的笑容绽开了,那么美丽。姬野很高兴,因为他觉得女人很高兴。他想多亏我先在心里练习了两下,要不然叫得不好,妈妈便会很失望。
他把头缩在女人的怀里。他感觉不到女人的体温,所以他努力地贴近女人要让她觉得暖和。他想把自己的体温分个她,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儿子和母亲生来就是一起的,他是她的一切,这是从他哇哇诞生那一刻起被注定的规律。
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怕屋外的那些人。
而屋外的那些人似乎愤怒了。他们在墙壁上捶打,他们开始吼叫,他们绕着屋子急跑,带起呼呼的风声,他们变幻出狰狞的各种形象,要冲进来。可是他们没能得逞,温暖的阳光在这间屋子里,外面的人无可奈何。
姬野从宽袍下把头探出来,他忽然发现原来阳光不是来自外面,阳光来自母亲的身体里。她的身体冰冷,却透着温暖的金色阳光。姬野欣喜得要手舞足蹈,可他发现女人在迅速衰朽着,她还在缝补,可她的身体迅速地干瘪下去,她就要变做一具干枯的骨骸。
姬野用力贴着女人,他想那是因为她没有体温,所以她变得消瘦了。只要有体温,她还会好起来。
女人轻轻摸着他的头:“所以,最后你依然只有你自己,因为我会死去啊。”
她说得很平静,可姬野忍不住大哭起来。他想是啊,她已经死了,所以世上只剩我一个人。
屋外的那些人还在狂奔,他们弄出的声音太大了,简直像是天地都要被他们的脚步震塌似的。整个屋子摇摇欲坠了,女人还在不停地枯朽下去,她身上的光芒正在黯淡,她的时间所剩无多。屋外的人发出即将成功的狂笑。
姬野站了起来,用尽全部力量对着门怒吼,他不再是小老鼠,他变成了一只被激怒的凶兽!
息辕已经在这座城市里转了很久了。他去了每一面的城门,城门禁闭着,城墙很高,没有任何办法逃出去。城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屋宇兵道,也没有河流,只有一堆巨木燃烧在城的中央,火焰永不增减。
息辕想大概有十几年过去了吧,也许更长。这里永远是黑夜,分不清时间。
真是孤独。
息辕想要有个人跟他说说话。他已经试着翻筋斗和倒立,可是很快这些也都没意思了。他无奈地围绕火堆转圈子,试着唱家乡的歌。可是无论他怎么唱,那歌都是一样的——
“天黑黑,要下雨。”
下雨了怎么办?这里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息辕忽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巨大的恐惧感包围着他,难道就是这样了?在这里直到永远永远?
“谁来救救我啊?”息辕放声大喊。
“你叫息辕么?”忽然间,息衍一袭黑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是。”
“跟我走吧!”息衍向他伸出了手,坚定有力,没有一丝颤动。
息辕盯着那只手看,那手的拇指上套着铁青色的指套,上面飞鹰的徽记栩栩如生。他缓缓地伸出手,在空中停了一瞬,而后紧紧握住了息衍的手!
七
数千里之外,宁州,古老森林的深处。
少女凝视着皇极经天仪的旋转,用炭笔迅速地记录在纸卷上。她脚下已经堆满了纸卷,密密麻麻都是从入夜开始写下的数据。她的老师却只是袖手在那里仰望,并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破军和贪狼开始出现半掩。”
“巨门的光度增加了,它的光度已经达到了‘角’不,已经达到了‘晴’。”
“禄存的光度也开始增加。”
“现在武曲和廉贞的轨道重合好,符合计算的结果再次分开。”
少女笔录的同时,不断报出北辰七颗主星的变化,老师听了微微地点头。
“别念了,记记就好。”老师忽然说,“如果你对比这些数据,会发现和以往北辰之相暴涨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作为星相师,笔录还是应该的。”
少女沉默了一会儿:“我是很想检验我测算的成果。”
“孩子,你的算学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好的,超过了我自己。测算北辰之相暴涨对你根本就不是难题,为什么你还是那么急于验证结果呢?那么不自信么?”
“因为始终觉得离星辰算学的最终完美还有距离,所以不断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来增强自信吧?”
“最终完美?”老师笑笑,“你确认最终的完美存在么?”
“就像您描述的谷玄七式的七道方程那样吧?最终的完美该是简单而圆满的,就像是一个圆,没有任何一处是它的破绽。”
“我说了圆心是它的破绽。”老师说。
“可圆心并非圆的一部分。”
“圆心是圆的一部分,”老师的语意高深莫测,“因为失去了它,圆周便失去了一切的依凭而不复存在。所以每个圆必然和它的圆心是一体,而那个心,便是它的破绽。”
“我还是不懂。”
“你太执着了。”
“也许。”少女低下头。
“北辰之弦的涨满我看看,”老师简单地扫视时轮,那是记录精密时间的庞大仪器,“大约该有三刻四分一厘的时间。想不想知道谷玄之弦何时涨满?”
“何时?”少女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知道老师是可以计算出谷玄之弦的人,因为他手中握有那七道方程。
“就是刚才,”老师笑了起来,“它的高涨略早于北辰,现在死亡星辰已经把它的力量播撒到大地的每个角落了,不过绝大多数人不会觉察。”
“您验证了计算的结果么?”少女问。
“没法验证,”老师笑笑,“谷玄仅仅存在于方程里,因为那是个死亡的点,吸纳一切的光,不能观察,也就没法验证。”
“半掩结束,贪狼和破军的亮度都在急剧增加。”少女看着天空。
“嗯,”老师赞叹中带着点儿调侃,“北辰之神求战心切。”
“求战?”少女问。
“这对星辰自古以来的力量之弦涨跌几乎是重合的,所以有人猜测它们是一对双生子星辰,也有人猜测它们是一对死敌。不过这次看起来北辰七颗主星冲距离谷玄极近,已经入侵了谷玄的防卫,所以倒像是这两组星辰的一次对抗。”老师说,“不过有以战争对抗死亡的么?”
“这大概属于辰月大师们热爱的话题吧?他们热爱哲学。”少女淡淡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热爱。”
“那老师思索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少女一边问着,一边不停地笔录,她的勤奋和老师的懒散对比太大了。
“得到的唯一结果是所谓的哲学都是人闲极无聊时的瞎扯,世界最终的意义和人有什么关系?”
“嗯?”少女愣了。
“比如,有人说神创造这世界是为战场,武士们总是高喊这句话拼死搏斗,以为这样就算明白了世间纷争的道理。”老师露出嘲弄的笑容,“可他们不明白,这句话是对的,他们的理解却是错的。”
“那么正解是什么呢?”
“神创造这世界是为战场,但是这战场并非留给凡俗的我们,这战场是神为自己预备的。星空诸神们终将亲自搏杀,要在这片战场上决出他们自己的未来!”老师低声说,“这一切和我们本无什么关系。”
少女并不理解老师这番话,却隐隐有些被打动,愣在那里思索。
“时间到了!”老师回头看了一眼时轮,“北辰和谷玄的对冲开始!”
八
吕归尘扑了出去!
他忽然握到了他的刀,只一瞬间,他的刀已在手中。刀柄粗糙的摩擦感如此真实。
他冲了出去,压住他的那人再也无法制约他的力量。力量在这个孩子的身体里盘旋、咆哮、驰骋,像是海水涨潮那样贯注到他身体的每个角落。他的身体在狮子般的前扑中飞速生长,那双柔软的手上暴起筋结,细瘦的胳膊上肌肉虬结,背肌收缩的时候像是帆船上拉帆的棕榄被绷紧,他的双眼暴睁,如同滴血。
“这才对!”他在心里咆哮,“这才对!”
刀上光如满月,向着那些男人的后颈斩落!
盗贼们射出了无数的箭。
古月衣在箭雨中抬起头,看着黑夜里星星点点的铁光像是一阵飞扑而来的蝗虫。李长根似乎要大笑,而他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看见古月衣握到了弓。
很多年以后,就是这个年轻的骑射手在看了战友和平民的死后绝望了,在李长根满足了自己血腥的欲望之后满意地离开镇子的广场时,那个年轻人疯子一样从难以发现的茅屋夹缝里冲了出来,把他唯一的一支箭投向了李长根留着血腥味道的大嘴。
古月衣抬起头,开弓:“我可以杀你一次!我还可以再杀你一次!”
息辕被叔叔拉了起来。
忽然他发现自己的面前并没有叔叔,他站在尚未点着的巨木堆前,身后是五百精锐。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他的手中是叔叔的剑,古剑静都。息衍叮嘱过他,任何时候,不要放开剑柄。
姬野慢慢地张开眼睛。
他的喉咙微微动了动:“原来是我自己怕看你的脸啊,看到了,我才会想起你已经死了”
这是一场蛊惑人心的大梦,所有人在同一瞬间醒来。他们面对着身边长鸣的武器,这些武器如同愤怒一样剧烈地震动着。古月衣抓着长弓追翼,忽然有些明白为何白毅要把自己的弓郑重地交给他。
这是楔子,刺穿无穷的掩盖,让人看向自己心底最黑暗的地方。
什么是最可怕的事?不是丧尸,也不是死亡,最可怕的事是站在自己心里最深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那是每个人心底深处的鬼魅,吸取记忆而存活,却又被强行封印在记忆的底层,不让它露头。可是它不能被杀死,也许可能被战胜。
喊杀声铺天盖地而来,醒来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息衍佩着侄儿的剑,袖手在另一处据点的巨木堆前,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差不多了吧?都该醒来了。”
丧尸已经突破了火门的外城。他们无可阻挡,只要一具丧尸爬上城墙,它就会占领那一片,十几个军士无法击退它。后面的丧尸却还在不停地往上攀爬,城墙无处不是他们的进攻方位,根本无从调兵防御。
冈无畏站在瓮城的城墙上,看着外城上仅剩的军士们绝望地以长枪戳在丧尸的身上,可那很难起作用,丧尸们僵硬的肌肉锁住了枪尖,普通军士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无法刺穿丧尸的心脏。战死军士的鲜血把城头染得鲜红,丧尸们因为感觉到了鲜血的气息而格外疯狂。
“军人终要为国靖难。”他面无表情地挥手,“不必管剩下的人了,投掷火油罐!”一百名遴选出来的大力军士在瓮城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