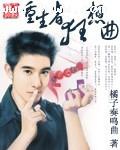天鹅奏鸣曲-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瞬间的沮丧,他很快转过了身子,把酒杯放在方向盘旁边。
“我明白。”他的语气中并没什么变化,“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不过我还是想试试,我甚至努力过。”
“所以你抓了雷蒙得·戴斯先生。”他对我的“善意表示”也以伤害到别人为前提吗?
“我只是不想让您第三次进警察局。”这个纳粹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过分,“得给盖世太保足够大的甜头才能保住您。相信我,我很清楚您在干什么,‘天鹅肉’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饵料。”
“我并不会跟您说谢谢。”
他苦笑了一下:“我没指望这个。”
我端着酒杯,冷静地看着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丝颤动。在灰暗的月色中,我能感觉出今天晚上的少校在我面前呈现出了另一种面貌;这种面貌正可以与我接触到资料划上等号--一个缺乏感情爱护的人,他的脆弱可以变成乖戾阴险的武器,尖锐地伤害别人和自己。
我几乎要怜悯他了
另一种寂静在车厢里蔓延,这时少校的嘴角微微地抽搐起来:
“我说了别这么看着我!”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夺过我手里的杯子扔到外面,随着玻璃清脆的碎裂声,我被这股力量牢牢地定在了座位上。
一张端正的脸猛地凑到我面前,我这才意识到他的上半身几乎都贴了过来,有力的双手扣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呼吸变得粗重,似乎在压抑着暴怒的情绪。即使背着月光,我也能清楚地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些疯狂的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一切那我就是不折不扣的白痴--
“你对我有欲望吗?”
话音刚落,肩上的手掌一下子加重了力道,像是在证实我的猜测。
我反而在下一刻平静了:“假如前两次是你故意戏弄我,那这次又算什么?”我直直地看着他,“我也是男人,不要以为我会一直把你的动作当作是玩笑。”
肩膀上传来剧烈的疼痛,我的骨头似乎快碎了。他恼羞成怒了吗?不,我可不认为他是一个有那么强烈的羞耻心的人!
波特曼少校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声音:“我该说你聪明,还是迟钝呢?你如果装作不知道或许更好。”
“是您教会我坦白地直面危险,而且如果我装傻,只是令您不那么尴尬罢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处。”
在蓝色眸子里燃烧的黑色火焰仿佛激烈地跳跃着,仿佛在竭力挣扎,终于渐渐熄灭,我肩上的力道也一点一点地撤离。
少校慢慢坐直了身子,凝视着我:“您的确变成熟了许多,伯爵大人。您现在能寻找到最好的方式消磨对手的意志来保护自己,但是您必须知道,我是个固执的人。”
“这很疯狂,而且我并不欣赏。”
“我不在乎。”他挑高了眉毛,“我从来都不在乎。”
这张年轻英俊的脸上又有了我熟悉的那种倨傲和玩世不恭。我心里很清楚,或许他压根没把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看得有多不得了,他只是拼命得在填满空虚的欲望,不仅仅是肉体应该是借助肉体来渴求心灵。
可惜他选错了对象。我既然能正面接下他的挑战,那么我必然不会让他得逞,这是意志上又一场新的较量--
“好了,伯爵大人。”我身边这个男人很快戴上了他惯有的面具,烦躁地把香槟扔出车窗,“不管怎么样谢谢您今晚陪我。大概也快天亮了,我得把您送回去。”
车轮碾过芳香的玻璃碎片离开了河边,一路上我们没再说话。直到汽车开进塞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我远远地望见了门前挂着的一盏灯。
“好了,就在这里停下吧。”我低声说,“别让马达声惊动我母亲。”
少校很配合地熄了火。我伸手推开门,他却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臂。
“有句话我得告诉你,夏尔特--无论你相不相信,害死吉埃德小姐的人不是我”
客厅里亮着光线微弱的壁灯。
我移动着僵硬的腿来到沙发前,叫醒倒在上面睡着了的多利奥小姐。我尽力使她相信我没事之后,吩咐她不能把今晚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母亲。她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向我做了保证。
把这个善良的老妇人劝回了房间,我才乏力地坐下来。
我无法漠视分别时少校说的那句话,他真正想告诉我什么我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不过我不愿意去想得太深刻。因为我有了一种新的念头,这样的念头甚至让我自己害怕。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尝试,否则就会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不认为少校还会像今天一样在我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既然挑明了他的目的,我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听见古老的大座钟滴答作响,不时地敲几下提醒我。等它连着响了六下的时候,窗外弥漫着淡淡的雾气,薄霜已经凝结在了玻璃上。
我站起来,伸了伸腰--我必须把自己整理好,别让母亲看出我一夜没睡,否则麻烦就大了。所以大约七点她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装作和平时差不多的模样在客厅里喝着牛奶。
“早上好,妈妈。”
“早上好,亲爱的。”她温暖的嘴唇吻了吻我的额头,“你没看报纸,在想什么呢?”
“一个小问题。”我亲昵地搀扶着她向餐厅走去,“主要是关于人性中的善恶倾向?”
“有什么高见吗,我的哲学家?”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可不可能让一个坏人变好。”
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手:“相信我,孩子,不要简单地说一个人是‘坏人’或者‘好人’。你要明白即使是杀人犯也疼爱过自己的孩子,帮助过邻居;反过来即使是有名的慈善家也会因为商业上的考虑让别人破产。要是我,就不会用简单的字眼儿去判定‘人’。”
她睿智的蓝眼睛让我觉得心底更加明朗:“这就是父亲会不顾祖父反对和您结婚的原因吗?”
“或许吧。”她的脸上浮起幸福的神色。
“有您在我身边真好。”我由衷地感谢上帝。
母亲的话是对的。不光是人,所有的事情也一样。
因为波特曼少校暗地里的动作,瓦尔叶泰剧院的刺杀案件被嫁祸到了戴斯先生的身上。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让盖世太保相信他的鬼话,但处决戴斯先生的罪名中确实有“策划并实施对柏林特派员及高级警督的谋杀”这一项。
是的,处决。他们残忍地砍下了那位出版商的头。
我好像安全了,可这是在戴斯先生的生命庇护下才成功的。虽然我明白是波特曼少校导演这一切,为的是卖我一个顺水人情,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将无法摆脱内疚的感觉。
“你大可不必为此难过。”事后他曾经打过电话给我,“事实上单凭《巨人》的事他已经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与其再牺牲一个人,他独自承担了更好。况且我向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
波特曼少校用一种聊天似的口气跟我说到,我仿佛能看到他脸上不以为然的神情。就他而言,只要是他不关心的事情都可以当成垃圾。
于是在1941年深秋时节弥漫了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稍稍消退了一些。我和朋友们的剧团在德国人的监督下重新恢复了正常运作。
“天鹅”的行动也在开始复苏。
我一直担心戴斯先生遇害和我的安然脱险会让行动组的成员产生疑虑。因为莫名其妙地接受一个纳粹的帮助是件蹊跷的事情。我知道解释是没有用的,唯一的用处是越描越黑。好在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因为我的同事们信任我,当我告诉他们我有些新的想法时,他们还像以前一样参与了计划与讨论。
“转化?”弗郎索瓦首先觉得不妥,“先生,您说转化一个党卫军?”
“是这样。”我耐心地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他转化成我们的帮手。”
“那太冒险了!”戴西摇了摇头,美丽的卷发甩出大大的波浪,“成功与否先不必说,如果他有背叛的意思,那我们反而会处于最危险的情况中。”
“当然得考虑到这些。”我明白他们的担心,“可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德国人内部有一只眼睛那将多么方便。几个星期后我们将接应三个英国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勒阿弗尔,如果有党卫军少校的帮忙,在通过沿途关卡的时候会安全得多。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露旺索他们行动时的危险性。”
“这是事实。”弗郎索瓦有些赞同,“不过,先生,您怎么能让一个纳粹军官来帮助他的敌人呢?”
“首先他和其他的狂热分子不一样,他心里对他们的元首没有起码的尊敬,他把战争当作是一场报复游戏而不是为争夺什么‘日尔曼人的生存空间’。这点我敢肯定!至于怎么说服他我很难跟你们说清楚,但是我有把握。”
“太冒险了。”
“那这样吧。”我知道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试试。如果在英国人来之前我能说服他,咱们就多一份胜算。”
我年轻的同事互相望了望,终于郑重地点点头。
天鹅奏鸣曲(十四)
或许是有些疯狂,但是却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把自己投入了一场赌博,而筹码是包括了五条生命以外更多的东西。我在刀尖上的舞蹈越来越绚烂了,我没办法控制内心的变得愈加茁壮的蔓藤,或许它最终会把我拉到不可知的未来,我却不打算放手。
因为现在的波特曼少校在我的眼睛里像一幅看不懂的现代派油画,众多的色彩把他弄得有些奇怪。当那个残忍的刽子手在我的面前逐渐转过身时,我惊讶地发现他那边的脸居然千创百孔这样我便不能把他简单地毁掉,更何况从他身上我还有些急需探听的事情。
于是在五天以后,我生平第一次向自己最恨的人发出了邀请。
“或许您愿意在白天和我到蒙玛特高地上去喝杯咖啡,少校。”我在电话中跟他说,“这比夜晚更有情调,您能把这当作一次必要的‘回礼’吗?”
他在那头低声笑了,口气中带着往常的揶揄:“您的邀请方式还真不客气,伯爵大人。看来我没道理不去咯?”
“那么明天下午三点,我会在‘风信子’那儿等你。”
“一定准时到。”
初冬的空气中已经有了迫人的寒流,加上不景气的世情,即使在白天这一排精致的咖啡馆也是冷冷清清的。客人们大部分呆在室内,所以临街的露天座椅上空着许多位子,一眼望过去没几个人。
我独自在“风信子”外面品尝着比以前苦涩了很多的咖啡,熟识的老板有些内疚地对我说:“糖和牛奶都非常短缺,伯爵大人,您也明白”
我宽容地向一脸歉意的中年男人笑了笑,告诉他这没什么,我觉得很可口。战争的恶果一贯是由人民来承担的,但无论如何也必须坚韧地活下去。在一年前我或许根本没有想到生活圈子以外的东西,甚至曾经调侃过法国人的肤浅和过分浪漫,对可现在我发现自己的同胞其实远比我想象得要坚强和可爱。
我婉言拒绝了老板“入内就坐”的邀请,因为我害怕那个人如果穿着一身德国军服出现的话会在人群中制造出惊人的效果;可能连我背上都会被鄙视和痛恨的目光烧出个洞吧。
所以当我远远看见他那身朴素的便服时,隐隐约约有些高兴。
“刚好三点,一分不差。”我打开怀表,“德国人果然很守时。”
“哦,这是个好习惯。”波特曼少校在我对面坐下来,叫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
他破天荒地没戴帽子,任那头金发蓬松地垂落在额角,身上也只是简单地套上了暗青色的西装和白色的长裤,除了衬衫领口露出的花色方巾,几乎没有一点显眼的地方。可我知道即使如此仍有些女士用暧昧的目光注视着他,这个人就像个发光体,不管怎样都会让人注目。
而波特曼少校看着我的神情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那么自然,仿佛几天前深夜里的突然来访是我的幻觉。
“能接到您的邀请还真是荣幸啊,伯爵先生,能告诉我您打算和我谈什么吗?”他倒是非常直接。
我微微坐正了身子:“您还记得四天前说过的话吗?”
“酒精不是个好东西,我象是说了不少话。”
“你说,害死玛瑞莎的人不是你”
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烟,点燃。
“别告诉我你忘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在送我到家的时候,你亲口告诉我的。”
“对。”他承认了,但是眼睛里却渗出了一点点狡黠的光彩,“不过,伯爵大人,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件狠毒的事,是您一口咬定我是凶手啊!”
“我在玛瑞莎身上发现了你的头发!她紧紧地攥在手里!”
“那又怎么样?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金发吗?”
“但在世界上和我有过不快的金发男人只有你一个,更何况你从来没有辩白过!”
“您在那样的状态下会相信我说的吗?”
心脏因为他的话突然膨胀起来,我提高声音:“你保证过会救出玛瑞莎,你有这个能力!在看守所里谁敢对一个少校特别关注的犯人下手!能伤害她的,除了你还有谁?”
少校的脸色有些难看,仿佛要发怒,但是却硬生生地忍了下来,柔软的烟卷在指间扭曲成三段。
“真是严厉的审判啊,伯爵大人。”他把烟扔在地上,“这么说您到底还是不相信我。”
“如果不相信你,我们还有可能坐在这儿吗?”
“那么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掏出纸币压在杯子底下:“愿意和我走走吗?”
穿过了乔治五世路和巴塞诺路,又从加里略路、上林苑和普里斯堡路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