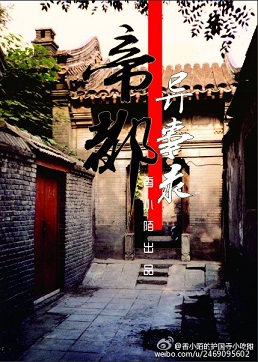雍容帝都一锅粥(轻松,年下,党争)作者:汤桥-第5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人连连声讨,要他赔钱。
就这时,冼清一下子从椅子上摔到地上。
“你小子,凳子都坐不稳!怎么回事?”张简笑道。
冼清没回话,只是晃晃悠悠站起来看着不远处。
那里站着一个男子,一身火红的官服,剑眉星目,身后有一抹淡淡的晚霞。
张简刚想张口说话,却被身后的人一拉,萧华衣将食指摆在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下。
草地上,小树下,鲜花渐渐长出了花骨朵。
小小的屎壳郎蹲守在这片花园,希望总有一天它能看到。
若干年后。
深夜,卿云阁。
张简咬着一块芝麻饼,不满道:“你教会他雀牌,助他在福建立功,给他介绍朋友,现在还要给他做挡箭牌?”
“什么挡箭牌?”冼清看着萧华衣道:“八八,你说我像挡箭牌么?”
萧华衣道:“我觉得,既是太子殿下让他做的,你就不要插手了。”
薛靖赞同道:“这么多年,殿下一直提拔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殿下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可不能就这样躲着。”
“他也没躲着!”冼清道:“就是我想替他把事情办了。”
萧华衣喝了口水,淡淡道:“不行。”
“为什么?”
“殿下抱恙,宫里的其他太医都信不过,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殿下的病怎么办?”
冼清摆手笑道:“我怎么会有事?这事情我有十足把握!”
“再有把握也不比整个都察院弹劾来的强。”薛靖道:“冯荣现在是言观统领,上弹章是分内之事,就算皇上没折腾四皇子党,他也不吃亏,反而能够树立威信。
再说了,早就有风声传出来,四皇子党已经把矛头对准他了。”
“他要能拉着言官跟他们斗上一斗,都算赢不了,也能名垂千古!”
“千古名声能吃么?!”冼清撇撇嘴:“我就希望他能能平平安安的,每天都快快乐乐,不要卷进是非之中。”
“为官的,不卷入是非是不可能的。”萧华衣道:“你这样一味护着他,别说殿下不高兴,就是对他也不好。”
“他在这里待了那么些年,却还是不懂官场规矩,人人都喜欢他,可不是人人都愿意帮他。他这样直来直去的,早晚要捅娄子。”
“就是!”张简脚一翘:“阿城说,第一次见到比我还不会做官的!”
“少跟我提你家那卖酱菜的!”冼清道:“他第一眼见到毛茸茸就说他要吃大苦,这人也太不会说话了!”
萧华衣伸手往他脑袋上点了一下:“我就觉得他说得对!”
冼清瘪着嘴巴,道:“我知道二殿下跑了,现在四殿下正红火,有些针对我们了,太子殿下不过是想自保。”
“可我觉得这事儿让都察院出面都没用,毕竟殿下已失宠于皇上。我想着反正殿下仍旧是太子,万一皇上要驾崩了,殿下就是”
张简立刻蹦起来,伸手去捂他的嘴巴,小声提醒:“你活腻了么?”
冼清挣扎地掰开他的手:“我只是有主意了。”
薛靖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什么主意?”
“下药。”冼清道:“与其被他折腾死不如先下手为强!”
“打住!”萧华衣突然道:“这事不许再提。”
“我已经跟殿下提了!”
“他怎么说?”
冼清笑道:“他没说话。”
大家都沉默了。
没说话,就是不反对。
冼清道:“对付四皇子党的事我也有办法,你们就别操心了。”
萧华衣看着他,问:“有办法和能办到不是一回儿事,你确定你一个人就能对付他们?”
冼清笑了:“有时候一个人就够了。”
很快,天德帝身患怪病,时不时口吐鲜血吓倒一群内侍。
而柳家大公子是断袖的事情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许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人,开始猜测他的断袖对象,并纷纷把矛头指向四皇子党。
四皇子党渐渐有了焦头烂额之势。
帝都局势一下子乱了起来。
冯荣打开奏折,却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他知道一切的真相,却无法全盘托出,只因他是个太子党。
他突然奇怪,在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权力,斗争和仕途。
就连曾经那个善良的人也不例外。
为了打击四皇子党,他不惜出卖信任他的朋友,灌他酒套他话。并对君王下毒。
这个帝都,真是越来越不像儿时梦中的样子了。
他无意中注意到那个被伤害的人,他原本是那么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样子,对谁都好,而现在脸上却藏着深深地忧郁。
他还记得,他当初去顺天府找张简,那人刚挨了骂,水头丧气地趴到一旁的桌子上,可等他从张简那里出来,却见他乐呵呵地分着梅菜饼,还蹦过来打招呼。
他还记得,那天下起了雨,他没带伞,便躲在一旁的屋檐下。那人下班看见便把自己的伞给了他,说是自己的小仆一会儿就来接他,让他先走。
他还记得,在那个孤寂而清冷的黄昏,他孤零零地在玉轩宫外头的花园里徘徊,像个被人揭露了坏事忐忑不安的孩子。
他终于忍不住,拨开树间重重地枝桠,走了过去。
很快,有人说,断袖怎么了?太子党的冯总宪也是个断袖啊!
太子气得药都喝不下,冼清对着水榭一旁的湖水无奈一笑,手中丢出一把鱼食,沉沉地坠入水中。
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
黄鹂爱上了水中的锦鲤,日日贴着水面飞翔。
一个黑黝黝的身躯躲在一株雏菊的后头,风中有股咸咸的失望。
天德十四年,冯荣为太子伸冤而获罪流放云南。
民众夹道送行,有个人站在低矮的小楼下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果然,即便是替了你做了一切,依然救不了你。
很多年后,伊人归来,依旧是兄弟,却生生得觉出了隔阂。
冼太医再一次倒下,专业人士郭柄吓傻了眼。
原先他昏迷,他因为知道是假的,所以没一点担心。可现在是扎扎实实地饿晕了,他却慌了手脚,镇定下来之后哆哆嗦嗦喊人煮粥。
冯尚书在礼部翻公文,听到了这个消息,冷冷一哼,把公文拿起贴着脸不理来人。
萧华衣轻轻一笑:“呆子,东西拿反了!”
冯尚书不吱声。
萧人精靠在门背上,道:“他待你可比待我们好得多,巴不得替你把往后的路都铺齐了,你就算没一丁点儿喜欢,也得心存感恩不是?”
冯荣:“我怕我一直虔诚感恩着,他却一个人醒过来到处乱跑。”
萧人精眼睛也不眨:“就是因为给你的诚心感动,他的病才好了呀!”
他正说着,陆曼凌从一旁侧身走出,拉着他就走——
“算了,你吹牛,还不如人家柳闻烨呢!”
萧华衣:“”
礼部尚书办公室,公文乱七八糟堆着,冯荣却没有再看的心思。
在福建,他觉得这个人善良,又孤孤单单,总是一个人猫在角落里吃素菜,可怜兮兮的,又待人真诚。
在帝都,他觉得他不拘小节,虽然总是一副从鸡窝里钻出来的样子,却毫不掩盖他的可爱。
党争时,他恨他不择手段,无父无君,出卖朋友。
再后来,他病了,像死去了一般,他却觉得自己的心狠狠地痛了一下。
伤心,果然是骗不了人的。
他每天都抽空去看他,虽然做不了什么,却觉得能这样陪着就好。
有时他看到他的手动了一下,便欣喜万分,以为他会醒来。
那时他天天想着,他要是能醒过来,他把那些往事都忘了,从此,只记他的好。
可结果
哼!——
冯尚书的办公室里想起了摔笔筒的声音。
一大群下属偷偷贴着门听,却不再有任何响动。
太医院。
冼清还是醒了过来,当然,他是饿醒的。
这些天,他先是被饿昏,而后被饿醒,真不知道是不是天谴。
不过他刚睁开眼睛,就又立马闭上了。
有个人正坐在一旁的桌子上,拿着两个杯子,反复把一点茶水倒来倒去。
冼清开始思考要不要醒来。
毕竟上次就是因为自己装病才把他给气跑的。
但是现在醒来,会不会
也许他只是来看两眼,走个过场,以示兄弟义气。
其实他也知道,冯家在南方也是个大家族,冯家世袭千户,他爹又官至总兵。
而他自己,别说相貌平平出奇邋遢,还是个孤儿,要不是郭柄当初在麻麻山上捡了他,他现在就在阎王殿里磨药了!
他们之间差了那么大一截,还都是男人,什么人约黄昏白头偕老,都是扯淡。
虽然他嘴上不依不饶说是一定要把人娶回家,可心里却明白,不过是吼两句,过过瘾罢了。
他想要的,只是希望那人能多在他的世界停留,哪怕那段停留只有一个回头。
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被紧紧握住,那感觉,就像很多年前,在福建的堤坝上,他在风中握住他的手。
那么紧,让他不惧风雨。
冼太医睁开了一只眼睛,看着冯尚书道:“你往后还能这么一直拉我的手么?”
冯尚书点头:“嗯。”
冼太医睁开了另一只眼睛,突然嚎啕大哭:“呜呜呜!——你知不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啊!——呜呜呜!——”
冼太医抓住冯尚书的手,一脸激动:“荣荣,快给我弄只烧□!再不吃,我们就天人永隔了!”
冯尚书看着自己的手,面无表情道:“以你这种力道,是不会天人永隔的。”
冼太医连连摇头:“荣荣,我是想吃饱了就顺便入个洞房,这样你就不会跑啦!你放心我会很小心,不会让你疼的。”
冯荣嘴角抽搐地看着他:“你你会很小心?”
“嗯!”冼太医连连点头:“我有药,你喝了顶多过一个时辰就没事了!绝不耽误你明天上朝!”
他话音还没落,眼前就只剩下了一团空气。
却听见冼太医不死心地朝门口大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荣荣!”
却见外头依旧没有声音。
冼太医渐渐屈服了,只能委屈道:“那就给我带个烧□我们来日方长”
可过了很久,门口只剩下风的声音。
冼太医叹了口气,果然还是太心急,给吓跑了。
却见门外砸来一个东西,落到床上,冼太医打开纸包,呵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烧鸡会有的,洞房也会有的!
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小屎壳郎正在一片叶子下休息。
却觉得身后有了一阵响动。
回过头,却见小黄鹂站在那里,嘴巴上叼着一根小枯枝,递了过来。
小屎壳郎思考了半天才发现小黄鹂想让他爬上去,于是擦了擦手脚,慢慢地爬到了枯枝上。
于是它看到了蓝天,白云,和近在咫尺的树冠。
在小枯枝上,他学会了飞翔。
从此,透明的天空下,总会有一只黄鹂叼着一只枯木在飞翔。
枯木上趴着一个小小的屎壳郎,手紧紧抓着枯木的一边,他那小小的身子随着风轻轻摆动。
我为你造了一座城堡,本以为那里没有我,却不想那个小小的“我”和那个高高在上的“你”,已经变成了“我们”。
第七十章 【番外】独白(上)
我记忆的最初始,是一缕淡淡淡淡的香味,那是母亲特有的香味。
而我眼中所看到的第一抹色彩,却是沉默的黑。
那是我所在的偏宫的屋顶。
我的偏宫没有人,只有一个小小的我,有时会有宫女太监进来洒扫或是送饭,可也只是那么一瞬。
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有一个乳娘。但是没多久她也走了,因为给我这种孩子喂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宫女,她在生下我后没多久便死了。
我之所以能留在这里,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地方的主人,人们说他聪敏而果敢,博爱而温和。
但是这个博爱而温和地父亲,却从没有来看过我。
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断奶太早,生了肠胃病,哭闹不停,宫女这才把我送到太医院,并告诉他我的存在。
我依旧没有见到他。
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是应该很疼自己的儿子的,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孤单,永远都是一个人,听着宫女和太监谈论着外头的事情,心中麻木。
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早已和我无关了。
人们说,他们的圣上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并不是他的儿子。
就因为我不是他的孩子,我的母亲成了一个罪人,而我便是证据。
他之所以留下我,也许是为了留下一个嘲笑我母亲的证据,或是因为心中的那一点点怜悯。
也许我还要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而感激他呢!
我喜欢在偏宫一旁的花圃里挖土,用一根小树枝,挖啊挖,这样很快一天就能过去。
有个老嬷嬷跟一个太监说,我比蚯蚓还厉害。
我总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时我还以为,我生来就是在这里待着,然后和老嬷嬷一样白发苍苍。
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到来。
这个人来的时候没有一点响动,就像偶尔在墙头探脑袋的虎纹花猫。
他蹲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堆黄土挖到一旁,又把它们填进洞里。
其实我早就看到他了,可我不想理他。
我在这里寂寞惯了,越来越讨厌和人说话。
以前,每当我想拉个宫女或是太监说话,他们总是像蹭到墙上的灰一般厌恶地逃走。
从此,我不再和人说话。
那人突然伸手把我手里的小树枝抢走,扔在一旁,淡淡道:“殿下,想不想去见见您的母亲?”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话用敬语,而且他对我说——
母亲。
在这个宫里,我的母亲是个禁忌,没有人会说,更没有人会提到他。
我看着这个人,他是个中年人,个子不是很高,眼睛仿佛藏了秘密,手掌上密布着纹路,满是岁月的痕迹,却那么温暖。
他牵着我的手,带着我从小道离开,来到一个树林子里。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