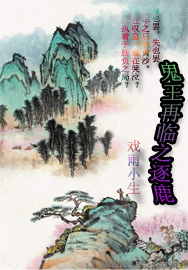惊雷逐鹿 作者:金龙鱼-第3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适时推行,此为军国大事,断不可轻忽视之,故须尽快与独孤岳面谈。
至于莺羽黄之事,他即或判断有所错谬,在他也是无关紧要事,何劳挂心哉?一笑带过可矣,对此自是丝毫不以为意!
这一夜,独孤岳别业的会客花厅上席开两桌,场面虽嫌简省,便也权当是给雷瑾一行接风洗尘了。独孤岳亦是知道雷瑾不喜繁文缛节的脾性,再则又是秘密莅临,不宜铺张,所以索性只按寻常家宴的规格摆酒设席,也不分什么男席、女席,料雷瑾必不在意的。
花厅之中,这会儿已是十分的酒酣耳热。
“圆纠纠紫葡萄闸得恁俏,红晕晕香疤儿因甚烧?扑簌簌珠泪儿腮边吊。青丝发,系你臂,汗巾儿,束你腰。密匝匝相思也,淡淡的丢开了”
调丝弄弦,独孤岳府上的家班女乐,十来个清秀女孩儿或坐或站,在六扇屏风前箫管琵琶齐奏,琴瑟笙笛合鸣,编钟悠扬,牙拍轻敲,家伎口中浅吟低唱的并不是士人们雅好的昆腔南曲,而是时下的市井小调《桂枝儿》,如今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的俚俗曲子。
这倒也正合刻下的宴饮气氛,若是吟唱昆腔南曲,反而很不搭调,扦格不通了。
烹羊宰牛且为乐,席上酒水,金华酒、惠泉酒、血珀葡萄、荔枝绿、水井坊、剑南烧春、泸州大曲等应有尽有。席间男男女女,吃酒之人,各取所好,只求尽意痛饮,放浪形骸,不论尊卑男女,都拿出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劲头,饮如长鲸吸百川,不使金樽空对月,彼此言笑甚欢。
在座的除雷瑾、独孤岳之外,尚有‘执政同知’雷水平、驻成都的骑兵军团节度阿顾,独孤岳的正室钱氏夫人和侍妾王氏、张氏,还有栖云凝清、倪法胜、凝霜亦同在这一桌,其他人则合共另外一桌。
世宦大户之家的旧俗风习,是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内宅女眷向例是不令与外客见面的,家中但有外客到访,家中女眷即须回避。
反过来,主人若令家中女眷出见外客,往往包含着‘你我之间并非外人’的一层意思。若非主客之间的关系确实相当亲厚,就是主人以此来暗示客人,他对来客非常重视,彼此间的交情非其他人可比!
当今天下,风俗以奢靡为上,礼崩而乐坏,仍然严格遵守这等旧俗风习,完全规行矩步的人早已不多。即便是如此,过于放肆的蔑视礼法,仍然足以令人侧目,招致恶评。
独孤岳如此设宴,便是因为这在座的几位确实与他都关系匪浅,不比寻常外人。然而,以这花厅中在座诸人的身份地位而言,在酒宴上如此的不论尊卑男女,共桌宴饮,若被外间一干道学儒生知悉,怕是又要口诛笔伐一番,恨不能以道德杀人了。
独孤岳回头看看花厅中各色空酒坛子,未及搬出去的,竟是满满当当码起了两层,不禁笑道:“侯爷果是海量,卑职怕是难于奉陪到底了。”
雷瑾不由大笑,转而低声说道:“论喝酒啊,先生却是差些。嘿嘿,要想纵横花丛无碍,这喝酒上也得有些本事才行。小子当年狂荡荒唐度日,尽日纵鹰放犬走马射猎,又在风月渊薮中行走厮混,名声虽是不佳,这酒量上却是练出了几分本事不假。”
说罢竟是喟叹一声:“昔时种种,犹在目前,却是此生再难寻回当时当日之肆意情怀也。”
独孤岳不禁默然,谁无青春年少头角峥嵘的岁月啊,干将发硎,鹰隼试翼,肆意挥霍,弹铗狂歌,豪饮达旦,快意恩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气吞万里如虎!都是一般的锋芒毕露,豪情万丈,算而今年华老去,无复少年狂,忆往昔峥嵘岁月,几缕惆怅生。
心念至此,独孤岳也便是一声感慨:“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射杀山中白额虎,步行夺得胡马骑,少年不识愁滋味!如今却道,天凉好个秋!”
陪坐一旁的雷水平呵呵大笑,端起甜白瓷酒杯,一口饮尽杯中的‘泸州大曲’,接口说道:“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独孤大人正当盛年,何出此言?”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阿顾虽是回回,却亦曾进学,遂笑说道:“末将粗陋,只依稀记得东坡翁最后这句豪气干云。”
雷瑾哈哈大笑,随口评点道:“独孤先生似有几分‘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的感慨呢。嘿嘿,‘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阿顾的豪情壮志,倒是恰与先生‘天凉好个秋’一呼一应,莫非天意乎?”
“呵呵,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人老即不以筋骨为事,谈不上什么感慨喏。阅尽沧桑后,处之自淡然,再无什么可抱怨可烦恼之事,灭却心头火自凉,便是好个秋。”独孤岳说着端起酒杯,笑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阿顾将军赶上了好时候,今秋射猎定可大获成功,满载而归斯可预期。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老夫在这里预为之贺,来!满饮此杯。”
“阿弥陀佛,独孤先生已通禅机,菩提妙心,佛果可证,善哉!”倪法胜嫣然笑道。
这厢阿顾忙起身回敬独孤岳一杯酒,推杯换盏,一通儿热闹。
雷瑾亦笑道:“此秋非彼秋,天凉好个秋。‘赫赫我车,一月三捷’,今秋射猎,若能凯旋,便是借得独孤先生今日吉言也,大家满饮此杯!”
说着径自举杯汩汩饮尽,席上众人亦陪饮一杯。
雷瑾放下酒杯,对独孤岳道:“先生的建言,卓识深远,小子揣摩于心,亦以为然。只是先生的手折中,屡屡提及四川执政府右参议何健,先生有以教我乎?”
独孤岳拱拱手,说道:“右参议何健,乙榜举人,籍贯四川叙州府,系留用的前巡抚衙门僚佐。此人在洪氏幕府中,职掌钱粮出入。洪正任浙江藩司(即布政司)左参政时,何健以乙榜举人的出身任职浙江督粮道,少年得志,时人视为仕途异数,后终以‘贪酷’免官回乡,永不叙用。到洪正主政四川时,才延入幕府,为洪正麾下重要幕僚之一。
何参议在洪氏幕僚中以任事见长,谋划献策却是不多见。倒是留用之后,他在实务上多有建言献策,卑职衔命执政四川,能得今日之治绩,何参议与有力焉。其人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尚属可用之才。
奖掖贤能,荐举人才,卑职职责所在,分所应当,故尔不惮烦琐,向侯爷荐举此人。
此次析分陕西、四川的提议,即为何参议倡议,卑职亦曾在官署与同知大人、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会议商讨,但兹事体大,故卑职仅以个人名义上手折建言,以供侯爷参酌。
另外,‘邮驿合并’暨‘革新邮政’事,大要纲目虽是刘长史、蒙长史以及卑职等人反覆商榷敲定,但其中亦有何参议最初条陈献策之功,至于一应规条、施行方案的草拟亦经其手,卑职不过稍事润色而已,蒙长史自认此事上他着力不多,不愿掠美贪功,所以呈禀到侯爷处,只有卑职和刘长史的联署。蒙长史固是不愿掠美,何参议之功卑职却不能隐匿而不报。”
“哦?”雷瑾眉尖一耸,“这何健在洪氏幕府为何谋划献策不多?倒是留用之后,便茅塞顿开了吗?”
“这——”独孤岳没想到雷瑾会问出这样一句话来,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知道雷瑾这位侯爷阅人历事已多,用人任事自有一定之规,对僚属贤能与否、事理原委,无不博访周咨,平日默识于心,不大宣之于口,却是以备他日用人任事之时参酌决定。而且随着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举凡相貌、言语、举止、呈文、行事、待人等等,俱在眼目之中。僚属的才能优劣、品性脾气,等等,平日即已展开不动声色的内查外调,对多方面的情况加以参互质证,比对核实,对僚属的才能品德考察结论,总是在不断的评估、修正、完善,因之这种详实缜密的甄别考察,绝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惯例的考核、考绩、考成等官方正式程式。
稍作思忖,独孤岳笑道:“卑职推测,是因前巡抚洪正本人颇有谋算,且为人多少有些刚愎自用,较少向幕僚讨教机宜,故而何参议谋划献策较少,便也不难理解了。”
“这样么?”雷瑾目光炯炯,悠然一笑:“四川官属僚佐,小子自不如先生熟悉。此番南来,倒要见上一见。这何参议既是才能卓异,大可不必在乎其品性上的瑕疵,不过——本侯先得见上一见,异日任用其人,才能心中有底。”
独孤岳一听,便知自己的荐举已经得到雷瑾大体上的认可,顿时大感宽慰。但也了然雷瑾在酒宴上说起此事的用意,这事儿便无形中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诚所谓‘臣不密,失其身’,但凡是这酒席上谈及的政务,尤其是与这何参议有关之事,若是提前泄露出去,他可吃罪匪轻。今晚这酒宴一散,就得饬令家人守口如瓶才是。
想到这里,独孤岳便朗声大笑,说道:“侯爷即有此意,不如明日造访何氏府上?侯爷意下如何?”
“呵呵,”雷瑾颔首一笑,“先生但去安排,小子无不从命。”
“那就如此了。”
独孤岳说到这儿,想起一事,又道:“锄奸营的谍情通报说,近期因为侯爷南下四川,各方秘谍纷至沓来,云集成都。其中还说到京师司设监宦官张玉私入四川,已露踪迹,锄奸营正加派人手比对追查。如此形势,侯爷出入还要多加小心才是。”
“司设监的张玉?他来四川干什么?”
雷瑾皱了皱眉头。以张玉的中官身分,若非奉旨入川,雷瑾这等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真要想名正言顺的对付他,抓住张玉这一条私自离京的罪状已经足够。
毕竟宦官不奉旨而私自出京是犯了皇朝大忌的,皇朝太祖太宗时所立的祖制,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谁胆敢公然的违逆,虽则天下早已呈现瓦解之势,但究竟还是皇甫家坐着龙庭不是?
张玉身为内廷宦官私自出京,潜入四川,定当小心隐藏不为人知才是,这么容易就暴露了形藏,必是其中有诈。
张玉身为畸门高手,并非仅只武技高明而已,自是有些不为人知的绝活,可资隐藏和保命;何况其人久处宫廷权争漩涡,不会不知自保全身是第一要义。这宦官私自出京,变易形貌以避人耳目,应是一般而言的常识,凭张玉的出身、阅历、武技修为,哪里是那么容易被锄奸营发现踪迹的?
“这事有些蹊跷,”雷瑾说道,“怕就怕,他是蓄意暴露形藏,以自身作饵,吸引锄奸营的注意,从而掩护暗中进行的诡谋。张玉此人来历非同一般,锄奸营不要被他蒙蔽了。告诉锄奸营,要他们特别注意这点。另外,铁血营要加强警卫,注意防范可能针对执政府重要僚属的袭击、刺杀。大家伙出入都要小心了。”
独孤岳微微点头,“侯爷说的极是,这事卑职今晚就交代布置下去。”
“那就好。来,满饮此杯!”
雷瑾举杯,座中诸人齐声应诺,花厅中一片笑语喧阗。
玉河水静,桨声灯影里,一条官船悠悠滑过水面,荡起涟漪。
国朝初年,蜀王府宫城修建时,挖土筑城,高垫地基,隆然居于成都重城的中心,又疏导开挖环绕宫城的河沟,广设明渠暗沟以宣泄大雨洪水,使宫城之内免受洪涝之害。
环绕蜀王府宫城,外通金河,内连摩诃池的河沟,由于河面甚宽,建造宫城时,可以船只来往运送木料砖瓦。王府既成,王府生活所需之物,亦可由船只运入,民间俗称为玉(御)河。
这一条官船,就是给蜀王府运送柴炭、蔬果、牛羊猪肉、活鸡活鸭等生活必需品的船只之一,每晚三更开始,由金河转入玉河,最后驶入蜀王府宫城卸货交割,第二天一早再由执政府指定的专人,点算清楚,逐一按品秩分发给王府上下主仆人等。
官船驶过水道转弯处,船工都专注于划桨、使橹、操舵,根本没有察觉一个窈窕人影从官船上纵身飞起,宛如大鸟腾空,无声无息地横越水面,跃到岸上,借着夜色掩护,贴着墙根奔行,迅快无比的闪入一条街巷。
黑影忽动忽停,如同一缕轻风,七拐八弯之后闪入一条巷子。
前无去路,但一侧高墙底下有一道门户,想是这户人家平时出入的小门。
黑影闪到门边,倏然潜入,原来紧合的门扉只是虚掩而已,门后是一个小小的后花园,山石嶙峋,花木扶疏,点点流萤映照,显得影影绰绰,宛如鬼怪,蛙声虫鸣的细碎合奏则因了黑影的进入,打乱了原有的节奏。
“拿到了吗?”
在突兀奇异的假山石后,一个低沉沧桑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是男人的嗓音,年纪不会太年轻。
“拿到了。”
自外而入的黑影答道,软媚轻柔,自是女子无疑,显然黑暗中问话的声音是女子所熟知,丝毫不显惊诧。
“后面没人跟着吧?”
“我搭顺风船进的城,不会有人跟在后面的,放心啦,我江湖上的字号可不是白叫的。”女子似乎很有把握,“哦,你肯定那人会来么?”
黑暗中的男人回答:
“以那人的脾性,我的举动迟早会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来了,你拿到的东西,就是他的阎王催命符。如果他不来,那只能说他命不该绝,气数未尽。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能以后再找机会。这次你从汉中南来,正是八方风雨汇聚成都的时候,又赶上了眼下这档子事,正要借重你的本事。诗经有云‘远客来矣,维风及雨’,或许真能一击得中亦未可知。”
“不要信心太足,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女子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道。
“好啦,不说这些了。把东西给我。”
男子在黑暗中说到,并没有察觉女子的异常。
在黑暗中接过女子递过的物事,男子又道:“你先歇息吧,我从地道过去那边院子。”
“真的要致那人于死地吗?”女子在黑暗中问道。
男子稍稍停顿了一下,“你怎么了?此人一身系军国之重,最适宜偷袭暗杀,一旦身死,军心必乱,其手下乌合之众肯定作鸟兽散。哦,对了,刚好得了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