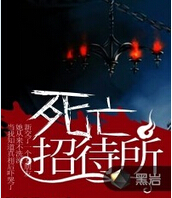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3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ͷ��Ŀѣ�����˳��������������֮�С�
�������������ˣ�Ҳ�������Ϊ�����������ĸۿڳ��У����ų����εĻ�������ͷ����ͷ��ͣ���Ż������洬����ͷ������һƬ���������dz�����ɫ���̴���һ������һ����һ��С���Ӹ�����˿�����档�����ǿ�����ֹ���ڵķ�����ʱ���ֿ�������һĻ����һ�л�ͣ����ͷ����ͷ���вֿ⡢���߸˺�·�ơ���һ�ж�������������ͬ��
������������ͧ������עĿ��ʻ���˸ۿڣ����Dz��ڻ�������ͷǰ���ص������ȴû�п����������ĵ����ķ������Աߣ���һ������ˮ�Ϸɻ����أ���ֻ�ɴ���������������ǵ���ǰ�����������˴����ɿ���ƿ�������ͣ����խ��·�ϵ�����������ж�³��صĿڴ������ǣ�Լ��ѷ˵�������Ǵ���������Ь�����������ˡ��ϵ���Ǯ�к���������һЩ�������Ż�������ѿڴ����ϻ��֡����һ�����Ÿֿ����ձ��ˣ�������Ŧ��һֱ�۵���ڵİ�ɫ��������������������ɫ�Ŀ��ӣ���ɫ��Ь������������ô���Ʒ�
��������Ȼ����ij���������Ʒ��ļһ�ע������ǡ�
�����������Ǹ����ⷢ������ʵ�������Լ��ʮ�������ҵ����ˣ�����һ��dz��ɫ�Ĵ�����������ڳ����ţ��̿���ñ��Ҳ��dz��ɫ�ġ������Ʒ�����������η�壬������Щ���ͺ������������ֻװ��������ǹ�ĺ�ǹ�ײ���������ƨ���ϡ�
�����������������١���Լ��ѷ����˵��
���������Ǹ����Ʒ�����������ָָ�����ǣ���˼�·�����˵����ʿ����������ǡ����ã�������û������ǹ�����������ƺ�������ˣ����������Ǻ���һ�������������
��������Լ��ѷ������ش�����������������˵�ñ��������ţ������ǵ������ƺ�������ϸ�����ô����Ļ�������һ��������к���һ������һ���������Ʒ��ľ���һ·С���ܹ��������Ǹ��ּһ�ڽ�����һЩָ��֮�����ܿ��ˡ�
��������Ȼ���Ǹ������ʵ����Ļ�ӭ�߽ǹ�ף��ó���ֻ�����˿ھ���������ǹ��ָ�����ǡ��ں��������м�IJոDz�����Ҳ����һֻ��ͬ����ǹ������û�б�Ҫʹ���������ǵ�����ֻ���ڱ������ǡ�
������������������ǹ���棬�ڲֿ�������֮�⣬һ�����͵����������ͷ��������������ưɣ����۷��ݣ�С�̵꣬�ֶ���ľ�ṹ�Ľ�����ֻ������������ש������Ұ�X�����������������Ƕ����У����������г���
�����������㶮������������ýӽ������������Լ��ѷ�����ǻ���Сͧ��ҡ�Ρ�
��������������ôһ�䣬����˵����������ȥ��һλ��Ӣ��ľ������Ӵ�һλ��Ҫ�ķÿ͡���
�����������ǵ��������������������Ǻ��У������������˵�����죡����Ȼ���ҵ����ǿ������ҵı��ܡ�
������������û�е�̫��ʱ�䣬����λ�־��ٷ�����ʱ�����������Ϊ��������һ���ලװж�ļ��վ��������ǰ����һ����С��������������ļһ���ĺ����ǻ�ɫ�ģ�˫�˿翪��˫�ֽ���������Ҳ���Ű�ɫ�ֿ����������鲼�����볤�㡣
��������������ϸ��һ�ۣ�ȴ�������Ĵ�����ڲ�ͬ���������鲼���������ż��£��ֿ���Ҳ�н�ɫ�Ļ��£�������ǹ�������ʽ����ǹ������������ϡ������Ҳ࣬������Ʋ�ӵ���ʹ�á�
�����������ۡ�����ˣ�������ƽ�����ȵ�����˵�������ൺ����־ֳ�������ۿ��Dz�����ŵġ���
����������ƽ�������ˡ��ŵĴ���ŷ�ġ�Լ��ѷ��ξ��������˵�����ܱ�ǸóȻ�������������ǵĴ�ͣ�������ǹ涨����Ӣ��֮��ĺ����������ﲻ��Ϊ�������ϰ�������ж��һλ�˿͡���
���������Ǹ����ٴ������ҵĺ����ºͰ�Ӳ�죬������ƽ���ı��飬����Ī��������Ҫ�½�ʿ���Ѿ���������ʦ�ˡ���
��������Լ��ѷ˵�����ͼ�������һ�۰�������֤������
����������һ�߰ѻ��ձ��������ŵݸ�����һ������һЦ���Ǹ����ټ���˻��գ�Ȼ���û�з�ڵ��ŷ��АJ���������ţ��������ţ����Ͽ�����ʲô���顣
��������Լ��ѷ�������������������ʼ磬���ٵ��۾����ŷ���������Щ��ǹ�����ˣ������������ĵش������˼䣬���ڲոDz��ϡ�
��������Ȼ������˾ֳ����������Ǹ������ʵ����ľ���˵��ʲô���·���һ���д������̵�ָ�
�����������Ǽ�����֮�ڣ��ұ㱻�Ǹ����������˾���ͧ�����˰������ٰ��ҵ����а��ݸ��ң�ͬʱ���Ҳ���Ȼ��Ц��һЦ�����ൺ����ֳ�С�������ذ����ۺã������ŷ��Ȼ����������Ż����ң�������һ������
������������ӭ��������������������������˾ֳ�˵��
����������Ҳ��ֳ�����һ������Ȼ���������Ĵ���һ��ͷ�������ѰѾ���ͧ���˸�ͷ�����ؿ����ˡ�
���������������������������ൺ�ϡ�
����ʮ���¡���������
���������������һƬǦ��ɫ������Ϯ��֮ǰ�ȷ���һ���磬�������С�����Լ������ʮ������ҡ������Ơkȴ���������ܣ��ҵĺ��������Ӳ�춼��ճ�������ˣ����������ֱ����ᡣ
���������������������а������ڴ����Ʒ��ľ���ֳ����ߡ����Ǽһ���������������ֶ�����������ǰ����Ⱥʯ��һ����Ĭ����ÿ���˶�����Ͷ�����������Ի��Ŀ�⡣
�������������������ﲻ������������𣿡����ʡ�
�����������ǵġ�����������·ʱ�������۾�һֱע������ǰ������ʹͬ��˵������Ҳ�����ҿ�һ�ۡ�
��������������˵��������ʦ����
������������������Ī�����ģ���������ʦ����ɫ����ڡ���
����������ɫ���磬һȺȺ����Ϸ�ĺ����DZ����������ѧУ�ķ�����ȥ��ż�����䵥�������Ҵ�������ͷ���������Ƴ���С�����������г��������м䣬�����ǵķ��Խ����ţ��������·��������̣����������г����ʵ�Ա�뾯�첻ʱ�ذ��ų��壬������Ϊ�����ÿ�����
����������Ȼ��û���˸ҳ��ž���ֳ������壬���������İ�С��ȴ��������������η�����ϡ���ʵ�ϣ�ÿ���˶�Ϊ�����ÿ����������������������ǵ��Ӷ������Ŀ�⣬��������ֳ�Ϊ��ͬһ�����������һ��
��������������һ��������С����˵��
���������������й�����ҽԺ���ʾ֣����磬���ߵ�̨�������豸����
�������������Ǹ��ִ����ij��С���
��������������һ�棬�����ƺ���û����ȫ���������н���ã�С��ĵ���������࣬û���������ࣻ�̵꿴������һ���������ƣ�˽��ס��ҡҡ���������������һĿ��Ȼ����ʹ���ǻ�û�а�װ�������ִ�ͳ�İ����ʹ�����
������������һֱ�߹����ĸ���������ʱ�ֵ�ǰ�������С��Ĺ㳡���㳡�Ա���һ����ΰׯ�ϵ�������¥ģ���İ�ɫ����ľ�ṹ¥����¥ǰ�����ӣ���˫���š�����·���������ܵ�С������ĵط�������������ÿ���˶���������װ��̿㣬���Ű�ɫ�İ�������ñ���ɫ�ֿ�����ɫ��ñ�����Ű�Ь��
����������˾������������˾ֳ�˵���������в�����ɫ�Ľ��������ҵİ칫�Ҿ����Ƕ�����
��������������û�н�¥���ֳ���һ������¥ǰ�ĺ�ɫ�γ�ǰͣ���˽Ų�������һ�����̿�ġ�����Ժ��¥��ȥ�ľ�������������Ǹ����������Ǿ���һ�����������ܽ�¥�ڡ��ܿ죬��һ������Щ�ľ������˳�������Ҳ���Ű̿㣬���Ű�ñ�ӣ�������һ����Ƥ��������ֳ����˸��ֳ�����˵��Щʲô���Ǹ����ᾯ��˵������������Ȼ��Ϊ�������γ��ĺ��š�
��������������γ����ֳ����Ҳ������������ľ����Ƶ���ǰ��������ʻ���
�����������������һ������Ҫȥ���ﲻ���Եò���ò�ɣ������γ������г�����ʻʱ�����ʡ��������λ�ܿ����������ⲻ�Ǻ����γ����������ձ��γ������������ʣ���ʹ����������һ�ܱ��ص���������������Ӧ��ѧϰһ���������������켼����
����������ԭ���ҵ���������˾ֳ�˵����������ȥ������������
����������Ŷ�����صij��٣���
�����������ǵģ����dz�֮Ϊ���ܶ�������
�������������ൺ���ܶ�����
���������������������ൺ��������������Ⱥ�����ܶ�����
����������Ŷ�������ܿ��������ǵġ���
�����������ǵġ�������������һ���ܵ����������������������ҪԶʤ�����տ����Ǹ������������µĺ��ӵ����ӣ������ú�ľ��ξ��ȥ�����ˣ��Ǹ�����������С��������������һ���־䣬�����������ǵ����
��������Ȼ����������λ�ϣ�Ϊ�Ǿ�ֵ�ü���ľ��Ӷ����⡣
�����������Ǹ����š�������Ӣ���𣿡�
������������һ�������Ȼû���ҽ��úã�����������
�����������Ǿ�����һ������������̨����������˵Ŀ�Ĺ�������������İ���ĵط���������һ����Ϥ���������������ʻ�����ﱦ����״��ʥ��ʱ���ҵ�����ӿ��һ�������İ�ο�С�
���������������������ʡ�
��������������IJ��������ӹ���ʯ���Ƶ��������������
�����������������ˡ��Ұѳ���ҡ����������𣿡�
������������㡣����˵��
���������γ��ں��Ơk��Ψһ�������������ǵĶ�������������磬�ֳ�ҡ�������DZߵij�����ֻһ�����������˵������һ�������ˡ�
�������������������һ�¸����˳ǵ��˿�״���𣿡�
���������ֳ�˵����һ����ǧ�ˣ�����һǧ�ˡ���
���������ܸ������������¶���ҡ�
����������ԭ��Ϊ��ط���һ������ɭ�ϡ���ͬ����һ���Ļ������䣬�����෴�����߽���һ���������У���������Ϊ���ǵ�������������һ����һ��������ʯ̨�������̨���ϵ�С�ȷ��εض��������ͥԺ���뻨��������ľ�ϡ���ʯ����â�������ܷ��ݵ�ʽ�����ִ����ݶ�ȴ��������Ƥ������һ�����Ĺ������ÿ�����ˮ�������������ˮ���С�ż����һ����־�����ൺ�¹���ͳ��ʱ�ڵ�ʯͷ���ݻ���ֲ���ķ��ݳ��֣����˷·��ֻص����������˵�ʱ����Ȼ�������������ľ���������ݶ�����С����һ���Ĺ�������������Щ��ľͷ�ģ���������¸ǵĻ������ġ�������������������ִ������������
��������������������������������ʲô�������ǧ����ľ������������������dz������������Ĺ���
���������ڳ��еı�Ե���ڳ��������ڴ��Ѿõ�һƬ�ƾɵ��������ݣ�����һ����é�ݸ������ݶ���ľͷ���ݣ�������ֵ�����������Ů������ɫ��ɯ��������ǰ���Ҹе�һ˿Ī������ο��
����������������������������ʣ��Ҽ������������ǣ����˼���������ѽѧ���Ĺ�ƨ��С�ຢ��
������������ѧУ�����Ǹ���Щͷ�Լ��˴����ˡ������������ֳ�������˼������һ��ü���ܿ����ʶ���Ҳ������������һ���ʵĺ��壬������������˵������������
������������������
��������������һ��ͷ���ƺ���˵������ȫ��ȷ����Ҳ��ࡣ
������������ʻ���˳��У����ſ�����̽��úܺõĹ�·ʻ��Զ����Ⱥɽ�����ĺ�ɫľ����·���ߵ������ʢ���ţ���ʺ������ڱ�һ��ͦ����һ����������������ҶƬҡ���ţ���ʾ�ŷ�����١����ǵĽγ�������һ������б����ʯ��������������ï�ܵ��������ʻ������ԣ������𣬻Ƶ���ϼ���ڻҰ��������°����š�
����������������һ������ͬ����ͬ��ij���Ҳ������ʯ�����ġ�������ɫ�γ��Ѿ�ͣ���������ˣ����ϵ��������Ű�̫�����ձ����졣����ͣס�˳�������ľ����ƹ���Ϊ�ֳ��������š��������ȥȡ�ҵ����а�����ʱ����˾ֳ�˵����û�б�Ҫ���������
�������������ұ�����а����ڳ������ֻ�ź��ھ��IJ��������ڰ��ڣ������ҵļ������õ������µ��С�����ľ���˾�����ڳ����������˾ֳ����ſ������ʯ�����߽�һ�����������Ķ���ʽ���У��ķ��ε������Բ�εĹ�ľ���ö��߽��ģ���������һ����ɫ��ľ¥�������������У�ľ¥��Բ���Ǻ�ɫ�ģ�ͨ��ľ¥��ʯ�����ണ����ʯ����¥ǰ��һƬ�ջ��ĺ���ɫ����ɫ����ɫ����ɫ��Ѥ�����ˣ���ĸ��ɫ��������غ���һ�ԡ�
������������ط������������ܶ��ĸ�ۡ��
������������ǰվ����һλ�������٣���������ɫ�����Ʒ��������㣬����ѥ����ɫ������ǹǹ�ף�����һ����ʿ�����Ҿ����һ���ϲ������һЩ���Ʒ���
����������������������¥�ڣ��߽���һ��ľǽ�����ű�ֽ����������Ӳľ�ذ塢��ǻ�ƿ�в����ڻ������硣��������Ь��������Ь������ͬ������һ���˱��εĴ����������п�����������ң���������һ���Ӵ��Ҽ�칫�ҡ�������ļҾ߲��࣬���Ǻ�ɫ�ĐJľ��ߣ��������Ӱڷ��ھ�İ칫��ǰ�����ӵ���һ����һ��Ϊ��Ҫ�������ĸ߱��Ρ�
��������ռ�����Ÿ߱��ε���Ҫ������һ����С�����֡���Լ��ʮ�����ҵ����ˣ���ֳ�һ��Ҳ���Ű�ɫ�Ʒ����������ź�ɫ���������û�й���ǹ��Ҳû������ʿ������������Բ���֣�����ƺ����������ˣ���������Ҳ���ƣ�����ɽ��������ڲ�ͬ��ϡ��ĺڷ������ǰ����֩��һ����������ǰ���ϡ�
������������˾ֳ����˰������˵��������������λ�����������ܶ��ֻ��IJ���������������
����������������������λ������˵������ͳ����ں�����¡¡���죬�������ҵķ���������ԡ���������һ������
����������Ҳ����һ�������������Ҹе�������ң����ˡ��ҿ����ҵĽ����ų����𣿡�
�����������������˵�ͷ��
���������Ҵ��������Ŀڴ����ͳ��������ŵݸ�����
������������������������˵����������˾ֳ�ʾ��һ���⡣
�����������������������������������Ķ��棻������������ľ�߱����У������۾�����ʼչ���������š�һ������ͷ��ӡ�Ŵ�ʹ�ݵ��������ǵ¹�פ������ʹд�ģ���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