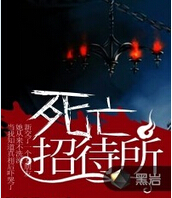死亡飞行-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过失灵的历史,在一九三六年本迪克斯飞行大赛中,它的油箱漏过油,舱盖也被吹走过。
从图森起飞,她驾驶着维修过的厄勒克特拉飞往新奥尔良,在下午六点钟抵达目的地。星期六傍晚降落在苏珊机场,在机场旅馆登记住宿。她同G.P.还有她的老朋友唐妮…雷克一起出去吃了顿平静的晚餐。所有这些轶闻我都是从报纸上收集到的,我的心追随着我做长途飞行的朋友,当报纸不能详尽报道她的一切情况时,我就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调查。
她现在似乎很不走运,即使是在迈阿密。第二天早晨,她驾驶着那只银色大鸟重重地摔在地上,几分钟后她从驾驶舱中爬下来。这次“几乎”坠毁的着陆被报纸登了出来,并引用了她的话,“我确信把它摔得很重。”
厄勒克特拉再次举止失常:减震器失灵,从新奥尔良起飞时就一路上漏着油,着路时太猛,油管也在漏油。麦肯尼雷领着一群机械师对所有毛病做了一次全力以赴的修理。
五月二十九日,阿美对记者说她要从迈阿密机场起飞,按着泛美航空公司的路线由东向西穿过西印度群岛,然后沿着南美洲东海岸继续飞行。G.P.与麦肯尼雷留在后面,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弗莱德…努南在六月一日凌晨五点五十六分出发。五百多名飞行迷到机场欢送,却被一队警察远远地拦住了。飞机起飞以后,她那些忠实的崇拜者们拼命地向飞机挥着手,并欢呼他们女主角的名字。
新闻界已经不容易被打动了,在芝加哥,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的是南部芝加哥的警察闹事,十名罢工的共和钢铁厂的工人死于这次事件中;而在第三天,每份报纸的头版都爇衷于报道英格兰的爱德华与巴尔的摩的沃利斯…辛普森的婚事。
在接下来的六天中,报纸上轻描淡写地提及了阿美,厄勒克特拉正飞过中美洲与南美洲的东部海岸,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委内瑞拉的卡瑞皮特,苏里南的帕拉马里博都做过停留。然后——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穿过了一干六百二十八英里的丛林与海洋——抵达巴西的福塔莱萨,纳塔尔是她横渡南大西洋之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据报上所载,在她每一处停留过夜的地方,她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身,睡眠不超过五小时。而那些飞行,坐在噪音嘈杂的飞机里,驾驶舱狭窄闭塞,这些才是真正的耐力测验。多数情况下,她同领航员努南的交流不是通过语言,而是一张用衣架固定在滑轮上的字条,否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要爬过位于她的驾驶舱与努南的导航桌之间的巨大的辅助燃料箱来交谈。
在大西洋上空的飞行很顺利,尽管遇到了一些逆风与暴风雨,厄勒克特拉表现正常,努南也显示了一流的导航水准。但是当他们在六月七日靠近非洲海岸线时,阿美没有听从努南的建议向南飞向达喀尔,而是坚持向北飞,沿着非洲海岸线又飞行了五十英里。当她注意到圣路斯几乎在达喀尔以北两百英里处时,她递给努南一张字条,问他是什么使他们偏向北方,他回答一个字:“你。”她后来也这样承认了。
他们在圣路斯着陆,他们修正后的目的地。在那里,兵营一样的宿舍,满床的臭虫与简陋的洗手间设备等待着他们。但是,他们第一周的飞行是成功的,四十小时之内飞行了四千英里。
短途飞行到达喀尔之后,阿美遇到了两天坏天气,她不耐烦地把下一个目的地从纳尔梅堡转移到法属西非洲的高尔,在北方的沙暴与南方的龙卷风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七个小时之内飞行了一千一百四十英里。第二天早上,她又做了将近一千英里的飞行,从高尔出发越过撒哈拉沙漠直抵法属赤道非洲的莱梅堡。酷爇难挡,在日落之前厄勒克特拉根本不能加油,因为那些汽油碰到烫手的金属几乎就可以燃烧起来。然后,他们飞往苏丹的艾尔法舍;六月十四日,又飞行两百英里到达红海沿岸的阿萨伯,在苏丹的喀土穆停留一下吃午餐,又在厄立特里亚省的马萨瓦港喝了茶。在第二周结束而飞行超过一万五千英里以后,她看起来比出发时还要津神。
接下来的一天,她穿过了红海和阿拉伯海,抵达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她在那持续的沙漠高温下度过了不愉快的两天,骑了两次骆驼,然后到邮局去挑选邮票,并监督邮局的工作人员盖销她保留的七千五百张首日封。六月十七日,她与努南向卡丘塔出发,即使在天空中,酷爇仍丝毫未减:在五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气温可达九十度。最后,酷暑消退了,暴风雨又来了,气流使厄勒克特拉以数秒钟一千英尺的频率上下颠动着。
六月十八日,她从卡丘塔的达姆达姆机场出发,厄勒克特拉在雨水浸渍的跑道上艰难地起飞,几乎撞到树梢上。季风雨在他们飞往缅甸仰光的路上一直陪他们到孟加拉湾。她没有一口气飞到仰光,而是在阿卡亚巴停留了一下,在十九日才抵达目的地,他们游览了金塔,第二天又动身去新加坡。她得到消息,说在爪哇的班多戈她可以找到机械师翻修她的飞机,这是她环球飞行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这次着陆并不稳定,然而,她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保罗…门兹后来所描述的“极度飞行疲劳”。
毕竟,她飞行了一百三十五个小时,飞越了两万英里;她在不熟悉的环境里睡觉,那环境有时简陋,有时异乎寻常;她吃得很少,睡得也少,忍受着酷爇、腹泻与恶心的折磨。
原定三天的维修厄勒克特拉的计划推迟到六天,直到六月:二十七日——延后的时间表会让C.P.普图南计划她七月四日返航时举办的盛大记者招待会落空——她与努南在帝汶岛的凯旁哥着陆,在夜幕降临之前,放弃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达温堡的打算,在高高的悬崖上,阿美、努南还有一些村民把厄勒克特拉用木桩固定在青草茂密的田野上.并用石块修筑了一圈围墙。用以防止野猪。她在凌晨四点钟动身,想要飞抵里尔,却由于逆风的原因被迫飞往达温堡,于上午十点钟在达温堡降落。飞机又做了一些小小的维修.然后——经过七小时四十三分钟的飞行,飞过一千两百英里的路程——厄勒克特拉在六月二十九日到达了巴布业——新几内亚的里尔。
天气与仪器故障耽搁了起飞,直到星期五,七月二日。上午十点二十二分,厄勒克特拉——携带着超过一千加仑的燃料,还有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弗莱德…努南——在一条长度仅一千英尺的粗糙跑道上轰隆隆地滑行着。前方还有两千五百五十六英里的长路在等待他们。导航员努南在地图上太平洋中部的位置上准确标出了湖兰岛的位置。
跑道的尽头是悬崖,下面是陡峭的胡思湾,许多旁观者带着看真正的惊险表演的心清聚在旁边。厄勒克特拉一直在跑道上滑行着,直到最后五十码,它的螺旋推进器卷起了一股红色的灰尘。在这炎爇晴朗的清晨,没有一丝风来帮助飞机起飞,旁观者们都说飞机似乎跳进了海里,企图自杀。的确,它看起来冲出了跑道,掉到了悬崖下面。
当厄勒克特拉再度出现时,它似乎盘旋在海湾上面,距离水面不超过五、六英尺,水花飞溅。它用了很长时间,那些旁观者说,最后才从水面上升人空中,但它终于做到了。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厄勒克特拉在人们的视野里停留了很长、很长时间。
之后,终于,它消失了。
在她飞行的最初七个小时里,阿美一直同里尔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在规定的航线上,相隔七百五十英里,她的声音能被清晰地接收。他们建议她保持同样的无线频率以进行联络。但这是里尔地面人员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美国舰队的驱逐舰安大略号,就停在里尔与湖兰岛之间的太平洋上,准备提供导航信息与天气变化情况。厄勒克特拉应该经过这条船,舰上的三名水手一直在注意地…望,一名报务员早已等待多时,但是没有她的迹象。当然,午夜之后,好天气变成了坏天气,暴风袭来,一直盘踞到黎明,这也许减慢了厄勒克特拉的速度,并且(或者)使她用光了燃料。她逃过了暴风,也可能无意中远离了安大略号的视野。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依塔斯克号在湖兰岛附近,受命以定向无线电讯号、声音交流与水面烟柱等方式来帮助艾米莉…埃尔哈特。但是从子夜开始,依塔斯克号的无线电台每隔一个半小时就报告一次天气情况,而阿美却没有任何回答。
然后,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那名首席报务员——有两名通讯社的记者正躲在挂着“闲人免进”的无线电通讯室门外窃听——认为他辨别出了她的声音,那两名记者也听到了;之后,在三点四十五分,他们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这一次清楚多了,她说:“埃尔哈特:多云,隔一个半小时后在三千一百零五千赫接听。”到了凌晨四点,报务员呼叫三千一百零五千赫,询问:“你的位置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到达湖兰岛?请回答。”
但她没有回答。然而在凌晨四点五十三分,当报务员正向三千一百零五千赫发送最新天气情况时,阿美虚弱的、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插了进来,在静电的干扰中,只有“部分陰云”几个字被分辨出来。
在她原定到达湖兰岛的最后十五分钟,凌晨六点十四分,阿美的声音再度被听到,她说:“隔一个小时后向三千一百零五千赫发送一次信息,我会在麦克风里吹口哨。”但是她的哨声在黎明时分淹没在太平洋电台和谐的呜咽声中了,报务员无法再确定她的频率。
七点四十二分,阿美的声音大一些了,她说:“我们一定在你们的视野里,但是看不到你们汽油没有多少了,无线电波到达不了你们的范围,飞行高度一千英尺。”一分钟之后,阿美又打断了依塔斯克号发疯似的呼叫,仍很大声说:“埃尔哈特呼叫依塔斯克号,我们在兜圈子,但是听不到你们”
依塔斯克号的报务员向阿美有可能使用的每一个频率传递信息,并仔细接听,她最后的信息来自八点四十四分,她声音发抖而恐惧,“我们的位置在一五六一一三七,我会重复一遍,我会在六千两百一十千赫重复一遍。等一会儿,收听六千两百一十千赫,我们由北向南飞。”
由于没有参照物,她的“位置一五六一一三七”和“由北向南飞”根本全无意义。一直到上午十点,报务员仍试图同她联络。
上午十点十五分,依塔斯克号的指挥官命令开足马力,开始在海面上进行紧急搜索。很快,扫雷艇斯万号,战舰科罗拉多号,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还有四艘驱逐舰也加人进来,它们还从来没有为一架失踪的飞机做过这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
艾米莉…埃尔哈特又回到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第九章 疑云重重
午后,在我的办公室里,坐在我的转椅中,我后面就是死气沉沉的高架铁道线与范布轮街,温暖的、几乎不易察觉的清风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我手中拿着自来水笔对着办公桌上的一堆零售信用支票簿发怔,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大声问,尽力盖过街道上传来的噪音。
“内特…黑勒?保罗…门兹。”
即使只在这两个名字中,我也听得出他有些心烦意乱,因为我们之间唯一共同的朋友是阿美,所以他的语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了听得更清楚些,我关上了窗户,尽管这长途电话听起来已很清晰了。
“你好,保罗我们女孩的环球冒险进行得还顺利吧?”
“不,”他断然地说,“事情变得更严重了,她起飞了。”
我向前倾了一下身体,“那不是飞行员应该做的事吗?”
他的语调里有一些苦涩的滋味,“她对记者说,她要驾驶厄勒克特拉去试航,但是她去迈阿密的真正目的,却是开始她的环球飞行。”
“你在哪里,伯班克?”
一列火车从高架铁道上隆隆驶过,我不得不提高了声音。
“不,不,我在你的后院圣路易斯。我们在兰勃特棒球场举行飞行集会。”
“我以为你是艾米莉的专职技术指导。”
“我是的。自从二月份开始,我就放弃了其他飞行活动,一心为这次环球飞行做准备。可是当这次飞行集会临近时,艾米莉与吉皮都鼓励我花些时间去参加。”
“你是说他们共同愚弄了你?她在她的首席指导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溜掉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这是普图南的主意,听着这件事有些不对头,我们最好谈一次。”
“我们不是正在谈吗?”
“你想要工作吗?”
“通常是的,你在想什么?”
“你这个周末有空儿吗?”
“我永远都有空儿它会每天花掉你二十五美金。”
由于G.P.与阿美每天付门兹一百美金,我猜他付得起这个价钱;此外,我不得不取消星期六晚上与弗瑞忒吉儿…贝的约会,当她在咕咕俱乐部表演完之后。
“我买你两天的时间,”他说,“不管你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我明天整天都参加飞行集会,但星期天不参加。我们在星期一之前不会回家。”
“你到我这儿来,还是我到你那儿去?”
“你到我这儿来我们星期天下午在运动公园碰面看比赛——另一天玩掷骰子。我赢了两张卡迪那兹棒球队与巨人队比赛的包厢座位票,那会是一场津彩的比赛,迪恩与哈贝尔当投手。”
这趟旅行看来是值得的,棒球不是我最爱的运动——我的运动是拳击,同巴尼…罗斯一起在西城区长大,理应如此——但毕竟狄赛…迪恩与卡尔…哈贝尔是棒球王国的明星。
“你明天乘火车到这儿来,”门兹继续说,““我给你出旅费,我会在科罗拉多旅馆为你预定房间。”
那是我与阿美在演讲旅行中住过的地方邑在那里,我第一次为她按摩颈部
“你也信在那里吗?”我问他。
“不!我住在机场附近的旅馆.在比赛开始前我不想同你见面。
“为什么要这样鬼鬼祟祟呢,保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