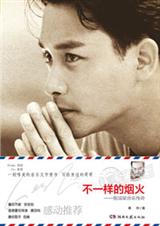张国焘传-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三月初陈先生向我表示: 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页。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首脑打出旗帜,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但当陈独秀表示要慎重,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时,张国焘则认为陈独秀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张国焘另组工农党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这种想法却十分清楚地表明: 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就会背离中共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和他自视势单力孤,没有将这种意图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当他人强马壮时,就毅然决然地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这一切都表明,在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摆正。
二 争论于中共六大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因此产生了混乱。一些人面对异常艰难的革命局面,表现出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翻开当时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人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在各种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员的人数一时由近6万人减为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内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和急躁冒险的盲动主义错误,进一步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系统地研究党面临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将革命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春开始,各地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赴苏。鉴于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但是,陈独秀却拒绝参加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罗亦农等人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说动他。
陈独秀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党内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的话,那么,张国焘就是第二责任人。所以,当张国焘接到参加中共六大的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自己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到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当的。邓中夏也热心地劝说张国焘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作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指派张国焘在哈尔滨接应途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 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就这样,张国焘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顺利过境后,才最后离开哈尔滨。唐韵超: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既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视。为了给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于6月12日前后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现在不是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而是低潮时期。斯大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确定党的任务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定了调子。
当时,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思想极不统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责任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出席者是: 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夏曦、蔡和森、何资深、项英、李立三、黄平、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向忠发、张昆弟、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王仲一、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共21人。“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会上,布哈林要求大家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 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 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 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画出中共的真相”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8页。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用时达九小时。在报告的结尾,瞿秋白说: “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张国焘早就对瞿秋白的报告一肚子意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地说: “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瞿秋白却耐心地说: “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
从6月21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讨论中作了长篇发言,就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过去的教训,“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党的政策,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另一方面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他还认为,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能与革命情绪混为一谈,目前没有广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形势。
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他指出: 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过每一个领导群众争斗或动员群众的机会,以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并进行不断摧毁敌人实力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才能形成强固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肃清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只有这样,党才能应付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和实现在此高潮中组织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他在发言中,有时不是客观地分析以前党所犯的错误,而是夹杂着个人泄私愤的情绪,尤其是对瞿秋白多所指责。如,当他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时说: “自当初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对于这种政策的观念,都是模糊的,有许多不自觉的‘左’倾或右倾的倾向。现在秋白同志分析起来,说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左’倾和右倾,好像机会主义推进的两个轮子,都是机会主义的根源。大家同志或许不太明了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 当时张国焘同志是代表‘左’倾的观念,陈独秀同志是代表右倾的观念,这都是机会主义。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当时和独秀同志的见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说别人脑袋里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轮子,那末,他自己脑袋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轮子。”
同时,张国焘在发言中也试图澄清一些与他自己有关的历史事实。例如,他针对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给他的处分中说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和他“假传圣旨”一事说: 在武汉讨论南昌暴动时,曾有加伦、罗明纳兹、恩来和我到会。讨论时我曾提出了湖南的意见。加伦说: 还是到广东东江好,有两个理由: 1。东江方面军事空虚;2。那里农民颇有势力。当时我就说: 若说到农民势力,湖南农民势力并不差,而且尚未冷却,往广东如何与两湖秋收暴动相联系呢?所以后来中央说: 南昌暴动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于南昌暴动如何发动、用什么政纲、政权组织的形式如何,是没有讨论的,更没有决议。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纳兹说: 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说,南昌暴动若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叫我们同志退出军队,送他们到农村中去。加伦报告说: 他早上会见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就是他的军队不再东进,停留在南浔路一带,逐渐向广东进发。因此,加伦主张我们同张发奎一同到广州,到广州后再行与张发奎分化。同张发奎到广州有二利: 1。军力较大,可以击破敌人军队,实际到达广州; 2。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再在广州分化,我们可以多分他张发奎一部分军队。因此,他的结论是,到广州后再和张发奎分化。他们两人说完话后,大家都没有发言,罗明纳兹也没有表示不赞成加伦的意见,他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当时不肯去,后来秋白、维汉说这件事关系重要,还是你去一趟吧,我就是奉这个使命去南昌的
当时张国焘的意见是: 将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联系起来,就是决定南昌起义后发兵湖南;或者把南昌暴动推迟,等与张发奎共同到广州后再举行。至于后一种意见是否可行,张国焘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南昌暴动后,张发奎并未对教导团采取清洗措施,使其一直保存到广州,并成为广州暴动中的支柱。
张国焘发言的过程中,有人问他去南昌的任务是否是传达送信,张国焘断然回答说: “我去南昌当然不是专去送信,是去参加讨论是否在南昌暴动的,岂有中央委员专去送信的道理。”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
张国焘参加了政治、苏维埃运动、宣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