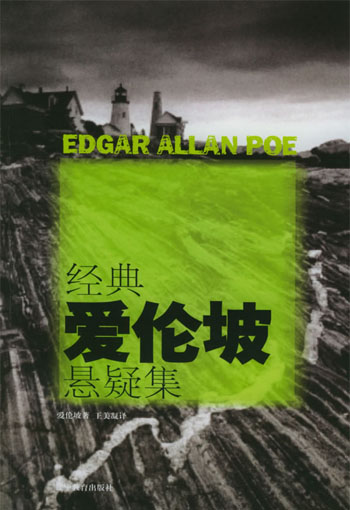希区柯克悬疑小说-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珍尼特是这样说的?”
“当然。”
“还有什么?”
“够了,我真不想多说了。”
“快说,快说,请继续吧。”
“噢,累欧耐,别这样对我大叫大嚷。你非要听我才告诉你,不讲好像不够朋友。你不认为现在我们已是真正的朋友了?”
“快说吧!”
“嘿,老天,你得让我想想,就我所知道的她确是这样说的。”格拉笛模仿着我那极为熟悉的珍尼特的女中音说:“累欧耐真是个乏味的人,吃饭总是去约赛·格瑞餐厅,总是在那里,反复地讲他的绘画,瓷皿,瓷皿,绘画。在回去的出租车里,抓住我的手,紧紧挤靠着我,一身劣质烟草味。到了我家,我总会告诉他呆在车里不用下来了。他也总是假装没听见,斜着眼看我开门,我总能在他尚未动脚以前赶快溜进屋,把他挡在门外,否则”
那可真是个可怕的晚上,听到这些,我已完全垮掉了,沉沉的回来,直到第二天天大亮尚没能从绝望的心情中挣脱出来。
我又是疲惫又是沮丧地躺在床上,拼合着昨天在格拉笛家所谈内容的每一个细节,她丑陋扁平的脸,鳗鱼般的嘴,说的每句话和令人难以忘记的珍尼特对我的评价。那真是珍尼特说的!
一股对珍尼特的憎恶突然升腾,像热流般传遍全身。我突然像发烧一样一阵颤抖,竭力想压下这股冲动,对,我要报复。报复一切敢于诋毁我的人。
你可能说我太敏感了。不,真的。当时这件事逼得我差点杀人,要不是在胳膊上掐的一条条深痕给了点痛苦,我真可能杀人。不过,杀了那女人太便宜了她,也不合我的口味,得找个更好的方法。
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也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职业。但是,怨恨与暴怒能使一个男人思维惊人地敏锐。马上,就有了一个计划,真正的令人兴奋的计划。我仔细考虑了它的每一个细节,改掉了几处难以实施之处。这时,我只感到血脉贲张,激动地在床上跳上跳下,捏得手指嘎嘎作响。找到电话簿,查到了那个电话,马上拨号。
“喂,我找约伊顿先生接电话,约翰·约伊顿。”
“我就是。”
唉,很难让这男人想起我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他。当然他可能会认识我,每一个在社会上有钱有地位的人,都是他这号人追逐的对象。
“我一小时后有空,我们见一面再说吧。”
告诉了一个地址,我就挂了电话。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一阵阵的兴奋,刚才还处于绝望之中,简直想自杀,现在则亢奋极了。
在约好的时间,约翰·约伊顿来到了读书室,他个不高,衣着讲究,穿件黑色天鹅绒夹克。
“很高兴这么快就见到了你。”
“荣幸之致。”这人的嘴唇看起来又湿又粘,苍白之中泛点微红。简单客套几句话,我马上就谈正题:
“约伊顿先生,有个不情之请要劳您大驾。完全是个人私事。”
“噢?”他高仰着头,公鸡似的一点一点。
“是这样,本城有个小姐,想请您能为她画张画。我非常希望能拥有一张她的画像,不过请您暂不必告诉她我的这个想法。”
“你的意思是”
“是否有这个可能,”我说:“一位男士对这位小姐仰慕已久,就产生了送她一幅画的冲动,而且要等到合适的时候突然送给她?”
“当然,当然,真是罗曼蒂克。”
“这位小姐叫珍尼特·德·倍拉佳。”
“珍尼特·德·倍拉佳?让我想想,好像真没见过她。”
“真是遗憾,不过,你会见到她的,比如在酒会等场合,我是这样想的:你找到她,告诉她你需要个模特已好几年了。她正合适,脸型,身条,眼睛都再合适没有了。你愿意免费给她画张像。我敢肯定她会同意的。等画好后,请送来,当然我会买下来的。”
一缕笑意出现在约伊顿脸上。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是不是觉得太浪漫?”
“我想我想”他踌躇着想说什么。
“双倍画酬。”
那个男人舔了下嘴唇,“噢,累欧耐先生,这可不寻常啊!当然,只有毫无心肝的男人才能拒绝这样浪漫的安排呀!”
“我要的是张全身像,要比梅瑟的那张大两倍。”
“60X36的?”
“要站立着的,在我看来,那是她最美的姿势。”
“我可以理解,我很荣幸画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
“谢谢,别忘了,这可只是我俩之间的秘密。”
送走那个混蛋以后,我迫使自己能安静地坐下来连做了二十五个深呼吸,否则真会跳起来,像白痴一样快乐地大喊几声。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现在只有耐心等一段时间。按这个男人的画法,可能得几个月,我得有耐心。
消磨这段时光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出国了。我去了意大利。
四个月后我回来了。令人欣慰的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珍尼特·德·倍拉佳的画像已完成,约伊顿打电话来说已有好几个人想抢购这幅画像,不过已告诉他们这是非卖品。
我马上把画送进了工作室,强捺兴奋,仔细地看了一遍。珍尼特身着黑色晚礼服,亭亭玉立,靠在一个用作背景的沙发上,手则随意地搭放在椅背上。
这幅画确实不错,抓住了女人最迷人的那份表情,头略前倾,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当然,脸上的缺憾都已被狡猾的画家加以掩饰,脸上的一点皱纹,过胖的下巴都巧妙地处理掉了。
我弯下腰来,仔细检查了画的衣服部分。好极了,色彩上得又厚又重,颜料层能看得出来比其他部分更厚出一些。一刻也不想再等,脱掉上衣,就开始干起来。
我本来就以收藏名画为业,自然是个清理修复画像的专家。清理这活除了需要耐心外实在是个很简单的工作。我倒出了些松节油,又加了几滴酒精,混合均匀后,用毛刷沾了些轻轻地刷在了画像的晚礼服上。这幅画应该是一层干透之后才画另一层,否则,颜料混合在一起,那就要费大功夫了。
刷上松节油的那一块正处于人的胃部,花去很多时间又刷了几次,又加了点酒精,终于颜料开始融化了。
近一小时,我一直在这一小块上忙,轻轻地越融越深入到油画的内部。突然,一星点粉红跳了出来,继续干下去,礼服的黑色抹去,粉红色块显现。
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已知道完全可以不破坏内衣的颜色而把该死的晚礼服脱去。当然,要具备足够的耐心与细致,适当配制好稀释剂,毛刷子更软一些,工作自然进展得相当快。
我先是从她身体靠中间的位置开始的。礼服下的粉红色慢慢显露,那是一件有弹性的女子束腰,用来使身材更具流线型,可产生更苗条的错觉。再往下走,发现了吊袜带,也是粉红色的。吊在她那有肉感的肩膀上。再向下四五英寸,就是长筒袜的上端了。
当整个礼服的下部除去后,我马上把精力放到了画像的上半部分,从她身体的中部向上移,这部分是露腰上衣,出现了一块雪白的皮肉。再向上是胸部,露出了一种更深的黑色,像似还有镶皱褶的带子,那是乳罩。
初步工作已大功告成。我后退一步仔细端详。真是令人吃惊的—幅画。珍尼特身着内衣站在那里,像是刚从浴室走出来。
下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了!我一夜没睡准备请柬,写了一夜信封。总共要请二十二个人。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这样的内容:“二十一号星期五晚八时,请赏光到敝舍一聚,不胜荣幸。”
另一封信是精心给珍尼特准备的。在信中,我说我渴望能再见到她我出国了我们又可以见面了等等等等。
总之,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请客名单,包括了本城所有最有名的男人,最迷人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我有意要使这场晚会看起来完全是很普通的那种,当笔尖刷刷地在信纸上划过,我几手可以想像到,当这些请柬到达那些人手中时她们会激动地大叫:“累欧耐要搞一个晚会,请你了吗?‘噢,太好了,在他晚会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他可是个可爱的男士。”
他们真的会这样说?突然我觉得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是这样的:“亲爱的,我也相信他是个不坏的人,不过有点令人讨厌,你没听过珍尼特是怎样评论他的吗?”
很快,我发出了邀请。
二十一号晚八时,我的大会客厅挤满了人。他们四处站着,欣赏墙上挂的我收集的名画,喝着马提尼酒,大声谈论着。女人们身上散发着芬香,男人们兴奋得满面红光。珍尼特穿的还是那件黑色晚礼服,我从人群中发现了她。在我脑海里,见到的还是那个仅穿内衣的女人,黑的镶有花边的乳罩,粉红有弹性的束腰,粉红的吊袜带。
我不停地在谈话的人群中走来走去,彬彬有礼和他们聊上几句,有时还会接上话题,使气氛活跃起来。
晚会开始,大家都向餐厅走去。
“噢,老天,”他们都惊呼起来:“屋里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蜡烛,蜡烛!”“累欧耐,太浪漫了。”
六只细长的蜡烛以两英尺为间隔插在餐桌上,柔弱的烛光只勉强照亮了附近的桌面,房间的其他地方则一片黑暗,这正是我希望的。
客人们都摸索着找到了位置,晚会开始。
他们好像都很喜欢这烛光下的气氛,尽管因为太暗,使谈话不得不提高了嗓门。我听到珍尼特·德·倍拉佳的谈话:“上星期在俱乐部的晚宴令人讨厌,到处是法国人,到处是法国人”
我一直在注意那些蜡烛,实在太细了,不长时间就会燃尽。突然,我有些紧张——从没有过的紧张——但又有一阵快感,听到珍尼特的声音,看到她在烛光下有阴影的脸,全身就充满了一阵阵冲动,血液在体内四处奔腾。
时机到了,我吸了一口气,大声说:“看来得来点灯光,蜡烛要燃尽了。玛丽,请开灯。”
房间里一片安静,可以听到女仆走到门边,然后是清脆的开关声。立刻,到处都是刺目的灯光。
趁这时,我溜出了餐厅。
在门外,我有意放慢些脚步。听到餐厅里开始了一阵喧闹,一个女人的尖号,一个男子暴跳如雷的大喊大叫。很快,吵闹声变得更大,每个人像在同时喊着什么。这时,响起了缪梅太太的声音,盖过了其他一切:“快,快,向她脸上喷些冷水。”
在街上,司机扶我钻进了轿车,我们出了伦敦,直奔另一处别墅,它距这里九十五英里。
现在,再想到这事,只感到一阵发凉,我看我真是病了。
敲诈
敲诈
第一封信是在星期二上午送到的。这很奇怪,因为星期二约翰的信件很少。星期五寄出的信,星期一早晨到,星期一寄出的信,除非一早就寄,否则星期三或星期二下午才会收到。这封信是星期二上午十点时,秘书送来的,和其他信件一样,没有拆开。约翰的信都是自己亲自拆的。
其他的信件,大多是广告,约翰拆开后瞄一两眼,就撕掉扔进废纸篓。然而,当他看到这封特别的信时,停顿了一会儿。
他仔细打量着信封,地址是他的,邮戳是星期一晚上的。四毛钱的邮票,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
约翰打开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两人的半裸照片。其中一个是男的,五十出头,秃顶,窄鼻梁,薄嘴唇。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是个女人,看上去二十多岁,一头金发,身材纤细,非常迷人。男人就是约翰本人,女人是露西。
约翰盯着手里的照片,一动不动。然后,他把照片放到办公桌上,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前,锁上门,再走回办公桌前,坐下,确定一下信封里除了照片没有别的,然后把照片和信封一起撕成两半.放到烟灰缸上点着。
如果是一个不那么沉着的人,他可能把照片和信封撕成碎片,撒得满地都是,然后跌坐在办公桌后,担惊受怕。约翰是个很沉稳的人,他并不认为照片是一种威胁,这只是一种可能。他可以再等等。一位富于幻想的人,也许会把照片留下做个纪念。约翰不是那种人,他不留纪念品。
烟灰缸的火有一股臭味。燃烧停止后,约翰打开空气调节器,房间里的臭气很快清除了。第二封信是在两天后的星期四上午寄到的。这是约翰意料之中的,他既不高兴,也不恼怒。他在一大堆信件中发现它。信封和第—个一样,地址一样,是打字机打出来的,邮票也一样,只是邮戳不同。
这封信里没有照片,却有一张打字的普通信纸。内容如下:
“把十元或二十元面额的钞票一千元,放到一个包裹里,把包裹存放到时代广场的存物间,钥匙放进一个信封,留在假日旅馆的柜台上,留交查理先生。今天就办,否则照片将寄给你太太。别报警,也别请私人侦探,别做任何蠢事。”
最后三句话是不必要的。约翰根本不想报警、请侦探,或做任何傻事。
信和信封烧毁之后,约翰站到窗前,看着东43街。他想,信比照片更让他心烦,那是威胁。这件事会破坏他完美的生活。
在接到敲诈信之前,约翰的生活十分完美。首先,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是一位会计师,自己开业,每年由于帮助一些个人和公司偷税漏税,赚了不少钱。其次,他的婚姻也很美满,太太比他小两岁,家庭生活很愉快,太太从不干涉他的事。他开了一个户头,每年让太太支取两万五千元的零用钱。
最后,约翰还有一位情妇。当然,这位情妇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名叫露西。她向他提供肉体和感情上的满足。她非常细心,而且要求不多,他为她租了一套公寓,让她吃喝不愁,还给她一笔零用钱。
一个完美的太太,一个完美的情妇:这个敲诈者,这个查理,现在正威胁着约翰的完美生活。如果这该死的照片落入太太的手中,她一定会和他离婚,如果离婚的事宣扬开来,他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接着他就会失去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