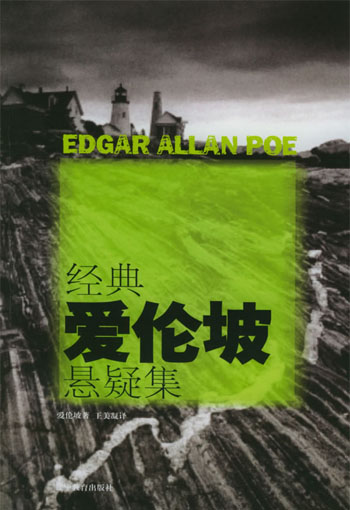爱伦坡经典悬疑集-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看来,墙壁与地面是彻底分离的。事实正是这样。我拼命从那道缝隙向外看,当然这么做
不过是徒劳而已。
我刚放弃这一企图,立刻发现牢房起了不可思议的神秘变化。我先前已观察过,墙上的
那些鬼怪图轮廓虽然相当清晰,但色彩似乎模糊了。可眼下,色彩即刻间却呈现出惊人的变
化,而且越来越光辉夺目。这使得那些妖魔鬼怪的画图更其可怕,就算神经没我脆弱的人,
也会吓得两股战战。先前从没看到过那些鬼怪有眼睛,可现在,一双双魔眼从四面八方瞪着
我,目光中还流溢出疯狂而可怕的欢快,闪出火焰般可怕的光芒,我无法迫使自己相信那火
是虚幻的。虚幻!——在呼吸之间,已有铁板烧热的气息扑进鼻孔!牢房里弥漫着令人窒息
的味道!那些盯着我受煎熬的魔眼一闪一闪的,也越来越亮了!深红的颜色越来越浓烈,在
那些血淋淋的恐怖画图上漫射。我气喘吁吁!我难以呼吸!毫无疑问,这是那帮折磨我的家
伙设好的阴谋。哦,冷酷的恶魔!为躲开炽热的铁壁,我只得朝地牢中央退缩。想到即将被
活活烤死,陷坑的凉爽倒成了精神抚慰剂。我迫不及待地冲到那致命的坑边,瞪圆了双眼往
下看。燃烧的屋顶发出的亮光,照彻了坑内的角角落落。我有一刻是癫狂的。我的心灵拒绝
领悟眼见的事实。但最后,它还是硬闯进了我的内心——在我发抖的理智上,烙下了深深的
印记。哦,不可言传!哦,恐怖!哦,登峰造极的恐怖!我尖叫着逃离坑沿,悲痛地掩面而
泣。
温度在急剧升高。我再次抬头张望,浑身好似发疟疾一样打颤。地牢里第二次起了变化
——这一次显然是形状上的变化。和以前一样,我一开始也是怎么都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
么。不过这一次我很快就吃准了原因——由于我连续两次脱险,宗教法庭在加快进行报复。
这次再难与死神周旋了。地牢是正方形。可现在我看到,铁壁的其中两个角已经变成了锐角,
另外两个则成了钝角。伴随着低沉的轰隆声,骇人的变化飞速加剧。瞬息之间,地牢就变成
了菱形。但变形还在继续——我一点都不希望他停止。我可以把火红的墙壁拥进胸膛,作为
我永恒的裹尸布,就此获得安宁。“死亡,”我说,“除了死于陷坑,我接受任何死亡!”
白痴!我难道不知道,火烧铁壁就是为了把我逼入陷坑?难道我抗得住铁壁的炽热?难道我
经得起它的压力?此时,菱形变得更扁了,速度之快,根本容不得我有片刻的思考余地。菱
形的中心,当然,也就是它最宽的地方,已横在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上。我退缩着——但
丝丝逼近的铁壁,不可抗拒地推着我前进。最后,我的身体烤焦了,它扭动着,翻腾着,可
地牢坚实的地板上,已无我的立锥之地。我不再挣扎。我最后响亮、悠长、绝望地尖叫了一
声,为痛苦的灵魂寻到了发泄的出口。我感觉到自己在陷坑边缘摇摇欲坠——我移开了目光
——忽然,我听到了一阵嘈杂的人声,听到了一阵嘹亮的声音,像是无数号角的奏鸣。我还
听到了似乎是雷霆万钧的刺耳的声音!炽热的墙壁“刷”地一下恢复了原状。正当我晕乎乎
地快要跌入深渊之际,一只手臂伸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那是拉萨尔将军的手 。法国军
队已开进托莱多城。宗教法庭沦陷敌手。
(1842年)
一桶白葡萄酒福图那托对我百般伤害,我都尽量忍气吞声,不过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
就要发誓报复了。您是熟知我的脾性的,总不会当我只是说一说吓唬人。总有一天我要报仇
雪耻。这个念头坚若磐石。既然主意已定,就没想着会有危险。我要让他吃够苦头,而且不
留后患。复仇的反得报应,这笔账就是没了清;复仇却不让仇家知道是谁害他,这笔账同样
没算清。
要知道,我的任何言行都没让福图那托怀疑是居心不良。我依旧对他笑脸相迎。他可没
察觉到,如今我可是笑里藏刀,一心要宰了他。
福图那托这个人在别的方面虽令人尊重,甚至是惧怕,可他就是有个弱点,老为自己是
个品酒高手而得意洋洋。意大利人中,几乎没人有正经八百的鉴赏家气质。他们的热心多半
为了随机应变,以诈骗英国和奥地利的大富豪。说起绘画和珠宝,福图那托和他的同胞一样,
只是夸夸其谈,但说到陈酒,他就不矫情了。我在这一点上跟他大致相同——对意大利葡萄
酒,我也是内行,只要有可能,总会大批量买进。
在一个热闹的狂欢节之夜,暮色四合时分,我碰到了这位朋友。因为酒喝多了,他跟我
搭起话来无比热情。这家伙扮成小丑的样子,身穿杂色条纹紧身衣,头戴系着铃铛的圆锥形
帽子。看见他,我非常高兴,不由想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
我对他说:“亲爱的福图那托,真是幸会。你今天的气色真是好极了。我弄到一大桶白
葡萄酒,可我不放心。”
“怎么?”他说,“白葡萄酒?一大桶?不可能!在狂欢节期间哪里弄得到它?”
“所以我不放心啊,”我答道,“我真是蠢得该死,竟然没向你讨教就把钱全付了。找
也找不到你,可我又生怕错过一笔买卖。”
“白葡萄酒!”
“我不放心。”
“白葡萄酒!”
“我一定要搞清楚!”
“白葡萄酒!”
“既然你有事,我去找卢克雷西。只有他才能弄清楚。他会告诉我”
“卢克雷西分不清白葡萄酒和雪利酒。”
“可有些傻瓜楞是说他的味觉跟你不相上下。”
“快,咱们走。”
“到哪去?”
“去你家地窖。”
“老兄,这可不行。我不能瞧你心地好就麻烦你,看得出,你有事。卢克雷西”
“我没事。走吧。”
“老兄,真的不行。有事没事倒不当紧,就是冷得要命,我觉得你受不了。地窖里潮湿
难耐。四壁都是硝石。”
“还是走吧。冷算不了什么。白葡萄酒要紧。你怕是上当了。至于卢克雷西,他根本分
不清雪利酒和白葡萄酒。”
说着,福图那托就架起了我的胳膊。我戴上黑丝绸面罩,裹紧短披风,任由他催促着打
道回府。
家里一个仆役也么有,都溜出去欢度佳节了。我跟他们说要到次日早晨才回来。我还清
楚得指令他们不得出门半步。我非常明白,这样的指令,足以让他们在我一转身的当口,马
上就一个接一个走光。
我从烛台是取了两个火把,一个给了福图那托。我恭请他举步。穿过几个套房后,我们
来到了通往地窖的拱廊。我走下一座长长的回旋楼梯,叮嘱身后跟着的福图那托多加小心。
终于下完了楼梯,我们两个并排站在了蒙特里索府邸地下墓穴的湿地上。
我的朋友步态踉跄,一跨步,帽子上的铃铛就叮当作响。
“那桶酒呢?”他说。
“在前面,”我说,“当心洞墙上一闪一闪的白色蛛网。”
他转向我,醉意朦胧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
“硝石?”他终于发问道。
“硝石,”我回答说,“你咳嗽多久了啊?”
“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呃
呵!呃呵!——呃呵!呃呵!呃呵!”
我那可怜的朋友咳得半天说不出话。
“没什么。”他最后说。
“嗨!”我毅然说道,“咱们还是回去吧。你的身子骨要紧。你有钱,人人尊敬艳羡,
又得人心;你像我从前那样幸福。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能受得了。我反正无所谓。我们还
是回去吧,你生病,我可真担当不起。再说了,还有卢克雷西”
“别说了,”他说,“咳嗽算什么,又咳不死人。我不会咳死的。”
“对,对,”我答道,“说真的,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你,这个没必要,不过你千万得小
心啊。喝点美道克酒暖暖身子吧,这么潮。
话刚落音,我就从泥地上那一长溜酒瓶中拿了一瓶,砸掉了瓶颈。
“喝吧,”说着我就把酒递给了他。
他瞥了我一眼,把酒瓶举到唇边。他停下来,亲切地冲我点了点头,帽子上的铃铛随之
叮当起来。
“为周围那些长眠地下的,干杯。”他说。
“为你长命百岁,干杯。”
他又挂上了我的胳膊。我们继续前行。
“地窖真大啊。”他说。
“蒙特里索是个大家族,人口多。”我答。
“我忘了贵府的徽章是什么图案了。”
“巨大的一只人脚,金的,背景是蔚蓝色。那脚把一只翻腾的大毒蛇踩烂了。蛇的毒牙
都插进了脚后跟。”
“贵府的箴言是?”
“凡伤我者,必遭重罚。”
“妙!”他说。
喝了酒,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帽子上的铃铛又叮当响了。喝了美道克,我越发胡思乱想
起来。我们走过成堆尸骨和大小酒桶混杂的长长的夹弄,进入地下墓穴的最隐秘的地方。我
又站住脚了。这次,我放胆抓住了福图那托的上臂。
“硝石!”我说,“瞧,越来越多了。像青苔挂在拱顶上。我们在河床下面了。水珠都
滴到尸骨里了。快,我们趁早回去吧。你咳嗽”
“没什么,”他说,“继续前进。不过先让我再喝两口美道克。”
我打开用大肚酒瓶的葛拉维酒,递到他面前。他一口气喝干了,眼里顿时精光四射。他
哈哈大笑着把酒瓶往上一扔,还打了个手势,我没搞懂那个手势的含义。
我吃惊地望着他。他又打了一遍那个手势——一个希奇古怪的手势。
“你不懂?”他说。
“不懂,”我回答。
“那你不是同道。”
“怎么讲?”
“你不是共济会会员。”
“我是,我是,”我说,“我是,我是。”
“你?不可能!你是?”
“是的。”我答道。
“暗号,”他说,“暗号。”
“就是这个,”我一边回答,一边从短披风的褶皱下掏出把泥瓦工的抹子。
“开玩笑,”他惊叫着退后几步。“咱们还是朝前走吧,去看看白葡萄酒。”
“好吧,”我说。我把抹子重新放在披风下面,又伸出胳膊给他扶着。他沉重地倚靠在
我的胳膊上。就这样,我们继续往前走,去找白葡萄酒去了。穿过一排低低的拱廊,往下走,
直走,再往下走,我们到了一个深深的地穴。这里空气极为污浊,火把的火焰都给扑灭了,
只能幽幽地燃烧。
地穴最遥远的尽头,有一个更狭小的地穴,墙壁上是成排的尸骨,一直堆到头上的拱顶,
跟巴黎的大墓穴如出一辙。三面墙都是这样尸骨林立。还有一面墙尸骨已倒,横七竖八堆在
地上,都成一个相当大的尸骨垛了。尸骨倒下的那堵墙裸露在眼前。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
个地穴,或说壁龛。它大约深四英尺,宽三英尺,高六七英尺。看上去当初建造它并没特别
的用处,不过是支撑地下墓穴顶部的两根支柱间的空隙罢了,倒是背靠着坚固的花岗岩壁,
就在地下墓穴的其中一堵墙上开辟而出。
福图那托举着昏暗的火把,竭力朝壁龛深处仔细探看,可就是白费力气,火光微弱,根
本照不见底。
“往前走,”我说,“白葡萄酒就在这里面。至于卢克雷西嘛”
“他是假内行,”我的朋友一面摇晃着往前走,一边打断我的话。我紧跟在他的屁股后
面。眨眼间,他就走到壁龛最里面了。一看前路被岩石阻断,他不知所措地傻站在那里。片
刻工夫,我已把他拷在花岗岩上了。花岗岩壁上装有两个铁环,横间隔为两英尺左右,一个
环上挂着根短铁链,另一个环上是个挂锁。几秒之内,我就把他用铁链拦腰拴好了。他大为
惊骇,都忘记了反抗。我拔掉钥匙,退出了壁龛。
“伸手摸摸墙壁,”我说,“一下子就能摸到硝石。真是湿得厉害。我再求你一次,回
去好不好?不回?那我肯定得离开你了。走之前,我得先力所能及地关照你一下。”
我的朋友惊魂未定,失声喊道:“白葡萄酒!”
“没错,”我回答,“白葡萄酒。”
这么说着,我就在尸骨堆里忙开了。我在上文提过这堆尸骨。我把尸骨抛在一边,很快,
就扒出好多砌墙用的石头和灰泥。借着这些材料和那把抹子,我精神抖擞地在壁龛入口砌起
墙来。
第一层还没砌好,我就发现,福图那托的醉意差不多已消失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壁龛深处传出了一声幽幽的呻唤。这就是他清醒的迹象。这呻唤声不像是发自一个醉鬼之口。
随即,是长时间的高度静默。我砌了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然后就听到疯狂摇晃铁链的
声音,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为了听得更称心,我索性停下手中的活,一屁股坐到尸骨上。
待到叮当声最终平息下来,我这才重新拿起抹子,一口气砌上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墙
面这时也差不多齐胸高了。我再次停了手,把火把举过石墙。几线微弱的火光,照在了里面
的人影上。
突然,那个上了锁链的人影爆发出尖声长啸,仿佛要拼命吓退我。有一瞬间,我踌躇起
来,浑身簌簌发抖,但马上就拔出长剑,开始用它在壁龛里边摸索;可一转念,我却又放下
心来。墓穴构造坚固,我把手放在上面,感到挺满意。我再次走近墙边,锁着的人大声喊叫,
我也大声喊叫。他叫唤一声,我应和一声,叫得比他还要响,还要底气十足。我这一叫,被
锁住的人也就哑巴了。
已是午夜,我快完工了。第八层,第九层,第十层都砌好了。最后一层,也就是第十一
层,也差不多了,只消填进去最后一块石头,涂上最后一抹灰泥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