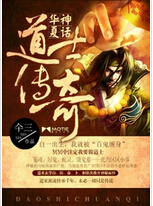��ѧʿ-��28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Ψ��������һ�𣬲�֪��ʱ���ܼ�����ʦһ�档���ĸ���Ů����������˵��Ψ�����ﵭ�кø����Ǽٻ����������彡�������������ӣ�Ҳ�����һ�����ϴ�ȥ�����ﵭȥ�����ˡ�����Ҳ֪���Լ��IJ��Ǻò��˵ģ�Ҳ��˼��ꡣ��������ﵭ��Ҳ�н��������ﵭ��Σ�ա�
��������������ˣ��β�����ݸ������������أ�
���������ﵭ��ο��������Ψ��Ҳ�������ģ�ҩ�ֿ���֮������ҩ�ֵ���ÿ�궼Ҫ������һ�˵ģ���ʱ�����ֿ��Լ����ˡ���
��������˵�꣬Ҳ�����飬�����ϴ�ȥ��
�������������˼װ壬������������������ſ��ˣ���Ψ���ڿޡ�
��������ͻȻ�䣬��Ψһ����У���������������ɽ�εؾ�ǧ�ɣ�������ѹ��֮�������Ӵ����£��Ͻ�Ԫ��������������ض��Ѿ�״������������ǧ�塣��¥������ɽ����һһ���������ݡ���
����������һ���߸贩����ʯ��ֱ���������߿�����������һ��
�����������ϵİ����ƿ��ˣ�������������Ͷ�����������������۵���ɫ��������ӿ�ȥ����������Ϊһ�塣
�����������˺ӻ������ʣ��������ݡ�
�������������о�����������ç�����١���������δ��������������ͨ��������벻�����Ȼ�������ﶬ���滨��ҩ�����������˲�ʶ���칤����
��������������һ���߸裬�����ͬʱ�ٽţ���������Ľ��ġ�
��������
�����������̼�ɽ�����ͯ�����ջ������ꡣ��ɽ֮�߹���ڣ���������**����������������ͬ���Ա�����������ʱ���������ɣ�Х��ɽ��һ���̡���
�����������ų�Хһ���������գ����ա�
��������һ�����շ磬������ԶԶ���ߣ��ﵭ����ӰҲ��ʧ�ڵ�ƽ���ϡ�
���İ���ʮ���¡�����
���������ξ��������¶�ʮ���գ�����һ����ˮ�Ѿ���ȥ����Ϊ��½��Ǯׯ�������ӣ����ϻ���������֧��Ų�����㽫��������ϡ���Ϊһ������Ƶ���Ĺ��ȣ������ھ��ֿ������зḻ�ľ��飬�����������õ�������ʰ�ĵز��������ٴ���ֺ�����͢Ҳ���������á���ˣ�Ԥ���е������ز�û�г��֣�Ҳ���Dz���֮�еĴ��ҡ�
��������������ˮ����ȥ�ˣ���ȴ���ӹ��ϵ����Ⱪ¶������
���������������һ�����ԣ�ֻ�еȴ���ȥ������ܿ���������˭��**��
����������ˡ���ϺӺӡ�����������ʮ����Ӷ���Ҳ��ֹ���˶��ٺ�Ǯ���������һ�ٰ�ʮ�������Ӳ������ɣ����л�ǣ�浽�����������ٹ�Ա��˾���ļ������࣬�����ûʵ��־���ŭ��
��������һ��������η籩��������֮�С�
��������Ϊ�˳��ײ���˰�����͢������һ������ר��С��Ļ���������һ��Ϊ�ף���许�֮���ټ����̲��������¡����Ժ����ʼ���˰���
����������������ģ�����������ͽ��������˶����ɵ�ȫ�����أ�һʱ�䣬����������
��������ͬ��ʵ����ʷ��ͬ���ξ����걾Ӧ�ٴη����Ĵ�����һ��Ҳ��Ϊ��讱�ǣ����ӹ�һ����û�з�����
�������������ij��һ�ȣ�����һ���ﵭ����֪����ʷ�����Ŀȫ�ǡ�
�����������ﵭ��������ȴ��һ�����¡�
����������˽����˵�������������Ԫ�����˶������ĺ����ѣ���Ȼ��ϣ�������������ڴ������**�е�ù��
����������վ����ʷ�ĸ߶��Ͽ���������������ϵ����Щ�ִ������Ĺ����ε�ζ������Ȩ��Լ��Ȩ���ʵ�Ҳ�������Զ�Ϊ��������������������������ʵ��������ټ����Ѿ��ȷ����ʱ�������ѿ��δ�ز��ܽ��й���������һ����·��ʮ�ꡢ��ʮ�꣬һ���ꡢ�İ��꣬����ʮ�������Ǻڰ���һĻ�ٲ�����ְɡ�
��������Ȩ����Ҫ��Լ��������˭��
���������ⳡ�ӹ����ķ粨���ܲ�������ϵ����ƣ������Ѿ����һ�������ĵز���ֻ��֪���ǵ�һ��������䵽˭��ͷ�ϡ�
�������������ʱ����Ѿ�����ʹ�ĵ�������ѩƬһ���ɵ��ʵ۰�ͷ����һ���Ѿ���һ�ٶ�ݣ����У����Ļ����������ڻƽ�ͷ�ϡ�
����������˵��Ҳ�֣��ʵۺ���û���κα�ʾ��һ�����У�����һ���������ǡ�
�����������ǣ��ı仹�dz����ˡ�
������������ǰ�죬��Ĭ�����õĻʵ�ͻȻ����һ���������ջ�˾��������Ȩ�����������۶�����һ�ݲ��ٵؽ����ʵ۹�Ŀ��
���������ܵ�������Ĺ��Ǹ����������ƽ������۸���ѩƬһ����������в�����ʹ���˵������ij¸��۵���
��������������ô˵���ƽ�������ռ��һ����С��Ҳӭ����������˾������������һ��Σ����
��������������һ��ûʲô��ı���ˣ��ۼ����Լ�����ʧ�ơ������������ӹ�һ��Ҫ�������������Լ���̨�������������永�Ĺ�ԱҲһ��ù����Ҳ����û���ȥ���ξ�����������������˵��������ɻʵ�ȴ��һ�����Ų�������Ȼ�ǶԻƽ�����˽�����DZ�Ǯ�Ķ�Թ����
�����������������ү�����ԣ���û��������������ˡ������һ���ײ������֣���ҪǮ�����ӡ��㶯������Ǯ�������������������
������������֮�£��ƽ�ֻ���óº��ó�һ�����������ɳº�ƽ����������������Ż��龢����һ�������£�ȴɵ�ˣ���������һ��Ҳ�ޡ�
���������ƽ�����֪��������º�������ﵭ��������������ù�����˻�����������ô���ܸ��������⣿
���������º�û�а취���ƽ���ĥ�����죬ֻ�ú�����Ƥȥ���Ź������Ź������¿���һ��������ƽ���ﰡ����С�ӹ��úܣ��϶����а취�ġ�
��������ƽ������������ӹ����������ϴλ�����Ȼ������ɽ���ɺô�Ҳ�и��������ݣ��������١��⼸�꣬�����Ǽ�����Ҳ���˵�����Ҳû���������������������������ϯ���ҡ��ң���ΪȢ����Ǿޱ֮��ƽ�������Ҳ���ǻ��ף����Ź�������Я����С��ȥ�겹�˸���»�µĹ٣�����ﱸ������ʱ���룬��ˮ���㣬Ҳ���Ǿ��ǹٳ���һ�����֮�ˡ�
���������������ƽ�һ��̫�Ƶ���ƽ������������̸��С�ӣ�������һ���Ȼ�м��ֱ��£�����Ʒȴ����⣬�Ǹ�ϲ����Ӫ��С�ˡ�����˾�����ӡ̫������ݣ�ƽ����Ҳ������������������������¹��Լ����������ɲ��ûƽ����������Ρ�
���������ܿ죬�ƽ��ھ��������ij���Ժ��¥����һ��Ƨ�����Ÿ���ƽ������档
������������һ���ƣ��ּ��������Ӳˣ��ƽ���������İ��ơ������˻��⣬�������˳�ȥ�����ſڰ�ס��
�����������а����������ƽ�װ��һ��Ц�ݣ����������ڹ�»�¹��ÿɺã���
��������ƽ����Եó��죬������Щ������ͳ��ģ�������а��Ųˣ�������˵�����ƹ�������»�����ֵط����ֲ��Dz�֪�������˼�����Ǽ��գ�ƽ���������������һֻ��ƽij����м��пڣ�Ҳûʲô�뷨�ˣ�ֻ��Ҫ����ô��ңһ���������ع���ȥ����
���������ƽ�������Ц����������ƽij��������Ȩ�����Ǽٻ�������Ҳ������Ȣ����Ǿޱ�������Ź��������֦�������ۼҵ���ù��ֻ����С�������Ѿ��ֿ��˻���һ��Ҫ���ҳ���ɡ�
���������ɱ����ϣ��ƽ��������ȵ�˵�������ǰ���꣬������æ���еĵط�����Ҳ���չ˲��ܣ������½⡣��
��������ƽ�������һ��ھƣ������еIJ���������ȥ���������֣����ƹ�����˵ʲô����ƽ���ﵱ�����˽������Ѿ����´������˵�����ݳ�ı�����DZ��֣����ڱ�����Ŀ���Ѿ��������˲������õ���һ�����ˡ��ƹ�������¾���һ�壬�㲻����ƽij�ˣ�Ҳ�������⡣��
��������ƽ����˵�úܲ��������ƽ���Щ���Σ��ɻ��Ǻ�����Ƥ���۾�һ�����߳������Ứ����ƽ�֣�ʲô����һ�壬�Ժ���Ҫ�����ˡ��ƽ���Ȼ�Ա������IJ��������κӵ��DZ߳���ô��©�ӣ�����������ͷ�ϣ�����������ŭ����ڣ��������ū�ŵ�����Ҳ���ѹ�������
�������������˹��֣���ƽ����������ʲô��ϵ�����������þ���һ�Ρ���
��������ƽ����Ц��Ц��ȴ��˵����ȴ����ȥ�˷������ϵĿձ��ӡ�
���������ƽ��ֺõ�����ƺ���Ϊƽ�������ϡ�
��������ƽ�������װ��һ���ܳ����������ӣ��ÿ��ŵ�����˵�������ƹ���������ǵ�����һ�ˣ�˾�������డ��ƽijʲô�ˣ���ô�������Dz�Ҫ�ɡ���
���������ƽ����������ƽ���������еķ��̣���ס��������ƽ������ƽ�֣��ѵ���ͼ������������ƽ����ˣ���������ʹ���߿졣������������Ҫ�����ʺ�û�лƽ��İ�ģ�ֻ�¶������ﵭ���ǰɡ����У�ƽ�֣��ﵭ��ǰ��ô���㣬�ѵ���Ͳ����һ�������ӣ����뱨���𣿡�
��������ƽ����ٺ�һЦ�������뾲Զ֮�����Ǹ�Ϊ����������������Ҳ�����أ�δ��һ����ɱ����Ҳ�������⡣��ʵ�����뾲Զ��˽����������˵��ȴҲ��������ϧ�ġ�������
�����������ڷ�һת���ֵ������������ƹ�����ղ��ⷬ��Ҳ˵��������������ס��ĵ�λ��ֻ�½����ҵ��Ƕ������ﵭ�ġ��ﵭ�ڻʹ����б��ƵĶ��������к���Ժ���������ڸ���˰����ͳ»ʺ�˵���������Ӵ���������з����������ƹ��������ѳֵ�˾���Ҳ���ˣ�ֻ�½����ҵȻ�ֻ�����ִ����ˡ���ˣ�ƽij�Żᵽ����������
���������ƽ�������Ӧ������һ������æ��ͷ����ƽ��˵���ǣ�����̡���������Խ��ƽ����Խ��˳�ۣ���ƽ����ʲô����������ǰ������һ��ɥ��֮Ȯ���������Ź���������ֻ�������·�ߵĶ��裬���ȴ���ۼ���ǰ�ô������л��ᣬ���������㡣
��������ƽ����ȴ���ʣ����ƹ�������������ʧ����û�У���
���������ƽ�����������ô����ʲô��˼����Щ���ã�����ƪ��������С��������������ô����û��������
��������ƽ����ȴվ�������������ֿ��Ŵ��⣬���������ر�����������������֮���������ߣ���������������˽Ե�֮���丸Ի���˺��Ϊ�����������£����������������顣�˽Ժ�֮���丸Ի�˺����Ϊ�������Ҹ����������Ӻ����������¡��˽Ե�֮���丸Ի���˺��Ϊ��������һ�꣬���˴���������׳�����Ҷ�ս������֮�ˣ�����ʮ�š��˶�����֮�ʣ������ౣ����
������������һ���飬����ٴ죬���鲢ï�����ûƽ�һ���巶����Ϊ���Լҵİ�Σ����ֻ����ס����ŭ�����������š�
�����������죬ƽ����ŵ������������ǿ����ת���ģ��Ϳ�����ô��������ʵ������¶���ƹ���δ�ز��Ǻ��£�������ҵ����⣬��˾�����ӡ̫���λ�ò�����ס�ˣ�ֻ�½���ʥ���¡����
���������ƽ�һ�����飬æ����Ҿ���أ�������ƽ����ָ�㡣��
��������������������ˮ�����������á���
��������������
���İ���ʮ��ƽ��ʦ
���������ƽ�����ƽ��������治���Ļ������ýг����������Ͷ���ֱͦ���ӣ�ŭ����ƽ����ȵ�������ô��ӣ���Ȼ��˵�������Ļ������ѵ��뱻�������𣿡�
��������ƽ���ﵭ��һЦ��ʾ��ƽ������������������ƹ�������������ƽ����ѻ�˵�ꡣ��
����������˵�����ƽ������������������������ǹ���������һ�������κθ��ڷ̰����µ��ˣ��ƽ���һ���Ų���������
������������ʵ������֮������������Ҫ����Ϊ��ˡ̰�۵���һ�ٰ�ʮ��������ȥ�����ס�������ͷ�Ǽ����ʱ���������Ǯ��౻��ˡ�л��ˣ�Ϊ�˾��������Լ�˳���ص��Ϻӵ��ܶ�����������ƻƹ����ѵ�����������𣿡�ƽ�������������룬Ц�������������飬������ҪʹǮ����Ȼ������������Ȼ�л������ڸ�ȥͷ�ۣ����ɲ��ű��²��ġ���
������������ȷ��ˡ�����Ȼ�����ˣ����ƽ�Ҳ���ò�������һ�㣬�ʵ۾���һ���۾������Ǯ���ˡ�
��������ƽ�������˵������ƽij����֪������̫���Ů�ǵ��·�Ҳ������ʮ��ǰ�ŷ���ȥ�ġ������������µף����Ͼ������£����·ݵĹ��п�֧��û�����䡣���ң����µ��ڲظ�����Ҳ���ˡ������ˡ���DZ����ӵ��֣����º�������˾��ȡ�����Ǯȴ����ˡ�л����ˣ����лƹ������Ź������ﻹ���˴�ͷ����˵�����ܲ������𣿡�
���������ƽ���������ͷ���ĺ�ˮ������������ô֪����ˡ����ͷ��Ǯ�����ˣ������ˣ�ǣ���ȥһ���ٺŹ�Ա�����ۼ�Ҳ�Ѳ��˸�ϵ��
����������ˡ������ˣ��ǽ���ǧ����в��ɡ���˵������ƽ�һ�������ݣ�ǰ���գ��̲����˻����������Ƿ�����һ��ն����˵��ˡ���dz�͢��Ա���������̣���͢�������ϲ��ÿ�����ν���̲��ϴ��
���������ޣ���ˡ���������뱣ס��ֱ��ն�������ˣ�Ҳ�����ۼ�������һ�ڶ�������
���������ƾ������ż����������ʣ���ƽ�����˵ʲô��ˮ�ģ��ϲ���Ϊ������������˵˵��ʲô����ƽ����Ц���ʣ����ƹ�������˵ǰһ��ʱ������������������
���������������£������Եǻ�����һֱ��������������ϧ������͢�����Ϸ��ӣ�����©�꣬���쳨�硣��ˣ�������ʮ�����𣬾�һ����ά�ޣ���ûͣ�������ˣ�����ô������������������ƽ���Щ���⡣
��������ƽ��������һЦ�����ʣ�����˵�ϸ��£��������DZߵĹ�����Ϊ��������û�з�Ǯ���������������������˼��졣���ڲظ������ȳ������ˣ���
����������˭˵�����أ����ƽ�Ҳ̾����������������ʲô�ط����ǿ�������ү�Ķ��������¼���Ҫ��֮���������Ǽ�ά��Ҳ����������������ȻҪ���ϳ˵ģ����������Ӷ�Ҫ�Ϻõ�ǧ���ľ������Ҫ���Ϸ��˽����ǡ��������ݶ���һƬ���ߣ�Ҳ���Ѳ��ƣ�һƬ�߶���Ҫ�������ӡ�����������������Ǯ�ѳ����ģ��Ǿ���һ���Ŀ�����������Ǯ��һ�Ķ��ٲ��ã���һ�ģ�Ҳ�˲��������������ԣ���Ǯ���Ƿ��Ƿ��Ū��������Ƕ��չ��ˡ�������ү��Ƥ�ӵ��������ӣ���Ȼ���ǿ��Եġ�û�취���ǹ�Ǯ�����ۼ���ʱ���ϵġ���ˣ�����ǿ���������ά�������ˡ���
������������˾ͺã���˾ͺá���ƽ������������Ƥ����������һ�䣬�ƹ���������ʲô�ط��ͳ�˽����������
������������û���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