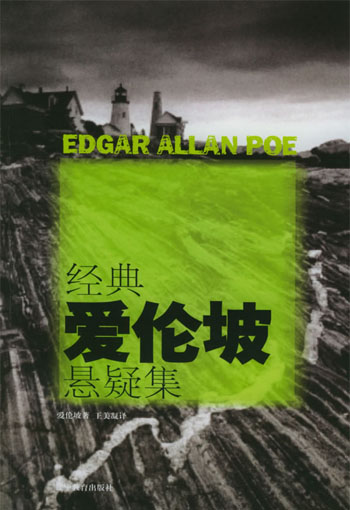堡门坡-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树春听着,问道:“云鹏兄弟,此信却从何而来?”贺云鹏道:“大同一带已非秘密可言,此地云集各路商贩,凡与商家有利的讯息儿自是传得甚快,没人理会那谁是谁非,尽知有大乱必有大定。”范忠庭道:“莫不是说若此言当真应了准儿,这其间竟是蕴了极大商机!”贺云鹏点点头,道:“商机无限。粮草、车架,上至染料衣帽,下到坛罐饮器,甚至北上内蒙贩那马羊牛,都是实实的大利!”
众人一时被这番言语挑得心动,眼前儿好一个豁亮的光景。
范理阳喜道:“少东家,云鹏兄弟这是个道儿,确可一试。”范忠庭沉吟道:“李掌柜,你怎看这事?”李树春听得显是激动异常,双手互扣,沉声道:“少东家,这实是少有的天道机缘,我等枉不上大同,一番大业便在眼前,只是要冒些险儿。”范理阳一皱眉道:“却有何凶险?”李树春道:“若欲争这等大买卖,必得在大同扎了根,开一家饭店自是不够,必得在粮行、杂行内立得下足跟来,在这几年时段内必挣得足额银钱方可行事。没钱,此等买卖显是上不得手。即便真立得住脚,若无兵事,便荒废了不少银钱。”范忠庭道:“经商,历来便是险道儿。要干成一番大事,淌得此点险原算不得险。我商家既要赢得大利,首要便是须抓得机遇,机遇一旦水逝,便是再也寻不得了。真若兵事不存,我天延村已将商铺开得这塞外之地,哪里就荒废了银钱?这倒是一石二鸟的机缘,是我等干大事、创大业的由头儿,一个字,干!”
众人听了,无不血脉贲张,情绪激动。姜献丰起身端起眼前一大碗酒来,通红着脸道:“少东家,诸位兄弟,想我东拼西杀半生,竟落得无处容身落脚,今遇各位,实是我姜献丰一生造化,投了明道,我愿随左右,拼了我一身血气,成就大事。”说罢,仰头一饮而尽,又道,“尽是碎骨粉身,值了!”
范忠庭当下便举起酒碗来,道:“云鹏兄弟,这一着路儿须得你走,你自便甩开了脚步,放手去做。有姜大哥助你,我等且腾得手脚,与我爹作得谋划,自便回来,我们携了手去干!”
李树春道:“想我与范老东家做得半世生意,原也有过这等想头,苦于无力无胆,脚步竟从未迈得出繁峙一步,你等年轻,此等想望便在你们身上实现了,且预祝云鹏兄弟旗开得胜!”
范理阳笑道:“姜大哥,你那一碗不算,再倒上!”姜献丰大笑道:“好,再来!”说罢又是满满一碗。
众人正待要干,却听得楼下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便纷纷放了碗。
贺云鹏放下碗来,挑帘儿叫道:“伙计,伙计!”
那伙计儿早一溜烟儿跑进来,头上满是汗渍。
“各位客人,有何吩咐?”
贺云鹏问道:“那楼下何事,这般杂乱?”伙计抹了把脸,笑道:“爷有所不周,今日‘大通庄’粮铺彭大掌柜在御河西又开一个庄子,名儿也自取了,叫什么‘大享庄’。今儿作东邀了大同名流在此聚会,并与数月前放出风儿,诚聘熟知书法人才撰那店名,谁的字大伙儿公认了,不惜重金。”
范忠庭噢了一声:“原是这事。”
晋商开店,极重店名;铺名好,可寓示生意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字写得好,亦示头面风采,芳流百世。因此,晋商原是极重这店名的书写。
贺云鹏笑道:“彭大掌柜?可是当年名誉大同府的彭百万彭世农?”伙计点头道:“不是彭世农,遍观大同直隶一带,谁还有胆敢称彭百万。”
众人听得一阵咋舌,姜献丰道:“既叫彭百万,似是身家贵重,有得极多银钱了?”贺云鹏道:“彭百万,其身家却何止百万,彭家祖上从明初至今历来以经商为业,经数代人滚动累积,现仅大同便有商铺不少二十余家,以煤炭、粮、油、木材为主,掌管着本地近三分钱货通畅,这尚不算在太原、直隶等地开的铺店。百万已是本朝初年的名号,现下,总有数百万资产。”
姜献丰大惊道:“世间竟有此等豪富!”
贺云鹏笑笑道:“姜大哥难道没听说,商海茫茫,原是藏龙卧虎,不可限量。纵观咱山西地面,不管在哪时哪地,你道那街上,尽自匆忙,却难料其间竟有一二怀揣万金之人,自不可小觑了去。这彭世农,我朝入关初,便有个事儿。”范忠庭兴趣极大,问道:“何事?”贺云鹏道:“当初,摄政王多尔滚率兵西下,经大同,因随从护架规模极大,竟无处落脚。后来有人支了个地儿,你道何处?正是那彭家大院,数百人的护架进了那院,大门一关,竟是纹丝儿不响,甚大气派!”
范理阳奇道:“数百人,竟是比得我半个天延村大小了!”贺云鹏道:“有过无不及。”范理阳跃跃欲试道:“我们何不下去看看此等人事头脸来,不定我等此辈也有这等阔绰;即便没那命运儿,沾沾福气也是应当。”
当下,贺云鹏便问那伙计:“不知这彭世农来了没有?”那伙计道:“来了,当厅便是,余外还请了十数人的评判,为字好字坏作评。爷们,下去瞅瞅热闹也好。这彭百万出手极是阔绰,三个字就是三百两的价码儿,一字百两!天可怜见,抵得上我这一辈子的想望了!”
贺云鹏道:“我们下去看看!”范忠庭道:“一睹百万风采,这大同当真不枉来得了。”李树春催促道:“走,走!”
一行人下得楼来,沿正门对过敞了一大北门。里边却是一宽阔院落,院内早聚了一圈人,约在百人上下。透过人缝,正中台上摆了一张桌子,椅子正中坐了一位年约五十,身穿蓝绸缎袍儿、头戴一六合统便帽、额头饱满,阔脸耸眉,唇下留一丛略显花白胡子的老者。两边倒八字排了两张桌子,端坐着几位士绅模样的或年长或中年的人物,兀自端座不语,眼光纷纷看着那台下。
贺云鹏小声道:“想那正中必是彭百万了,两边或是评判!”范忠庭点点头道:“想来正是。你且看那台下!”
几人捡了人缝挤得前来,方见那台下两边各并排摆了两张条桌子,桌上笔墨纸张一应俱全。此时便有六七个各式人等正或握笔凝神,或额首细思,或张目四顾,不一会,便纷纷奋笔疾书。少顷,早有几个伙计早按顺序将那墨笔呈上台前案头,几个评判一一拿起,细细评味。
台下,一时俱寂,都直愣愣挺了耳朵听那判词,无不兴奋莫名,直要看那三百两银子花落谁家,却比自个得了般还要上心。
“左云州秀才张信仁!”伙计站得台前一声吆喝。
左首桌前便有一位老者站起,手捧张信仁那字,上前道:“彭东家,这张信仁乃是小篆,观这笔下,自有繁复怪异之处,字体亦是均匀对称,却少了些整齐划一之感,且不可取。”
台下那张信仁便暗自垂了头,苦笑着融入人群。
“大同举人刘谈秀!”又是一阵吆喝。
又有一位四十岁的中年人站起,手捧刘谈秀的字,道:“刘谈秀写的乃是草书,看这行笔之间,透了隶书的波磔,点划之间映带连绵,一笔可成,却少了些端庄肃穆,挂之殿堂,实有不妥。”
人群一阵笑,那刘谈秀便也掩了脸一头扎入人堆。
余下人等,莫不从用笔、结构、章法及神采、气韵、意境等方面逐一苛剖,若非藏头护尾,却力流字外,点画势尽,力收乏力,便是圭画深藏,有往必收,却少些中锋力度云云,竟是全不可取。
第二轮,虽有两人获得好评,却不料彭世农数度审视,摇头喟叹。
一时竟有些冷场。
“想这商家纵有万贯家财,却多了商气,失了儒气。”
“看得总是学些实实本领好些,三字三百两银子,端的让人眼馋!”
有人笑道:“老张,你不上去亮亮相去,忍让那三百两银子装了别人腰包么!”
那人笑道:“我有那等本事,自考了那状元去!”
“学那劳甚子作么?不如早早经商去,看那彭大老爷,三字就是三百两银子,眼皮儿都不眨一下,还是经商来得快!”
恰在这时,忽听得场外有人叫道:“我且试试,如何?”
那声音倒让范忠庭等一干人听得一怔,一回头,惊问贺云鹏:“理阳兄弟哪去了?”贺云鹏掂了脚,下巴往里一探,道:“那却不是!”
早见范理阳挤进场院正中站了,冲台上诸人一拱手,不卑不亢道:“诸位,我且试着写写。”
说罢,也不理会众人,当场握了笔杆,看着那桌上写就的“大享庄”三字,足足盯了半顿茶时光。
众人眼见得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毛遂自荐,口气如此托大,便早存了看热闹的心思,齐道:
“年轻人,放开手写去,没准那三百两银子恰是你的,也未可知!”
范理阳却不理会众人说闹,自低了头,抬头向那台上一众人笑了笑,顿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书罢,将那笔往桌上一扔,拱手道:“献丑了!”
一时,伙计将那字幅送上台前。
那几个评判纷纷挤前来看,半时竟不致一词,却不住点头称是。
彭世农却也坐不住了,起身凑前道:“怎样?”
内中有评判道:“看这三字,笔体苍劲,阳刚味重,用笔、结字、章法、墨韵均法意兼备,自有浓郁辽阔之境,又有稳重端庄之意。”
“笔锋藏露,形态方圆得体,虚实有度,气脉连贯,相辅相成,实是近年来难得的上乘书作。”
“神采气韵尽致,直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眩目,这后生年纪轻轻,不想如此成就,少见!”
彭世农举了那字,横竖细看,脸上尽是笑意,不住点头。
“恭喜彭东家得此宝墨,‘大享庄’当开门大吉!”
当下,彭世农捧了那字,却如宝贝般轻轻交与伙计。从桌后顺台阶下来,站在当院,竟冲范理阳一揖道:“这位兄弟,承让了。不想年纪小至如此,却有这等笔锋功力,实在让我等大开眼界!”
范理阳亦忙还礼道:“不敢,不敢,此等夸奖实是让我汗颜不止。”
彭世农笑道:“好,好!来人,取三百两银子,我当场谢了这兄弟!”
不料,范理阳却道:“彭东家,我只是偶尔凑凑热闹,却并非为三百两银子而来。若是无缘,如非本意,纵是一字千金,我范理阳亦无此适心;若是有缘,如有创意,纵是分文不取,难得彭东家看上我这拙作,亦是我后生辈的荣幸。今日与大同帮我晋商楷模彭东家有幸一唔,便是千里有缘。仅此之缘,三百两银子何足道哉!”
说罢,竟是一揖,道:“告辞!”回头便走。
彭世农却也不阻,大声问道:“且请留下名号,我彭世农在大同府给兄弟留着号儿!”
范理阳一笑道:“代州府繁峙县天延村落魄秀才范理阳便是!”
无意得了这个彩头,众人自是欣喜不已,纷纷簇拥了范理阳上得楼来。早有店家上来,不住恭贺。
“不想我这店面儿今日蓬毕生辉,迎得如此贵客,今儿这酒菜全免了去,算作我请各位客人的。”那店家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一招手让伙计端了一杯酒来,道“闯荡大同十余年,迎得宾客无数,不乏高官显赫,腰缠万贯者,可舞墨风雅,技压群才者,我这地儿却是少见得很,来,我敬各位一杯!”范理阳道:“不敢,不敢,掌柜的这等说去,实实让我汗颜不止。”范忠庭笑道:“敢问掌柜台甫?”那掌柜道:“兄弟姓刘,单名一个成字。敢问诸位来自哪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氏。”范忠庭道:“我们均来自代州府繁峙县,来此做点小本生意儿。”刘成噢了一声,指着范理阳道:“这位兄弟,小小年纪却是令人当刮目相看。”范忠庭笑道:“我这兄弟实有些才气,不过却是屡试不第,无奈才流落出来,跟随我等趟了这等商路。”
刘成摇摇头道:“以兄弟才学,入得我等商门,自有用武之地,及第且能有什么想头,纵观我晋北商家子弟,虽是有些生计头脑,总是铜锈气大了些,整日里呼三海喝,招摇显摆,更有那不成器者,便学那京城邋遢旗人习气,不学无术,竟提了鸟笼子四处闲逛惹事,唉,这岂不坫污我商家风范。繁峙商家有兄弟这等人品才气,自是福气。”
贺云鹏笑道:“刘掌柜,经营原也不错。这大同府‘翠云居’独一无二,这规模、气派自是没人可比了去。”刘成笑道:“这位兄弟看得却是表里颜面,却未想得我已连续两年负债经营,其苦外人自不可知。”姜献丰奇道:“看这情势,饭客一晚间便水流般十多席面出了去,如何说的负债?你这掌柜的也是不大气,莫不是怕我等抢了你等生意去么?”贺云鹏一怔,道:“原想开这饭店是好买卖,如何能负了债去?便说这一席酒菜,成本也不过三四两银子罢了,扣除店内各式开销,最少有得三四两银子收益,这等近四六分成的买卖,比之我等远途贩粮强的不知多少倍了,尚不论市集差价涨落行情、道中风雪凶险。”
刘成淡然一笑,晃了晃油光滑亮的脑门,道:“听这兄弟,该不是有意也开家饭庄么?”贺云鹏并不回避,一拱手道:“兄弟确有此意。”刘成叹了一口气道:“听得客人原没有开过饭庄,自不知这内里情势,你看我这整日里红红火火,倒是流水般的人气,却非流水般的银子。”姜献丰挪了身子,直对了刘掌柜道:“我却不解,难不成这客人吃了饭,不给银子,抹嘴就走么?”刘成摇头道:“那倒未必,银子是有,却是一叠子帐面儿,你且要去试试,遇得好说话儿的,自知理亏,当想了法了还上;若遇得不好说话的,倒认承欠你帐儿,却是没有,你如何说法?逼得急了,伤了颜面是小事,关系僵了下去,天长日久,便要寻出事体来。”范忠庭道:“看来,这饭庄儿亦不是好做的营生。”
刘成道:“这也未必。即是负债经营,我也是不得已,十多年了,我们东家生意已成气候,这‘翠云居’的牌子却是倒不得,诸位都是商道中人,自知商家重信重誉,这牌子就是信誉!想来我们倒是有缘,前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