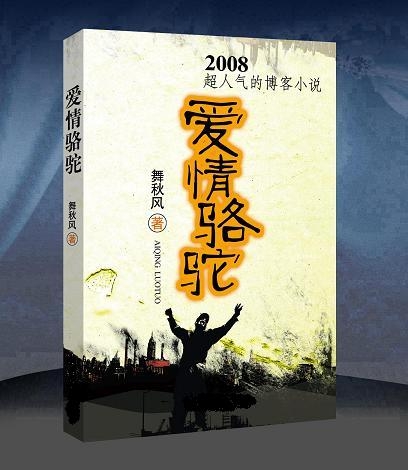骆驼祥子-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不去,万一丢了东西呢?
想不出主意。他又坐起来,弓着腿坐着,头几乎挨着了膝。头很沉,眼也要闭上,可是不敢睡。夜是那么长,只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
坐了不知多久,主意不知换了多少个。他忽然心中一亮,伸手去推老程:“老程!老程!醒醒!”
“干吗?”老程非常的不愿睁开眼:“撒尿,床底下有夜壶。”“你醒醒!开开灯!”
“有贼是怎着?”老程迷迷忽忽的坐起来。
“你醒明白了?”
“嗯!”
“老程,你看看!这是我的铺盖,这是我的衣裳,这是曹先生给的五块钱;没有别的了?”
“没了;干吗?”老程打了个哈欠。
“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儿粘赘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你看明白了?”
老程笑了:“没错儿!我说,你不冷呀?”
“行!”
第十三章
因有雪光,天仿佛亮得早了些。快到年底,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处处鸡啼,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到后半夜,他忍了几个盹儿,迷迷糊糊的,似睡不睡的,象浮在水上那样忽起忽落,心中不安。越睡越冷,听到了四外的鸡叫,他实在撑不住了。不愿惊动老程,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还不敢起来。忍着,等着,心中非常的焦躁。好容易等到天亮,街上有了大车的轮声与赶车人的呼叱,他坐了起来。坐着也是冷,他立起来,系好了钮扣,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雪并没有多么厚,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了;天似乎已晴,可是灰渌渌的看不甚清,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似的。一眼,他看到昨夜自己留下的大脚印,虽然又被雪埋上,可是一坑坑的还看得很真。
一来为有点事作,二来为消灭痕迹,他一声没出,在屋角摸着把笤帚,去扫雪。雪沉,不甚好扫,一时又找不到大的竹帚,他把腰弯得很低,用力去刮揸;上层的扫去,贴地的还留下一些雪粒,好象已抓住了地皮。直了两回腰,他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把雪都堆在两株小柳树的底下。他身上见了点汗,暖和,也轻松了一些。跺了跺脚,他吐了口长气,很长很白。
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他想往起收拾铺盖。老程醒了,打了个哈欠,口还没并好,就手就说了话;“不早啦吧?”说得音调非常的复杂。说完,擦了擦泪,顺手向皮袄袋里摸出支烟来。吸了两口烟,他完全醒明白了。“祥子,你先别走!等我去打点开水,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这一夜横是够你受的!”
“我去吧?”祥子也递个和气。但是,刚一说出,他便想起昨夜的恐怖,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
“不;我去!我还得请请你呢!”说着,老程极快的穿上衣裳,钮扣通体没扣,只将破皮袄上拢了根搭包,叼着烟卷跑出去:“喝!院子都扫完了?你真成!请请你!”祥子稍微痛快了些。
待了会儿,老程回来了,端着两大碗甜浆粥,和不知多少马蹄烧饼与小焦油炸鬼。“没沏茶,先喝点粥吧,来,吃吧;不够,再去买;没钱,咱赊得出来;干苦活儿,就是别缺着嘴,来!”
天完全亮了,屋中冷清清的明亮,二人抱着碗喝起来,声响很大而甜美。谁也没说话,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怎样?”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该走了!”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
“你说说,我到底还没明白是怎回子事!”老程递给祥子一支烟,祥子摇了摇头。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虽然很费力,可是说得不算不完全。
老程撇了半天嘴,似乎想过点味儿来。“依我看哪,你还是找曹先生去。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那么,你一下车就教侦探给堵住,怪谁呢?不是你不忠心哪,是事儿来得太邪,你没法儿不先顾自己的命!教我看,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去,找曹先生去,把前后的事一五一十都对他实说,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你走吧,把铺盖放在这儿,早早的找他去。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赶紧走你的!”
祥子活了心,还有点觉得对不起曹先生,可是老程说得也很近情理—;—;侦探拿枪堵住自己,怎能还顾得曹家的事呢?“走吧!”老程又催了句。“我看昨个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迷头。我现在给你出的道儿准保不错,我比你岁数大点,总多经过些事儿。走吧,这不是出了太阳?”
朝阳的一点光,借着雪,已照明了全城。蓝的天,白的雪,天上有光,雪上有光,蓝白之间闪起一片金花,使人痛快得睁不开眼!祥子刚要走,有人敲门。老程出去看,在门洞儿里叫:“祥子!找你的!”
左宅的王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在门洞儿里跺去脚上的雪。老程见祥子出来,让了句:“都里边坐!”三个人一同来到屋中。
“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可真冷!”
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曹先生会走了。楞了半天,他问了句:“曹先生没说我什么?”
“那什么,没有。天还没亮,就都起来了,简直顾不得说话了。火车是,那什么,七点四十分就开!那什么,我怎么过那院去?”王二急于要过去。
“跳过去!”祥子看了老程一眼,仿佛是把王二交给了老程,他拾起自己的铺盖卷来。
“你上哪儿?”老程问。
“人和厂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羞愧,与无可如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
老程接了过来:“你走你的吧。这不是当着王二,你一草一木也没动曹宅的!走吧。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还给你荐呢。你走后,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有煤呀?”
“煤,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祥子扛起来铺盖。
街上的雪已不那么白了,马路上的被车轮轧下去,露出点冰的颜色来。土道上的,被马踏的已经黑一块白一块,怪可惜的。祥子没有想什么,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一气走到了人和车厂。他不敢站住,只要一站住,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进去。他一直的走进去,脸上热得发烫。他编好了一句话,要对虎妞说:“我来了,瞧着办吧!怎办都好,我没了法儿!”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象拔去毛的冻鸡。
“哟!你回来啦!”非常的亲热,她的眼中笑得发了些光。“赁给我辆车!”祥子低着头看鞋头上未化净的一些雪。
“跟老头子说去,”她低声的说,说完向东间一努嘴。
刘四爷正在屋里喝茶呢,面前放着个大白炉子,火苗有半尺多高。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忘了我啦!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车没有?”
祥子摇了摇头,心中刺着似的疼。“还得给我辆车拉,四爷!”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
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茶非常的烫,火非常的热,他觉得有点发困。把碗放下,刚要出来,刘四爷把他叫住了。
“等等走,你忙什么?告诉你:你来得正好。二十七是我的生日,我还要搭个棚呢,请请客。你帮几天忙好了,先不必去拉车。他们,”刘四爷向院中指了指,“都不可靠,我不愿意教他们吊儿啷当的瞎起哄。你帮帮好了。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先去扫扫雪,晌午我请你吃火锅。”“是了,四爷!”祥子想开了,既然又回到这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吧;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他认了命!“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①进来了,“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
刘四爷笑了。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
“来,祥子!”虎妞往外叫他,“给你钱,先去买扫帚,要竹子的,好扫雪。得赶紧扫,今天搭棚的就来。”走到她的屋里,她一边给祥子数钱,一边低声的说:“精神着点!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象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象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地上的雪扫净,房上的雪渐渐化完,棚匠“喊高儿”上了房,支起棚架子。讲好的是可着院子①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棚里有玻璃隔扇,挂面屏,见木头就包红布。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厨房搭在后院。刘四爷,因为庆九,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所以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天短,棚匠只扎好了棚身,上了栏杆和布,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刘四爷为这个和棚匠大发脾气,气得脸上飞红。因为这个,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厨子,千万不要误事。其实这两件绝不会误下,可是老头子不放心。祥子为这个刚跑回来,刘四爷又教他去给借麻将牌,借三四副,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借来牌,又被派走去借留声机,作寿总得有些响声儿。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拉惯了车,空着手儿走比跑还累得慌;末一趟回来,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好小子!你成!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教我活几岁也是好的!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事呢!”
虎妞在一旁,向祥子挤了挤眼。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
“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
寿堂正中还短着个大寿字,照例是由朋友们赠送,不必自己预备。现在还没有人送来,刘四爷性急,又要发脾气:“谁家的红白事,我都跑到前面,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撂台,×他妈妈的!”
“明天二十六,才落座儿,忙什么呀?”虎妞喊着劝慰。“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的看着揪心!我说祥子,水月灯①今天就得安好,要是过四点还不来,我剐了他们!”
“祥子,你再去催!”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爸的面前喊祥子作事。祥子一声不出,把话听明白就走。
“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象我就得象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那可也无法。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可把事都作了!”
刘四爷没答碴儿,想了想:“话匣子呢?唱唱!”
不知道由哪里借来的破留声机,每一个声音都象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刘四爷倒不在乎,只要有点声响就好。
到下午,一切都齐备了,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儿。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处处花红柳绿,自己点了点头。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冯先生马上过来看了看,叫祥子去买两份红账本,和一张顺红笺。把红笺裁开,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当时要再约两手,和冯先生打几圈麻将。冯先生晓得刘四爷的厉害,没敢接碴儿。牌没打成,刘四爷挂了点气,找来几个车夫,“开宝,你们有胆子没有?”
大家都愿意来,可是没胆子和刘四爷来,谁不知道他从前开过宝局!
“你们这群玩艺,怎么活着来的!”四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