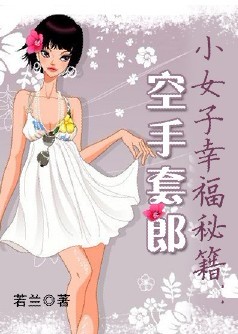幸福的拾荒者-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四篇:日记两则
2006年9月1日
今天我们说好要写日记,将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
昨晚我们到了香港。
大概睡了三个小时,大清晨6点多,突然醒来,蒙蒙眬眬看见他提着一条毛毯,正准备给我盖上。他劝我再睡一会儿,已经连续五十几个小时没休息,眼睛困得睁不开,可是意识上不想睡。
就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我们已经置身于香港某家医院;昨天的一切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窗外一片翠绿,高楼林立,宁静得连风声也听不到,只看见树枝在摇摆。外面是另一个世界,仿佛跟我们毫无关系。
没多久,护士已经进进出出,他非常有礼貌地跟人打招呼,说着不咸不淡的广东话。
8点整,主治医生Dr。Ma来看他,言谈间不断拍着他的肩膀以示鼓励。这次的治疗由三位专业的医生组成,Dr。Ma是著名的整形医生,Dr。Lin擅长骨科,Dr。Yu是眼科医生。
9点45分,他到医院的眼科中心做检查,他的右眼重创,眼球红肿,眼角非常刺痛,怀疑里面还藏有玻璃碎片,并且开始发炎。
检查的结果让我们放下心来,Dr。Yu认为那是血块,应该没有大碍,但他的视力下降,从1。5变成0。8,两只眼睛看的色温不一样,我不太担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恢复过来。
从手术室出来的那一刻到现在,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就像他所说,命能保住已经是万幸,眼睛没瞎已经是赚到了,剩下的只是容貌问题,能恢复多少他都无所谓。
“做了二十四年帅哥,还想怎样?”他问。
当然,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射雕》还没有完成。他问我要不要考虑换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今天让他最开心的,是护士Emily帮他洗了个头,清理了一大堆玻璃碎片和血块。
我尽量配合他的幽默,他笑个不停,已经学会了如何笑让伤口没那么疼。
奇怪,怎么会有人伤成这样还那么开心?
他说他也不知道,小时候腿断了,大人担心得不得了,他自己躺在床上还挺乐的。
他说可能车祸之后,大家对他太好了,仍视他为以前的胡歌,所以就算毁容了,大家应该也不会嫌弃他。他说,或许是自己还没有机会去面对残酷,说不定有一天他走出去,大家都像那天那位光线传媒的记者那样,看到他的样子呀的一声,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定那时候他也会难过起来。
我说他太勇敢了,就这样只身来了香港。他说我昨天太有效率,早上才说要去香港,他还没缓过神来,中午就动身了,让他完全没有思考的余地。
得到别人绝对的信任让你肯定了自己的价值,更清楚自己需要担当的责任。
临走的时候我给各方好友群发了一条短信:我会尽快带他凯旋归来,把更帅的胡歌还给大家!
他睡得很沉,中间突然醒来,很在意自己有没有打呼,以前我老是说鄙视他打呼。
我说好像没有听见,他摆出胜利的手势。唉,没打才怪。不过鼻子伤了,算了,别怪他。
今天老是想起远方的冕,心里一阵阵刺痛,很想尽情地哭。于是借故发点小牢骚,故作生气,趁机发泄,可是很用力才挤出了两滴眼泪。他笑忘我这是太阳雨。
他说他想打几个电话,可是我把他的三个手机都没收了,锁在保险柜里,他说我这样的行为会让朋友们责怪他、、、、、、
他说见到我们一家人很融洽,让他有点想家、、、、、、
他感叹有点无聊、、、、、、
今天他一直在问冕和小凯的情况,他说今天一定要打个电话给冕,他说这事也别怪小凯,他心情一定很沉重。
我跟他说冕的电话被压坏了,只能够等林林他们去看她,再打林林的电话找她。我说冕有她妈妈照顾,你放心好了。
“那、、、、、、你去买几本帅哥的杂志给我看,我可能会变好看一点。”
“你又不是怀孕。按你的理论,最可怜的是我,每天对着你,等你好了,轮到我要去整容了。”
他乐坏了。看着他笑得很开怀,我要加油!
2006年9月2日
今天下午2点钟拆线,发现起码拆了五六十针,还没把星期一要拆的那些算进去。
Dr。Ma亲自操刀,我站在他的床边,手握着老袁送给他的佛珠、、、、、、
他表情平和,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是在鼓励Dr。Ma不用担心他会疼。
这次伤得最厉害的是左边 眼帘,整块眼皮被切掉了,但搁在那里没断,医生说这叫游离皮,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硬把它缝上去,所以这块皮很有可能不成活,这样会影响他右眼睁闭的灵活性。不过Dr。Ma说这个位置也可以整形,一切只能看我们的运气。
如果他不是演员,脸上多几条疤也没什么,反而更有男人气概。
没拆一针,血就一条一条地渗出来,Dr。Ma问他疼吗,他笑了笑,说不疼。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终于将最影响容貌的线全部拆掉,还留下了一部分等下星期一拆。
Dr。Ma说之前为他缝线的医生很用心,可惜用的线不够好,怕伤口长得不好看,所以在第三天就为他拆掉,宁可让伤口自己愈合。
下午3点多,《射雕》的编剧Please来看他,她由衷地说:“其实你现在很有型,很man!”他瞄了我一眼偷偷地笑:“有人也这么说。”
临走时两人谈好了让他尝试写几集《射雕》的剧本,看来他这次养伤还过得挺充实的。
晚上9点多,他让我帮他剪头发。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突发奇想,他说反正又不用见人,大不了剃光。别人会觉得他肯定是疯了,没想到这才是他的“正常”行为。
他发生意外以来最想做的两件事都完成了,一件是洗个头,另一件是剪个头。
他今天又提出让我考虑换个人演郭靖,他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剧组这样耗下去损失太大,如果其他演员没有档期,也是要面对重拍,就算他好了,但很有可能两张脸前后不衔接,对于一个作品来说,是很大的缺憾、、、、、、而对他来说,不演郭靖,只是少演了一部戏、、、、、他让我一定要理智地去思考。
我笑了,我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事情发生了,你自有方向。
本来无一物,不赚一部戏的钱,就算赔钱了,那又算得了什么?
oh~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
oh~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
惟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
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
终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
第五篇:漫长的过程
四天两次全麻
8月31日到9月19日,他在香港港安医院度过了三个礼拜,他希望可以出院过生日。
9月8日和9月12日分别做了两次手术。第一个手术是鼻子,医生说鼻骨像鸡蛋碎裂开了,必须重整和扶正。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他鼻子插着两条塑料管,一直插接近额头的位置,四天里他吃饭用嘴巴、呼吸用嘴巴、说话用嘴巴,所以吃起一顿饭来,吃一口呼吸一下,再说一句话,很忙,喘不过气。当两条管子在第四天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惊讶于它的长度。
取出管子的当天,就是要做第二次手术的那天,这次是做眼皮,因为右眼盖的那块皮在车祸中被玻璃割开了,医学名称叫游离皮,当时医生硬把它缝回去,但说过可能不成活。我们看着这块眼皮逐渐变黑,把右眼往上揪,马医生当机立断,建议马上植皮。那块皮是从耳朵后面取过来的。
四天里他做了两次全麻。到第二次他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的时候,已面无血色,一下子苍老了二十年、、、、、、
朋友们来信说他这次真的吃了很多苦,除了皮外的伤,还有心里的创伤,虽然出事之后他一直表现乐观,几乎让我相信他会轻松接受毁容的事实。
谎言被揭穿了
在医院里他过得很开心,直到9月4日那晚、、、、、、
那天他借我的手机发短信,刚好有一条短信进来,第一句是:“你写的悼文我收到了、、、、、、”他突然喊我的名字,声音很不对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跑过去把手机抢过来,之前因为怕他会发现,我已经把不该让他看到的短信都删掉了。
他愣愣地看着我,很久都没说话。我不吭声,心快跳出来了,听到他开口问我:“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终于知道冕走了,愣了很久,放声大哭了。我说你不能哭,不能动到眼睛,于是他把头放得很低,让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上、、、、、、因为冕将在翌日出殡,他说他要回上海,他要送冕一程,我说现在太晚了没有飞机,而且明天一大早的葬礼,又是在嘉兴,赶不及了。他说他不管,他一定要回去。他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他像个不讲理的小孩,又焦急又没办法,只好底着头又哭了起来、、、、、、
林医生来巡房,站在门口傻住了,不敢进来。他说他要出去透透气,医院破例批准了。我们拦了的士到了浅水湾,已经是午夜12点,他去便利店买了一包烟和一瓶酒,我没有拦他。因为他眼睛裹着纱布,脸上一道道伤痕,付钱时便利店里的职员都不敢正视他。
我们在海边坐了很久,说了很多关于冕的事情。他问我是不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必须完成自己的功课,冕做得很好,所以比我们早一步到达了彼岸、、、、、、
凌晨2点我带他到铜锣湾吃晚饭,每上一道菜他都会问我这道菜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吃每道菜之前,都会在心里告诉冕这道菜的名称,叫她一起吃。后来他告诉我这个方法很管用的,感觉冕就在身边。
回到医院已经是凌晨4点多、、、、、、第二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冕向他告别,他送了她一程,他把梦告诉我的时候我才缓过神来,接受了冕真的走了的事实,压抑了这么多天,突然间崩溃了,号啕大哭,他也哭了、、、、、、
我把背着他写给冕的悼文拿给他看,我说可惜她的家人觉得不够严肃,没有选用,他看了后又哭又笑,说我写什么呀乱七八糟。当天晚上他把它放在他的博客上。
事后他借我的手机发短信给朋友,没有删掉,被我看到了。他说那一刻有几秒钟他很恨我,但看到我伤心的表情,他不忍、、、、、、我还挺难过的,问娜娜,这世界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娜娜说,只要坚持到底,一切假的到最后都会变成真的。这是我认识她以来,她最有含金量的一句话。
朋友自远方来
第一个星期,李国立和副总Sandra天天来陪他。第二个星期他姑妈也从无锡来了,住了两个礼拜。其间《射雕》剧组的人陆续来看他,包括导演、美术、武术、剪接、化妆、服装等等。他的好朋友们在我的过滤下,也一个个来看他,包括晏晏、阿宝等,娜娜也请了假,来看他的时候已经是住院的最后一天。出院后林依晨、黄磊、孙莉、何炅、炅的朋友晶晶都来看过他。陈秀雯和顾美华还请他吃饭,陈还准备了一大包电影VCD碟给他,顾一见到他就把自己的墨镜摘下来给他,硬叫他换上、、、、、、中秋节快到了,他的父母也来了,在香港陪了他一个月。我跟他开玩笑说这段时间我既做了私家看护,又过着迎送生涯。
住院期间我们偷偷溜出去几趟散心,走出港安医院的那条山路可以直通山顶,我开车载他和来看他的朋友到山顶吃过几顿饭。
他几乎没顿饭都吃猪蹄,还好有不同的店不同的口味,还有蔡妈妈(即我妈)每隔几天就会煮一大锅送到医院。除了猪蹄,对于香港极其熟悉的我尽量安排其他美食,包括金牛苑的越南菜、湾仔荣华酒楼旁边那家烧味、跑马地的一茶一盅、池记的粥面、满记的甜品,还有饭后的一大堆水果、、、、、、吃的是不愁,只是每次他都计较实在吃不下。
出院过生日
9月19日他出院了,因为他说最好能出院过生日。出院那天我们准备了两个蛋糕,和医院的护士们一起为他庆生,住院期间他已经跟护士小姐们混得很熟。
出院后他搬到西环的一所酒店式公寓,离我家比较近,方便照顾。
9月20日是他生日,当晚他请我们到港岛香格里拉吃自助餐,参加包括娜娜、阿宝,还有我们两个同事,大王也来了,他既是同事也是他中学同学兼死党。
9月21日,我说带他们去宝莲寺,开到半路,已经4点,听说宝莲寺快关门了,正好看到迪斯尼的路牌指示,我问他们要不要去,结果大家举手同意,于是我转了方向盘朝着迪斯尼开去、、、、、、
这段时间他表现得乐观和轻松。
可是在他乐观积极的表面,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黑暗,尤其在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后来我看了他那篇《照镜子》,才知道他的恐惧和彷徨、、、、、、
出院后马医生介绍他去做疤痕治疗,于是第一个月我们每天去做疤痕治疗师Alice那里“上班”,之后是隔天去、、、、、、每天回家他还要对着镜子继续做疤痕按摩,每天要戴压力面具八个小时,时间太长只能在睡觉时戴,可是呼吸困难、耳朵压得刺痛使他无法入眠。
离开医院,除了疤疗,已经没什么可做了,只能等,等待的岁月不好过,只能无聊地等了再等,看不到哪天会结束。他几天提出不太想做演员,觉得不走演艺生涯他比较容易掌握自己的人生。他曾经想过去国外读书,他说他想学剪接、、、、、、他说,可是怎么办呢,总得把《射雕》拍完。后来等了再等,他几次劝我换人吧。
他的心路历程只有他最清楚,没有人可以帮他走,正如没有人可以帮他去受伤,只有自己独自承担,自我调整。
去山东后,我们回上海了
11月13日他获准离开香港,我们一起去了山东。11月14日,公司一行八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会合在一起,出席冕的葬礼。他终于见到她了。
之后我们飞回上海,为了不让媒体接触和跟踪,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我不得已对外宣称他仍在香港。后来我们去看《暗恋桃花源》还是被拍到了,事先我们不知道林青霞也去,会有大批媒体,直到当天才知道,但后面几天已经没票了。他很想去看,我希望他可以从接触话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