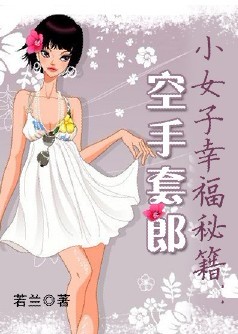幸福的拾荒者-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天晚上,医院特批我可以出去走走,Karen把我带到了海边,望着宁静的大海,我的情绪渐渐稳定,意识却去了遥远的地方。视线的尽头是 无垠的深蓝,海天连成一片。夜空并不晴朗,数目有限的星星在云端若隐若现,我不知道它们还能闪烁多久,有或者我们看到的已是它过去的光芒。世间没有绝对永恒的物质,但我相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让我们的世界有法可循,让生命有意义地存在。我们生活在物质的世界,我们以物质为基础来感知周围和自己。如若用心去感悟,生命似乎不应该依赖于血肉之躯,它的终结也远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想冕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呼吸之间。
这种想法让我心情平静而释然,它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天夜里,我梦见了冕。我送她去机场,她在梦里告诉了我航班的时间。醒来后发现那居然就是追悼会的时间,而在此之前我 并不知晓。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信仰,它很难用言语来解释。
11月14日,我参加了冕的葬礼。
我终于见到了她,静静地躺在妈妈的怀里。
我带去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集一份迟到太久的礼物。
凄厉的哭声划破了凝固的空气,冕妈紧紧抓住骨灰盒不原放手
没有人愿意放手,但冕终究是离开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相信她也不曾离开,因为我们不会将她遗忘。
此刻,想起她
“小伙儿,你好好睡吧!”
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我见过她两次,那都是在我的梦里。
当天(8月29日)
晚上要回上海,她一天都很高兴。我们说好了第二天要和公司同事去吃日本料理,然后去看“六零一”。 她很耐心地等我收工,等我卸妆洗澡,等我给车加油,等我买晚饭回来吃,等我收拾行李一起出发。
一路上她都在开怀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相当痛快。我早就习惯了她奔放式的乐观,并且深深被她感染。
她心疼我一夜未眠,让出了后排的座位方便我躺下睡觉:“小伙儿,你好好睡吧!”
我很快就睡着了,却不知是要去梦中找寻回忆里,她的影子。
一天前(8月28日)
我们完成了内蒙的拍摄任务,要和这片纯净的大草原告别了。她显得有些失落,坐在我身边,凝神望着车窗外的绿色。
她喜欢亲近自然,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她喜欢徒步穿越,背包旅行。她在旅途中认识了许多朋友,经历了很多故事,我永远是她最忠实的听众,因为我们志趣相投。
车渐渐远离了颠簸的山路,她在平稳的车厢里睡着了。我知道美丽的景色已经在她的梦中浮现——浅浅的微笑正挂在她的嘴边。
一周前(8月22日)
她今天一定感觉很幸福,即使她表现得相当羞涩。老袁给了她深情的一吻,虽然那只是庆生的玩笑,却也让我们看到她难得的满脸绯红。
谈及爱情,她也是滔滔不绝,不过话题总在她妈妈身上。阿姨秉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积极为她物色对象,希望女儿能够早日找到归宿。她却无动于衷,坚信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且为了保证美食这一最大爱好而渴望得到一份不在乎外表的感情。
内蒙的夜空繁星满天,不知她会对星星许下什么样的愿望。我们只想托星星告诉她,幸福并不遥远。
一个月前(7月26日)
《射雕》开机了!
这两天把她忙坏了,白天要拍定妆照,要给艺人作采访,要联系媒体,晚上还要写稿发稿。不过我想她应该早已习惯并且乐在其中。之前十四个萝卜丝饼的纪录就是她在忘我工作数小时错过了午饭的情况下创造的。
她在饿晕的时候仍然不会忘记提醒我接受采访的时候不要驼背,不要傻笑,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做表情,不要做太多手势,不要“人来疯”。她教育我的时候特别严肃,和平时简直判若两人。我经常虚心接受,屡教不改,每次她都说不管我了,但是每次又要把相同的话重复一遍。 在她的勤奋努力下,公司的企宣做得有声有色。我虽然嫌她烦,心里却觉得很踏实。
一年前(2005年)
我们是在大学生电影节的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见她是在她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我是电影节颁奖嘉宾,她是接待人员。
让她负责接待工作非常合适,因为她太爱笑了,让我自以为很幽默,话越说越多。渐渐发现其实就她一个人在笑我,其他人都在笑她。我感激地说她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她认真地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笑。
结果我真的很好笑地在颁奖的时候摔了一跤,
从此对她印象深刻。
在拥有的时候就懂得珍惜,就不会害怕失去。
若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就算不上真正拥有。
但愿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无悔地放下。
如果歌声可以穿越时空,我希望她能够听到。
乘着我的思念,载着我的祝福。
生日快乐
晚上去吃面条了,今天是冕的生日。
听大人们说,过生日吃面条是可以长寿的,所以也叫吃长寿面。现在想到冕会有些难过,但时间不会太久,因为记忆里的她永远是那么快乐。她的快乐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也作为她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所以今天我吃的应该叫作“常乐面”。
我去了一家素菜馆,饭馆蜷缩在旺角某个商业中心的六楼,门面不是很大,生意却很兴隆。这个地方要不是我娘“佘赛花”陈秀雯推荐,还真不知道也找不到。我点了两个菜和一大碗面。服务员整理桌子的时候多放了一份餐具,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巧合吧。
两个菜都挺有意思,一条“鱼”和四个“蟹钳”。它们全是用素的材料做的,厨师花了很多功夫,从外形到口感都有八成像海鲜。以前在上海和北京也吃过几家素菜馆,也全都是这种假荤腥的做法。我并不喜欢这种感觉,看在眼里的和吃在嘴里的并不是一样东西,有点像望梅止渴。可看着满屋津津有味的食客,就知道这是个招揽生意的好办法。原本不吃素的人或许为此愿意尝试了;坚持吃素的人可以自欺欺人来这里换换口味又不会动摇了信念。
正因为大部分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忽略了内心的感受,我们这个世界才变得越来越不真实。我看着左边没有动过的餐具,想像着另一个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活着的人肯定都没见过,所谓“极乐”也只不过是对现实失望,在心灵上有一份寄托罢了。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服务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很大一碗,足足够六个人吃的。汤料很清淡,只有豆芽、青椒、香菇,却是一碗非常纯正的素面。面条的形状是宽宽扁扁的,弹性十足,很有嚼头。汤不怎么鲜,却很可口,喝起来有点像东北的饺子汤。我筷不离手,碗不离口,几乎把那一大碗全部吞下肚去,这才是今天的主角。我吃得满头大汗,相当痛快。自从知道冕走了之后,我在吃饭的时候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会把每道菜的名称、材料、味道在心里默念一遍,我总觉得冕能听见,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冕是个贪吃的女孩儿,但每次看她吃东西总是囫囵吞枣,都不晓得她知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我总是告诉她没有人会跟她抢。现在回想起这些,才明白跟她抢的不是别人,而是时间。如今我的食量很大,除了想多补充营养,让自己快点恢复,也想帮冕多尝些人间美味。奇怪的是,我体重的变化和食量的增加并不成正比,所以我总是怀疑她有分享到我的美食。
看着左边一尘不染的盘子,我突然想微笑。这是生命的密语还是神明的暗示?死只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是生死循环的一个过程。我知道她不曾离开,并且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她过着让我羡慕的脱离凡尘,不受打扰的生活。
今天是她的生日,是吃面条的日子。
我和何老师的故事
与何老师的相识要追溯到1990年,那时我才年小学二年级。我就读的向阳小学开设了许多课外兴趣辅导班,一部分课程的老师是从校外聘请的,何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那个时候我最想参加的是篮球班,可是太胖了,而且名额有限,我努力争取的结果是被全班同学取笑,无奈之下只好转投朗诵班。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何老师——很喜欢开玩笑的一个大姐姐。一向在课堂上挺直了腰板,左手握右手,老老实实背在身后的我,从来没想过原来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那么无拘无束。在学校里因为遵纪守法而经常受到表扬的胡同学,也学会调皮捣蛋了,何老师拿我没有办法,却有很“纵容”我。后来她说那是为了让我解放天性,这是成为一名好演员的第一步。在朗诵辅导班最后一次活动结束后,何老师吓唬我,说我太皮了,要把我带去校长室告状,急得我哇哇大哭,却乐得她哈哈大笑。她说 她在少年宫开设了一个话剧班,如果我参加就不用去校长室了,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一个星期后,我与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儿一起去了少年宫。在路上我问何老师有没有要带她去校长室,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从学校到少年宫差不多要走四十分钟,我那个时候爬六楼都喘得厉害,等见到何老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挑了个最近的椅子坐下,拿出垫板肆无忌惮地扇了起来。“这位同学的名字叫胡歌,今天第一次来上课。”直到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所有人都在乐呵呵地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低下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何老师的课上表现得那么害羞,一是因为环境陌生,二是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大,他们戴的是红领巾,而我脖子上挂的还是绿领巾。
那天上课的内容是单人无实物小品练习,题目是去医院探望母亲。那些戴着红领巾的哥哥姐姐个个训练有素,都演得很好,轮到我的时候都快干了的衣服又被汗水浸湿了。为了不被抓去校长室,我硬着头皮上了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语无伦次地对着空气说完了准备了很久的台词,僵硬地完成了一连串前后不接、毫无逻辑的动作,最终换来了持续不断的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真想地上有条缝可以钻进去,不过我想自己那么胖估计也会被卡住,还是会被大家笑话。
在经历了那次失败的表演之后,我很多年都没去过少年宫,对于校长室的恐惧也随着季节的转换而渐渐淡忘了。
五年级的时候上海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市招聘“六一”节目的小主持人,何老师是考官,我是考生。那次见面很短暂,我仍然以胖子的姿态出现,不过艺术表现力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我问她还认不认识我,她说,不就是那个被她吓跑的胡歌嘛。
三年后我们又一次相遇,从那时起,我与何老师的联系不再中断,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初二那年,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为了能够在舞台上更好地展现新有一代中学生的风采(老师曰),我又回到了少年宫,报名参加了主持人辅导班,由于想要展现风采的同学比较多,我们上课的地点被安排在面积较大的卡拉OK室——也是何老师和她的学生排练话剧的地方。
那天,高昂的学习热情让我比上课时间早到了几分钟,推门而入看见几个人正在那里排练话剧。当我认出何老师的时候她正在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似乎某位同学的表演达不到何老师的要求,使排练的进度受到了影响。
“想不想来试试?”
“好啊!”在确定现场没有当年观看我表演“探母”的“红领巾”之后,我爽快地答应了。
试戏很顺利,我加入了何老师的话剧团,还认识了好朋友庞云和孙捷。
我们排的第一台戏《红手绢的故事》在当年的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艺术节上获得了一等奖。从那时起,我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明白“演好戏要先做好人”的道理,我在话剧度过了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除了在少年宫排练,我们也是何老师家里的常客,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何老师的老公小周叔叔——一个不平凡的男人。
这种不平凡的感觉最早是在何老师关于他的言谈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位医术高超的胸外科大夫,对艺术有非常专业而独到的鉴赏力,还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然而很多年后,当我听他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对他的“不平凡”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白布已经盖到她身上了,医生给出了死亡的结论。我摸了她的手腕,发现还有脉搏,知道还有救。我叫来医院各科的大夫想组织抢救,可是没有人愿意配合,因为他们都没有信心可以把她救活,又怕要承担责任。我对他们说:‘你们按照我说的做,一切后果我来承担!’”凭着这份坚不可摧的信念和难以想象的镇定,他把何老师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去年5月的某个晚上,一辆闯红灯的警车向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去,出租车在空中翻滚了三百六是度后重重地咂在地上,而何老师正做在副驾驶的位置。经检查,她颅腔大量出血,内脏器官有不同程度的破裂,还有多处骨折。恢复意识后发现视神经断裂导致左眼失明,记忆部分丧失,语言和算术能力都有一定的障碍。
在得到了医生和小周叔叔的许可后,我约了庞云一同去探望何老师。虽然有人做伴,我们还是在病房外站立了许久,谁都不知道何老师会变成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和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迎接我们的是小周叔叔,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人也瘦了。
何老师斜靠在病床上,身上绑了石膏,手上插着各种管子。她的头发被剃光了,脸色很差,没有一丝血色。她轻轻唤着我和庞云的名字,无力的眼神中透射出牵挂和 喜悦。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说自己大难不死是上天的恩惠,她叫我们不要流泪,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坚强。她最惦记的是她现在的学生,他们正在准备一台话剧展示,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