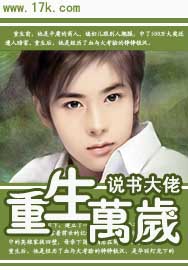吾皇万岁万万岁-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忽而一动,将她扯过去抱住,不紧不慢道:“你方至四品之位,就知道要货易官位、笼络人心了?”
这一句话如此露骨,令她心里登时一凉。
她抬
只觉这男人此刻神情深不可测、目光冷淡不像之前那个行为火热、数吻缠情之人。
好半晌,她才低头,“臣并非此意。”
他却道:“若非有你允其升官,想曹京也没这胆子敢第一个站出来参劾魏明先。”停了停,又道:“先放御史台,后去翰林院,连方怀都被你说动了,你当真是好本事。”
她虽是被他抱在怀里,可他说的话却令她脊骨寒颤。
此言似责非责,半是试探半是警告。她去何处有黄波报与他听,而他心智是那么机慎多敏,又怎会不知她做了何事。她的官职车宅皆是拜他所赐,她在外面所行诸事亦是顶着太子宠信之名才能成。他说得没错,那一夜若非她允诺曹京事后保其升官,曹京又怎可能贸然参劾魏明先。而曹京之所以肯信她,还不是因她受他宠信之名为众人所知。
他虽是对她如之,赏赐封赠事事逾例,浓情彻骨之时亦是体怀入微,可在这政事之上却容不得她逾矩一分。
虽付她奸佞之名,却不许真行佞幸宠臣邀官之举。他这是要让她知道,他给她的全是因为他想给,而她若想居功索物,那便是不知轻重之举。
她想着,心角觉一酸,轻声道:“臣并无不尊殿下之意。”
熟读史书之人有谁不知,佞幸奸传中的那些起伏命途皆牵制于为帝者的喜好怒怨。他今日对她好是因为他想,倘是它日他不再想要对她好,她又如何能够保住自己的官位性命?
半夜之间,他这一热冷之变令她陡然失神,惶然不知所措。
明明还未登基为帝,可这帝心重气却是如此明显,刹那间便将她从先前的旖旎浪潮中拖拽出来。
到底还是冷情,冷情之人。
他看了她许久,慢慢地收双臂,将她抱紧,道:“便允你所请,迁曹京调补左司谏一缺。”
她蹙眉,小惊了一下,不解他为何突然变了话锋,“殿下?”
他抬手将她的头按在胸前,低声道:“你若能少想一些,我便能轻松多了。”
她轻喃:“臣没有多想,臣只是真的琢磨不透殿下。”她伸手去摸他的左胸,轻声又道:“臣不知到底要如何做,殿下心里才能真的满意。”
他却道:“你已做得很好。”
她抬眼望他,“可殿下方才分明是责臣逾矩。”
他的长指顺过她背后长发,“你是逾矩,可我满意。”
她在他怀中一动不动地靠着,目光随着床头那宫烛细苗一起晃动,许久才又开口:“臣忽然想起来,幼时尼庵里曾养了条狗,那狗刚被人捡来时性子甚野,捡它的人便将它拴在墙根,时而喂它好些,时而饿它几顿,几番下来那狗也渐渐明白了,在那人面前变得乖顺了许多,捡它的人便让它夜守尼庵院房,它因顿顿都能吃上好的,便也乐于在门口作凶恶之象来吓退恶徒,本以为能够就此享食终老,却哪知几年后被外面的人下毒手宰杀烹了,捡养它的那个人也没见有多难过,只当是少了个看门之物罢了,又重新去寻了条弃狗来养。”
他听着,目光渐渐趋冷。
她喘了一口气,又道:“臣此时想起来,竟觉自己有些像那狗。”又侧脸对上他的眼,轻声道:“可臣与那狗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臣在想,倘若臣是那狗,纵是要被宰杀烹煮,也恨不能将一身骨肉送到捡养它的那个人盘中,让那人食臣之肉、饮臣骨汤、寝臣皮毛。”
他脸色骤然作怒,一把攥紧了她的腰。
她纤眉微扬,不惧却道:“臣爱殿下若此,殿下为何要怒?”
章六十二 登基(中)
待他开口,她便拼命从他怀中挣脱开来,拢衣下地,道:“臣从来不惧殿下之怒,臣自知臣之情意于殿下而言微渺不足,臣不奢望殿下能够付臣以真心,唯望殿下能够信臣,不弃臣。”
她望着床上那已是狼藉不堪的紫衣红裙,又道:“殿下既臣居位越,臣于殿下登基大典上便更当仅衣常服,横竖这祭服今夜已被臣污了,臣还有何颜面能穿此而上紫宸殿。”
他背倚床头看着她,眸色幽深。
这一张陡峭俊脸,是多么诱人又是多么冷峻,令她心头时时渴望又时时自卑。到底要做多少,到底又要做什么倾心倾情,倾此一身,倾此一生,却还不够辨不明他的心道不出她的意,想不通自己而又读不懂他。
她将头垂得极低,仿佛这样才能掩去她心底的浓浓失意,只道:“殿下既是无言示下,臣便退殿了。”然后飞快地对他行了个浅礼,便赤脚跑去外殿去拾她的裙裤官靴,胡乱往身上一套,便推门走了出去。
宫阶长长高高,叠复,在夜色烛光下更显冷凄。
她不该这样的。
她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以笑相迎,向不惊事,或有挑衅之行也多是顽闹之举,何曾如今夜这般动情动气、不管不顾地在他面前说出这么任性的话。
是不是一尝识他的点点温情就变得如此不知好歹起来摇头,又轻轻点头,眼角被风刮得有些痛,半丝湿意。
一过宣德楼前北横门,就见黄波马在候。
她随手乱挽地发髻蓬糟地。一身官服襦裙也是不齐不整。一路而来已受颇多宫人内侍们侧目以对此时见了黄波更觉不适。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便上了车。道:“回去罢。”
黄催马。在外小心地问她:“孟大人。诸事可顺?”
淡淡哼唧了一声。
黄波便爽朗一笑。又问:“太子殿下可还好?”
她在马车里坐着发怔半晌才答:“好。”
太子殿下怎可能会不好。他掌攥天下。权衡众臣。这世间哪有事情是他算计不了利用不成地,哪有人能敌得过他那深怀莫测地帝王心术。
她闭眼,忽然觉得一身沉累。
倘是这天下有谁能够比她爱他更多,倘是这天下有谁能够比她更愿负此侫幸宠臣之名,她情愿避位以让。
一月后乃有诏下式谕宰执及文武百僚内禅、登基二典诸例,各班直定序既成,又有谕昭朝中上下,以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孟廷辉为太子登基大典之前导官。
举朝哗然自不必提,便连京畿诸路重府大县的百姓们见到朝廷邸报后亦都是惊奇不已。
若依礼制,想孟廷辉无论如何也该上折谢拒此等恩典。不曾想她三日后只上折谢恩,竟是毫不言惭地受了这满朝举望之衔。
清议骤涌制重臣们愈发对她心生不满,多次当廷不齿与之为列、以表忿意;然未及半月闻御史台侍御史曹京被擢门下省左司谏、补孟廷辉右迁之缺,禁中有言道曹京此升乃为孟廷辉向太子所荐且先后不见曹京举奏参劾孟廷辉目无纲礼之行,因是人人皆信曹京乃与孟廷辉一党,而朝中新进入仕者更欲攀附孟廷辉以求荣禄。
那夜自东宫离去之前,她虽信口拒穿那典祭礼衣,可宫中仍是在离大典尚有半月余的时候将衣饰送到孟府、呈至她眼下。
是为太子之意,无人敢不遵从。
那绯章紫衣并红纱襦裙较之那一夜竟是愈显华盛,件件干净平整得像是新做的一般,且连襟袖处都加了金纹,与之同被送来的还有旒冠犀簪、金花钿,便是平日里女官上朝不允用的发托子之物亦是赫然在列,且俱都是用宫中金珠繁饰而成,个个都是耀灿夺目。
孟廷辉一一收下,恭旨谢恩,且是毫无推拒之态,更令来孟府送衣物的内侍官吏们咋舌。
转日便将此事说与朝中好事之人知晓,当下又是一风波。
皇上内禅、太子登基之日愈发临近,满京民情激跃,翘首以盼新帝新政、大典减赋,京官之间亦多有飞帖互拜、欲于新朝伊始之际拉拢关系之意。
唯独孟府之内声冷色寂,一副傲不理事之姿,无人知晓孟廷辉将来意欲何为。
大典当日,尚不到寅时,孟府的下人们便起来点灯,为孟廷辉入宫参行大典打点前事。
天还未亮,夜逢正黑,苍穹如鸦色大盖倾扣而下,好似遮去了天地间一切稀光重彩。
婢女捧了梳洗物去叩门,久不闻孟廷辉应喏之声,便轻手轻脚地进去,方欲唤她起身,却见她一头大汗卧在床侧,浑身发抖。
“孟大人”那婢女登时慌了,手忙脚乱地去摸火折子吹灯。
孟廷辉微微眉,淡声道:“无碍,我是夜里受凉,此时腹里翻搅得难受”
婢女伸手来探她的额头,竟是滚,不由惊道:“大人这样还要如何入宫?还是遣人去宫里说一声,大人”
孟廷辉费力坐起身来,脸愈显苍白,“我又没死,如何不能入宫?”她让婢女将衣物拿来,又道:“今日好生替我梳扮了。”
婢咬咬嘴唇,转身去拿东西,只小声又道:“明明是三伏热天,大人如何能在夜里受凉若是别的什么急疫,怎容得如此耽搁!”
廷辉开口欲斥,却使不出劲来,只闭了眼由她过来一件件替自己穿戴齐整,略略洗漱了下,便被扶过去梳发戴冠。
向来不胭脂色,今日苍色一抹红,竟似旁人俏容,难辨心颜。
待一身华衣祭服穿戴完毕,出府上车时天已微微发亮。
黄波在外等得焦急,见了她便急冲冲地催着上车,落帘时才瞧见她脸色有恙,怔道:“孟大人身子不舒服?”
孟廷辉额角俱是汗粒,却道:“我一切尚安,你赶紧让人驾车走罢,想来眼下太常寺和御史台的人都到德寿宫外次前列班候着了。”
就这么一路飞鞭驾车,到宫门时就闻皇上已出德寿宫,两面鸣鞭、禁卫诸班直及亲从仪仗迎驾升御座,将行内禅之礼。
孟廷辉趋步急行,到紫宸殿外的丹陛下乃见太常卿及阁门官分列在候,又有舍人从德寿宫那边过来,道宰执进言已毕、皇上降坐宣诏、太子已服履袍出东宫。
她听后不敢有所耽搁,忙随来传话的舍人一道,往东宫通往紫宸殿的西长廊行去。
刚至廊前百步,就见一众黄衣辇官们步履齐整,扛辇飞快而来。
舍人站定,她便也跟着站定,垂首以候。
背后冷汗骤涌,脑袋烧得昏沉沉的,只能看见那步辇缓缓降停,一人从上而下,步态雍容地朝她走来。
她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甚清,可却也不需看清楚——这一人,除了他还能有谁,除了那个尊贵无量雍华刚悍的他,还能有谁?
不由后退半步,两膝一弯,将跪行礼道:“臣孟廷辉奉旨前来,迎殿下入紫宸殿,为前导”
话没能说完,人也没能跪下去,当着大典众人的面,她被他一把拉起来拖至身前。
他出手迅疾,准而利落,攥住她的手就不再放开,横眉紧目地打量了她一圈,声音沉躁:“你病了?”
周围有小声悉娑窃语声,数束目光聚扫而来,皆是惊然。
她用力甩手,却抽不出他的掌心,只觉头又是一阵晕,道:“臣没病,大典要紧,皇上已在德寿宫降坐,还请太子殿下快些入殿”
他身定半瞬,开口道:“好。”
她小喘一口气,刚欲退身相让,却被他狠狠一拽,人跌跌撞撞地被他牵着往紫宸殿行去。
章六十三 登基(下)
短短数十步,她却走得有如足底踩针,步步紧颤。
一袭金章青衮在他身上那般契合,腰间玉剑白翠生辉,映着东边天际初绽的那一抹亮,淡淡眩目。
紫宸殿丹陛下已有诸臣在候,知阁门官、次管军官、文武百僚分班而列,人人眼中皆是惊而不信,一路目送他牵着她的手登阶入殿。
身后响起空厉的鸣鞭声,紫宸殿中金壁熠熠,空阔冷寂。
她急得要命,拼命地扭动手腕,且行且滞,欲挣脱他的钳控,心中不知他这是哪里不对劲,竟在这庄肃隆重的登基大典上做出此等大逆无纲之举。
他却将她攥得紧,口中低声道:“为何会病?”
她不答,忽而动怒浅喝道:“下!”头一阵晕眩,喉间大喘,心底又气又恨,气自己拗不过他的霸道,恨他为何如此心悉智慎事事洞明。
四扇殿门轰大开,有内侍舍人手捧德寿宫皇上所出内禅圣旨,上殿请太子升御座东侧坐。
他松手,深深看进她眼底,然后转走上龙座,面东而坐,长臂一展长服阔袖,金红色的蔽膝顺势而落。
外面又起一声鞭音,廷辉回头,见知阁门官已列班上阶,便深吸一口气,两手攥了攥裙侧,将掌心汗粒拭去,这才垂首缓步上前,在龙座之下向北而立。
待知阁门官、次管军官先后二十人殿称贺礼毕。朝中文武百僚乃依序而入。横行西向立。
她站在他座下。脸上强作定之色。直直地望着那些高冠重服地朝臣们一个个入殿、分列两侧。殿门之外。阶下青服散官们乌压压地站了一片。一眼望去似无止尽时令她头更晕眼更花。非得在袖中掐着自己地掌心才能稳得住身子。
朝中凡六品以上的女官们皆得以常服入殿。立于两制重臣们之后。虽不敢在这殿上相互耳语。可那些或遮或掩投向孟廷辉地目光却足以说明。这些女官们心中对孟廷辉能为大典之前导官一事亦是颇为不满。且先前太子当众与她执手入殿一景是令这些年华初放地女子们心生不豫之情。
从德寿宫奉旨而来地内侍舍人在前一展裱金御札:“皇上诏谕诸臣将校:‘皇太子仁圣。天下人所共知。皇太子可即,皇帝位称太上皇帝。平王仍称平王。与朕退处西都遂阳旧宫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在位三十九年。今乏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自朕心非由皇太子开陈。卿等当悉力以辅嗣君。共振天下之大业。’”
御札之言本在德寿宫行内禅之礼时就已由皇上亲自宣谕过。此时不过是登基大典之复例。可哪知座下殿中地两制重臣中。竟有人闻之流涕出声似悲不可抑。
皇上与平王共在位三十九年。从相争相伐到并肩舆坐四海定天下。收兵器治民生都合班以御世间万民。如今又携手退位让政终将这一世功业亲手交传给二人的唯一子嗣。如何能令追随二人数十年地老臣们坦然以受。
两侧臣众中一阵悉动,有人出列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