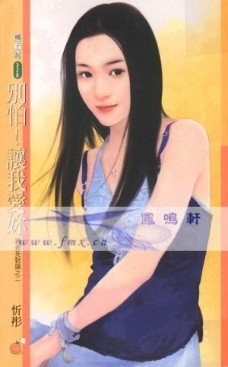告诉何冉我爱他-贱女孩 bitch girl-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妻子葵花儿般站在窗户边
窗户外沿是自由自在的蓝天
白云幕布上漂浮着繁华街道的倒影
是明媚的小孩子
中间隔了整整十八层
丈夫扯住妻子的胳膊
把她随意地提起来丢到窗户外
丈夫笑了
——我喜欢你在无边无际中的剪影
妻子也笑了
——我喜欢我在无前无后中的停泊
只
之前不是永恒
之后也不是永恒
作者有话要说: 我的第一篇日记
☆、【附】日记 2
第二篇日记写于2013年4月12日,题目是《周五将来干什么》:
我叫周五,我依赖于周五而生存。
那我,将来干什么呢?
我觉得吧,不结婚,不找工作。
是不是觉得我很堕落?
男子汉大丈夫,不成家,不立业。
甚至,最可耻的是,不养老。
我想流浪。
我想去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打一个月的工,在当地晃悠。
说赏景,太矫情;说体验民生,这不关我的事儿。
那我在那儿干什么?
——流浪。用心流浪。
什么时候没钱了,什么时候再干活。
挣餐费、车费,或者门票费。
如果有剩余的钱,买台相机。
买相机干什么呢?
拍不拍照呢?
拍什么东西呢?
我想去破旧的小餐馆刷盘子。——最好把我的手冻的满是裂痕。
我想去豪华的餐厅吃霸王餐。——最好把我打一顿扔到大街上。
我想去发臭的池塘抓鱼。——最好弄得我满身恶臭遭受行人鄙夷的眼光。
我想去有主的果园偷果子。——最好被主人发现被他家的狗咬一口。
我想去没路的荆棘林穿梭。——最好找不到路在里面饿三天。
我想去世界最高的山巅。——最好在回来的途中遇上百年不遇的雪灾。
我想去繁华街道的路边拉二胡。——最好碰上抢劫的拿走我面前放钱的帽子。
我想去学校旁边卖串串。——最好被城管连推带攘地轰走。
我想去荒芜的寺院求签。——最好被告知此生无望哀大于心死。
我想去深林里打猎。——最好与一头凶残的恶豹进行一场殊死搏斗。
我想去睡天桥。——最好是零下几十度的大雪天。
我想去讨饭。——最好几天没人开门没人理睬。
我想去监狱住几天。——最好在里面被打的鼻青脸肿无力敢还。
我想去精神病院。——最好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一个疯子。
我想去接触杀人犯。——最好他告诉我他心里最柔软最真实的不为人知。
我想去树底下遭一次雷劈。——最好死上几天醒来疯疯傻傻再一段时间。
我想去乘船遇一场海难。——最好能生还。
我不想死。
我只是想经历。
历经世事而活着。
我还是我。
我叫周五,我依赖于周五而生存。
我热爱生命。我热爱生活。
我会好好活着。
——————
说的是周五日记,我也并不是都在特定的周五才写,因为“周五”二字,其实是一个人名。我喜欢周五,原因是过了这一天,就是两天的周末休息时间,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算是象征着一种美好的希冀。
而且每篇周五日记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相同点就是我假想自己是一个男人,第一篇我已经结婚了,第二篇还没有。在这篇日记里面,我已经不想死了,我开始考虑一种我想要的、特殊的、惊世骇俗的活法。于是在我脑海虚幻的世界里,我开始想象过一种艰苦的生活,只有做出别人不想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我才能体验到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开始模拟自己是一个流浪汉,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我只要面包,根本不再去考虑什么爱情。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活着,不是好好的活着,而是真实的活着。我说不出来“真实”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一直认为,痛苦比开心更真实一样。
外国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亨利米勒,而他,很明显就是一个大疯子。百度百科给亨利米勒的评价是,美国“垮掉派”作家,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和业余画家,其阅历相当丰富,从事过多种职业,并潜心研究过禅宗、犹太教苦修派、星相学、浮世绘等稀奇古怪的学问,被公推为美国文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怪杰。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疯子,所以在日记中,也不自觉流露出了自己想过那种生活。我的疯狂,不只是在失恋的一个月中才有,其实前面也说过,在分手一年多再次见了何冉的第一面之后,我又有了疯狂的冲动,比如剃光头,比如把自己闷死在一间小黑屋里。我喜欢在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时,自己的小黑屋里长满了毒蘑菇。
我现在看着去年写的日记,才明白当时的我陷得有多深,所有的疯狂,都是为爱情而言,没错,我就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射手座女生。所庆幸的是,我已经不想死了,不管怎么说,疯狂都要比死好上很多。
现在的我,坐在电脑前分析一年前的我,真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是我以前写日记时也没有想到的。我想经历痛苦的实质原因,某一部分显然是想借助更大的痛苦来冲淡失恋的痛苦,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了。而做出一些很疯狂的举动,就像是男生对“当军人”的渴望一样,那是一种历练、一种生活对人性的打磨,经历过了之后,便会淡然如饱经风霜的老人,再也不用担心岁月风雨的无情侵蚀。
何冉曾经给我推荐过电影《燃情岁月》,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丢下了家中的一切去当军人。其实在外国的很多经典电影中,男人都对从军有一种莫名的情结,好像是男人证明自己力量的一种共性。就如我第一次见何冉时,他也提到了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后来被家人阻止了。
在日记中,即便我尽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人,可写出来的那种想法,却是只有女人才会有。我记得某个著名的外国作家说过一句话,意思是一个女人在写作时还记得自己的性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把那句话发在我的空间里,莹子姐在下面的评论是,“但在生活中,你必须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女人。”所以我觉得,若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女作家,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接近内心的真实感受。再或者,就算真切地想象出来了之后,也未必有笔力和胆量写出来。
我是疯狂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又迷茫了。我记得,在我以前跟何冉说,“我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女生”时,何冉冷笑一下,嗤之以鼻,“你?热情奔放?”也许是何冉离我的内心太接近,太了解我传统的本质了,然而即便是我自己,也不敢下一个确切的论断。
在分手一年之后的三次见面中,好像是第二次,我跟何冉说我很想去西藏,很想去鸟不拉屎的山村里指教,何冉没有很明显地鄙视我,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规划。截然不同的两种,也难怪在我问何冉跟我分手的真正原因时,他能够毫不犹豫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是一个空想家,所有的这些经历,想着永远比做起来要开心很多。就如我跟很多人说,我毕业之后要进施工单位,去工地上锻炼两三年一样,他们的反应都是很惊讶,“你没开玩笑吧?一个女生去施工单位,你会顶不住的,而且也不好玩。”
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三师父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三师父的态度是,“去工地上三年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有多白、皮肤有多好。”在此,我必须坦白,我是黄种人中偏黑的、黑种人中偏黄的,战痘人群中偏平坦的、平坦人群中偏战痘的。所以,可想而知工地上的生活该有多么恐怖。
三师父,就是我去年暑假在工地上认识的,皮肤很亮。所以,当我把这些正常人看来很疯狂的想法写出来之后,我也觉得有些不太实际。假如我真的很想体验生活,做收银员、刷盘子那种,几乎现在就有大把的机会。然而,我并没有去,我怕苦怕累,懒得动弹。所以,我始终是一个很懦弱的空想家,在爱情中,也丝毫不例外。
我暗恋朝晖师兄时,几乎没有任何表达爱意的行动,单靠平时的眼神和一句突兀的表白,把师兄吓跑也是应该的。而跟何冉在一起时,我也没有给他买过什么东西,没有用很实际的东西表达我的爱意。当我把这种愧疚的想法表达给何冉时,何冉很宽宏大量,“我能感觉到你很爱我。”对不起,也许从一开始,我就真的错了。
在后来写的小诗中,也有与这篇日记对应的一首,其实内容没有太大的关联,同样是写压抑而已,题目是《笼中狮》:
我再也看不到东海第一缕骷髅样的晨光
再也看不到西山最后一抹泣血的残阳
连同那夜的沉寂与荒凉
豹子的呻吟、羚羊的挣扎
我再也感受不到
不能独自走在通往巢穴的那道丛林
孤独如草莽一样滋长
啊
月亮月亮
我的毛发渐渐暗下金黄的色泽
我的爪牙也开始退化
我的眼睛涣散了深邃而悲悯的光芒
我怀念那广袤的草地和幽深的雨林
我甚至怀念
那嘴下的弱肉强食
晚餐的血肉流淌着胜利的骄傲
那是一种光明而伟大的竞争
我跑得过你,你便成为我的盘中餐
我跑不过你,我愿成为你的腹中肉
有猎人
也有对手
我不是出生在笼子里
现在却活在笼子里
多少个惨烈的暗夜
我仰天长啸
我要出去
可是笼子外面的世界
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笼子
只不过那里有更多的猎人、更多的对手
我要走到哪里去
对着日出的海、对着日落的山
做最后的朝拜
我蹲着
蹲成一座石头
周身散射出最美的金光
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
作者有话要说: 我的第二篇日记
☆、【附】日记 3
第三篇日记写于2013年4月16日,题目是《周五的脑子进什么了》:
不要!
不要再爬了!
不要再咬了!
啊啊!!不要
意识仍然处于不清醒状态,只觉得身体内有上千上万条小虫子在爬、在咬
不要!!!
努力让自己清醒一点点。
慢慢感受着它们的蠕动、啃噬。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感哟,仿佛全身是一具死尸——在它们咬的地方才有那么一丝丝的感觉,不甚灵敏,哪怕是痛的——尸体大部分尚且完好,只在苍白的腮面有点破皮,脚踝处有个不大不小的洞,这里它们忙着进进出出,与外界进行着不厌其烦的交流。这里是它们天然的舞池,欢快的乐曲、歇斯底里的吼叫、扭动的身躯、此来彼往的纠缠
哈!看它们多快活!
你知道吗?
它们有一个代表性的好名字,叫——蛆虫。
在你的身体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
死了无疑,活着也是这样的。
你的身体里有什么?新鲜到滴血的心脏、骷髅一样带有小孔的肺、黏糊糊的蛇一般的肠子被一群蛆虫占领,肆虐之后剩下的是什么?
你瞪着眼睛,死死地盯住天花板,脑子嗡嗡作响
你听到了吗?你体会到那种被啃噬的快感了吗?
舒服吗?
爽吗?
开心吗?
哈哈,不劳烦你们说我,我知道我的脑子进蛆了。
可是,神圣的你们敢不敢,敢不敢做个想象?
想象一下,你对面走来的美女,只被外面一层皮包裹着,里面是慢慢的、蠕动的——蛆虫。就像画皮一样。别眨眼,看着她,发挥你最生动的想象、透视一下。
你、还觉得她很美吗?
你敢试试吗?
——————
在那外面与内心同步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我害怕回到床上睡觉,我害怕看见我发霉的枕头。就连床上那只毛茸茸的小狗,也在默默地瞪大眼睛,只是没有泪水涌出。
那只小狗是阿琛送我的,在我大一上学期的生日时,从另外一个城市里寄过来的。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画面,我在南校的天桥底下翻找着我的礼物,因为阿琛没有提前告诉我是什么,所以我看到是只可爱的狗时,我一度以为它是一只小熊。
后来我发了我与这只小狗的合照在空间里,问这个娃娃的属性,除了大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之外,阿琛给我纠正了,“很明显是只狗好吧,天天啊,不到半年不见,你居然连你兄弟都不认识了!”后来,阿琛就非常恶搞地处理了那张照片,结果文静的我和可爱的狗,便都无法直视了。
阿琛是一个很喜欢小狗的人,家里养的有,当年那只名叫“艾贝”的小狗走失时,阿琛还伤心了好久。阿琛不甘心,还发了一些小广告,想要大家帮助把“艾贝”缉拿归案,只可惜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再后来,阿琛家里又养了小狗,依然是那种小小的宠物狗,她便转移了注意力,从“艾贝”丢失的悲伤中复原了。
我收到阿琛的生日礼物之后,就天天夜里抱着它睡觉,真的,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不例外。我觉得睡觉时抱着东西,才会有安全感,像是夏天放在床上的被子,就是用来抱的。
在很多夜里,我都是紧紧地抱着那只小狗睡觉,虽然它没有任何情绪。与何冉在一起时,我希望我抱着何冉睡觉,分手之后,这个想法也并没有变过。只可惜,何冉不是我的阳光,躲在了我背影之后,我再也见不到何冉了,我们已经永别了。
所以我心里时常会升腾起一种很大的恐惧,我不再躺到床上睡觉,我只是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外面暴雨如注时,宿舍漆黑的像一个坟墓,而我搭着蚊帐子的床铺,则是一具严严实实的棺材。我震惊在自己的想象里,手臂被头枕的麻木,没错,就像是有千万条小虫子在里面乱钻乱拱,只顾着自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