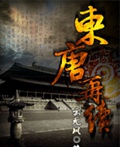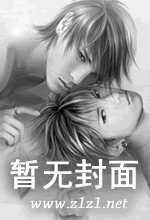东唐再续-第10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一迷信,再聪明也就化作流水,就如同那原本威震天下的高骈,坐镇扬州之后,就因为迷信,落了个晚节不保。此时的折嗣伦已然被李曜或者说李曜背后的高人“慑服”了,当下恭恭敬敬道:“如此某自然深信之,不敢有疑,不敢再赌。”
李曜依旧哈哈一笑,心道:“这算不算老子给将来的一位大名人取了名字?不知道日后史书记载折从远时,会不会写一句‘其名为李曜所取’?哈哈,有意思,有意思。不过,话说回来,折家真真崛起,好像就是从折从远开始,他今年出生,十几二十年后,不知道能不能为我所用?”
李曜于是回忆了一下,折从阮早年在李存勖部任河东牙将,领府州副使。李存勖灭后梁称帝以后,又授折从阮为府州刺史。后唐长兴初年,折从阮入朝拜见后唐明宗。后唐明宗以折从阮久镇边州,熟悉边地情况,所以特加捡校工部尚书,授他为府州刺史。
后唐明宗死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等条件,取得辽兵的援助,推翻后唐建立后晋。当时折从阮所辖的府州也在割让之列,消息传出,一时人心惶乱。至此,折从阮据险保境,以抗辽朝。石敬瑭死后,其养子石重贵继位,是为后晋少帝。后晋少帝恥臣于辽,反与辽朝为敌,并诏命折从阮出师伐辽。折从阮受诏后于次年春率兵击辽,深入其境,攻拔10余砦。不过后晋在将臣无能下累败于契丹军,折家在西北一隅的小胜并无法挽回汴京被破的命运。到后晋少帝开运初年,朝廷加封他为检校太保,及本州团练使,开运二年又加封他为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辽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侯等职。折从阮在后晋时虽保境有功,但可惜,其辖境仅为后晋西北边境一隅之地,幽云等北边重镇尽为辽朝所有,辽朝以此为基地不断攻掠中原。
到开运四年初,辽终于攻入后晋首都开封,后晋也就寿终正寝了。当辽兵攻入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诏抚后晋旧臣归附。这样,折从阮率众归从刘知远。当辽从开封退兵后,折从阮随刘知远迅速进占洛阳和开封,刘知远入开封后,揭开了后汉的历史,刘知远也就是后汉高祖。后汉高祖升府州为永安军,并将原振武军所隶的胜州及沿黄河五镇都划归永安军管辖;同时授折从阮光禄大夫、杜校太尉、永安军节度使,府、胜等州观察处置使等职,并特赐功臣名号。
刘知远做了11个月皇帝死去,他的侄儿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后汉隐帝加封折从阮为特进、检校太师。受封后的第二年,折从阮举族入朝晋见后汉隐帝,后汉隐帝又特任命折从阮子德扆为府州团练使,加授折从阮为武胜军节度使。
后周太祖郭威称帝,折从阮以北国雄镇,国朝重臣的地位,在奉表称藩后,后周就加封他为同平章事,等于是有使相的地位了。历任宣义、保义、静难、永安等四镇节度使,太祖将崩又以为世宗顾命。因镇守边关有功,去世之时,后周世宗赠为中书令。
李曜之所以这么肯定折从远今后必为使相,原本就是因为这些史实。不过他忘了一点,作为一只正在开始扇动翅膀的蝴蝶,他不应该忘了自己的存在是有可能给这个世界造成各种变故的,有时候这些变故不一定会出现,但一旦出现了,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
原本历史上的折从阮一生经历了五代时期最混乱的时期,又遇上契丹南下覆灭石晋的危机,府州直面契丹的西京大同府与西南路招讨司,作为河东地区抵御契丹入侵的第一道关卡,戍守边境、维护百姓,对于中原朝庭或华夏民族而言功不可没。特别是后周代汉后,因为北汉割据太原,隔断府州与汴洛的联系,而西面又阻于世仇的平夏拓拔部,折从阮仍奉表不绝,及至于二度入阙,其气节令当世感佩,更重要因为折家军的精骑无双,牵制北汉与契丹无法全力南下,才让后周世宗可以放手进行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
而在这个世界,折从远还会不会是那个折从远,是与历史上的折从远一样,还是根本挑不起折氏的大梁,又或者比历史上更加出众?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已经成了未知数。
李曜和折嗣伦二人因为此事一打岔,在门口耽误了片刻,此时事情谈完,担心中折宗本急切,不敢在拖延,快步走入中堂。
折家的节堂不比中原习俗,不必脱鞋跪坐,而是直接用的胡床椅凳。李曜虽然偶尔会有点大汉族主义,但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赞成民族平等的,他实际上应该算是“大华夏主义者”或者“大中华主义者”,对于椅凳,他绝无这时代一些守旧之人那种看不惯的心态,反而极其欣赏。
毕竟,作为后人,跪坐是真的累。要坐着舒服,还得用臀
“李某来迟,劳折兵使久等,恕罪,恕罪。”李曜进来就冲折宗本一拱手道。
折宗本反倒不像折嗣伦先前那么急切,而是笑着起身拉李曜坐下,这才自己坐下,说道:“大清早就叨扰李军使,本是老夫不是,李军使何谈恕罪?不瞒李军使,此番请军使前来,乃是前方探马探知一桩新的军情,事关重大,老夫不敢擅专,是以请李军使过来,参详一番。”
李曜点头谢过,然后问道:“未知何事?”
折宗本盯着李曜的眼睛,冷静地道:“前方探马探知,夏州增兵一万,已经开往府谷。”
李曜眉头一扬,反问:“夏州增兵一万,再来府谷?”
“正是。”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李曜眼中杀气一闪,寒声道:“拓跋思恭好大的胆量。”
折宗本笑道:“拓跋思恭的胆量一贯很大,当日他实力不济,尤敢挑战黄巢逆贼,如今羽翼丰满,自然更是胆量惊人。”
“胆大包天才是吧,折兵使?”李曜面色坚毅:“即便拓跋思恭增兵一万,某也只当他是土鸡瓦狗,今番不打得他疼了,看来他是真当我河东无人,自以为可以来河东捡漏子了!”
折宗本微微一顿,问道:“我等可需再请些援兵?”
李曜摇头道:“不必,拓跋思恭如今必然知道某已经到了府谷,但他原本就有优势,如今有增兵一万,必然气焰高炽。不过不妨,此时反倒是一个机会。”
折宗本一眯眼:“机会?”
第088章 胜败之论
李曜点头道:“正是机会。”他微微一顿,问折宗本道:“不知折兵使手中如今可以调动出战的步兵、骑兵各有多少?”
折宗本打量了他一眼,答道:“八百步军,一千两百骑。”
“好,那么折兵使可知拓跋思恭所遣援军之行进路线,其军如今已然到达何处,是否分兵,领兵将领为谁,其能力、性格如何?”
折宗本脸色逐渐严肃起来,点头道:“李军使年少有为,堪称知兵。据探马回报,拓跋思恭所遣援军,领兵主将乃是其五弟拓跋思恩,此人在拓跋家其名不甚彰显,本无从知晓其脾性,然则先贤有云:‘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拓跋思恩在家中与拓跋思忠最为交好。拓跋思忠乃是死于追击巢贼,为人骁勇而鲁莽,仗义而粗豪。某以此料之,拓跋思恩之习性,即便不与拓跋思忠雷同,亦当不远矣。”
李曜听到此处,微微点头,但仍然眉头轻蹙。
折宗本知他意思,又继续道:“至于行军路线,此事非是某麾下儿郎不尽力,而是西北自古荒凉,从夏州并无直接到达府谷之路,欲要往来夏、府,则唯有在银州转道。然则银州与府谷自来少有联系,古道虽存,时断时续。此番拓跋氏前来,进入沿河五镇地界之前,其行军路线足可以千变万化,委实难料。”
李曜听了,虽不甚满意,但也知道折宗本的话乃是实情。古人再怎么说重视情报工作,毕竟比不上后世那般花样百出,其情报水准自然难跟李曜从书中看来的“国府军事统计局”相比,就更别提那些什么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摩萨德之类了。
不过即便如此,李曜听了,仍是点了点头,淡然一笑,微微拱手道:“折公,此番拓跋氏增兵一万,全军或有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人,而折公与某,可调动兵力不过两千五百,拓跋氏之兵力,足我六倍,闻之令人不敢相抗。”
他说到此处,微微一顿,但折宗本深知他必有下文,也不打断,只是微笑着看着他。
果然,李曜忽然胸膛一挺,峥嵘尽显,语如斩铁:“然则我等乃有五胜,而拓跋氏却有五败,以五胜而战五败,焉有不克之理?某来府谷之前,只想着固守城池,使拓跋氏不得深入,便以为胜,此时却敢发下豪言,必大败拓跋,令其铩羽,三年内不复有东望府谷之勇!”
这一番话,委实太过惊人,就连折宗本这等有信心守住府谷的折家家主都震惊了,忍不住问道:“老夫愚鲁,未知李军使所言五胜五败,其理何在?”
李曜并不故作神秘,而是坦然言之:“拓跋思恭身为唐臣,官至夏绥节度,本当深念圣恩,表率一镇,然则却未奉敕旨,轻开边衅;河东节度陇西郡王李公,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剪黄巢、黜襄王、存易定,为朝廷屡立大功,近日又为朝廷剪除一地贼寇,天下仰望,威及四海今番夏绥来战河东,实在以逆而击顺,名不正,言不顺,此拓跋思恭大义之败,某等大义之胜。”
折宗本点了点头。他对这一点看得并不是很重,但知道但凡说话,这等大义名头肯定要挂在最首要的位置,因此李曜第一胜败之论,说大义,他并不惊讶。
李曜也知道折宗本是聪明人,对这第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就好,没有谁傻到点破。中国人自来有这个习惯,后世盛行的潜规则,似乎也与这种习惯不无关联。当然此是题外之话,不提也罢。
于是李曜便继续道:“拓跋思恭早年窃据边城,自称留后,圣人宽宥,不予追责,他却不知悔改,数度为祸,虽则响应郑相公传檄,出兵助剿巢贼,然却胜少败多,累为贼笑,可见其人志大才疏,并不知兵。此番出兵,领军之将拓跋思谦、拓跋思恩等辈,籍籍无名,碌碌之辈尔;反观我河东,并帅深孚天下之望,号称军中飞虎,兵锋所指,无有不克,旌旗所向,望风披靡,昔日长安之战,若非并帅之黑鸦军杀破贼寇,黄巢等辈,沐猴而冠,如今却也将安坐长安久矣!而于府谷,折公久领边地,晓畅军事,嗣伦兄为政宽和,人竞相附,即使我辈,军中亦有嗣恩贤弟自小从军,身经百战,国宝虎子,智勇双全,某麾下有旅帅朱八戒者,横勇无匹,马前素无三合之将如此,拓跋思恭将才困窘,某等群贤毕至,此我人才之胜,拓跋人才之败也。”
折宗本点了点头,依旧不动声色。
李曜又道:“昨日散席之后,某曾驰马于府谷周围勘察地茂,知府谷背水依山,易守难攻,山下要道,险要难行,城池虽小,坚不可摧。拓跋氏远道而来,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唯求速胜,可免一败,然则府谷险要,贼兵再多,摆将不开,也是无用,粮草又为困窘,一旦有个闪失,全军必陷危局。如此我只需一支可于山上跑马之精干骑兵,游击其粮秣,疲而扰之,却不与其苦战,则久之拓跋必然困顿,战意全无,唯有撤军,某等再假意追击,其必恃众反击,我等于是佯退,放其遁走。待其谨慎全消,再全力追杀,贼军必败!”
折宗本听了两点都不甚在乎,听到这里却是老眼一亮,精芒一闪。
不错,地理优势,他作为沿河五镇兵马使,府谷城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建设起来的,他自然知道府谷的地理优势很明显。然则如何将这种优势利用起来,不仅击退敌人,甚至直接击破来敌,他就有些犯难了。哪知道李曜寥寥几句话,一场勾心斗角而又惊心动魄的大战,就勾画在其眼前!
李曜自己对这个计划也比较满意,他昨天去观察地形,的确很是为这府谷的地理优势大声叫好。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之诗摹状的是古凉州,而其所状孤城地处要塞、境界孤危之况景,又恰似府谷。
府谷城筑于黄河西岸三百丈之上的一座石山之巅,依山临河,巍峨险峻;远望城廓,宛若一只下山猛虎突然昂头,又似拔地而起的孤岛。其东临黄河,南为悬崖,西为巉岩,北若虎颈。登临此城,极目远眺,滔滔黄河奔腾而来;隔河,河东百里之地尽收眼底。
当时他来到山城南门山根,举头仰望,危乎高哉!
那悬崖绝壁山腰的一排石窟,山寺凌空,架有栈道,岩石凸暴,给人以震撼之感。沿神路攀登而上,有一千佛洞,洞中石窟六眼,窟约深丈余,宽近两丈,高一丈,内供释迦、文殊、普贤等佛陀,第二窟内供大小佛陀千余尊,千佛洞因此得名;另有祖师殿一座,建于门洞右侧之逍遥楼上,内供东华帝君金身一尊,与石窟成掎角之势,互为呼应,可谓佛道一家。
那千佛洞建在悬崖绝壁上,乃是此地古今之人,用绳索从高处把石工放吊在半空,像当年林县开辟红旗渠一样,于峭壁悬崖上用铁锤钢钻凿以成窟。
置身千佛洞栈道上,凭栏望去,脚下万丈悬崖,滔滔黄河,川逝而去,山危水阔,穷尽险奇;是时,李曜心中一首清人徐恒赞《千佛洞》之诗涌上心头:“峭壁城南寺,重重石洞穿。下临河浪阔,平眺晋云连。远树当窗近,轻舟过槛偏。心空来坐久,且话静中缘。”那一时,他的心境仿佛出现一片空灵,一种神秘崇高的敬意,自然而然产生出来。千佛洞左下石壁为摩崖石刻,古志中记石壁上刻有“禹王初导”四字。
南城门悬空而下者,乃是水门。李曜当时一问之下方知,此城依山不井汲,乃汲于河。
水门乃古代士兵和居民打取生活用水的唯一通道。水门建造奇特,巨石砌筑,高数丈,门洞两侧为峭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水乃人畜赖以生存的命脉,水门建若雄关,正是为了保护汲路,防敌进攻时切断水路之故。
拾阶而上,但见水门之外、洞门之上建有亭阁,虽不算精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