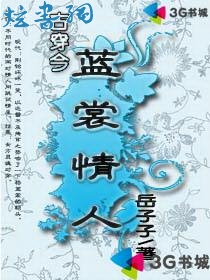明月照古今-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不管是京城的也好,外地来的客商也好,无数男子只为见我一面,一掷千金。我虽身处污秽之地,却也有自己的清高,我只见那些有才华的人,即使他们出不起钱,而那些商贾,愿意出钱让我从良,我却不予理会。也许公子要问,既然我自诩高洁,为何不愿从良,是么?”
周文宾正听得入神,忽听她发问,沉吟片刻,道:“文宾不敢妄言,想必姑娘定有自己的一番思量。”
若晴抿嘴一笑,又继续道:“公子说得不错。我不是不肯从良,我甘付一生,只愿等来我心中的那个人。公子大概不敢相信,我如今始终不曾梳拢,正是在等待我心里的这个人。”
她自倒了酒喝了,脸色愈发红晕,眼波流动,更增千分娇媚万种风情,“三年前,我迎来一位客人,他很有才华,他的诗,让我心生钦慕,但我只愿与他结为异性知己,却怎么也不肯答应他为我赎身娶我为妻,因为他还不是我想等的那个人。与他认识后的第三日,他邀我参加一个聚会——那是一个文人在一起谈诗论文的宴会,去的不止是我,还有别的姑娘,或跳舞、或弹琴、以助酒兴。就在那晚,我终于见到了我梦中的人儿,可是整晚他一眼也没有看我。他才高八斗、温润如玉、妙语连珠,加之身份高贵,使在场诸人众星捧月一般,这也许是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原因罢。之后,我再不曾见过他,虽说我知晓他的姓名他的身份,但我与他之间,却隔着屏障万重,他让我第一次生出卑微之感来,甚至我偶在练字时写他的名字也彷佛是亵渎了他”
周文宾微微皱眉,道:“姑娘太过妄自菲薄了,既然姑娘肯为他守身如玉,何不央中间人去说上一说,未必他便会拒姑娘于千里之外。”
若晴又是一笑,点了点头,道:“公子说的何尝不是若晴心中所想?那时我虽觉得论身份与他实在是有若云泥之别,但究竟心中爱慕难解,也不禁生出自不量力的想法来,于是我左思右想,写了一封信给我那异性知己,委婉地表明了我这番心思,只因他与那位公子正是至交。谁知信去后,却如石沉大海,这些年,别说那位公子,便是我这位异性知己,我也不曾见上一面,既遭蔑视,我岂能再自取其辱?我只盼着好歹见他一面,亲自问个明白,他朝寻个姑子庵,了此残生也就罢了。”
周文宾宽慰道:“想是信在途中丢了,你那位异性知己不曾收到姑娘的信。”
若晴轻轻叹了一声,道:“当时这冤家曾作了一首诗,这三年来,我日夜吟读,竟不曾忘却。凤鸣期不来,瑶华几消歇。唯有山中人,吹箫弄明月。”
这时的周文宾,脑袋中嗡嗡作响,如闻平地一声惊雷。这首诗,正是他所作!他顿时想了起来,三年前,他来京城看望父亲,受京城的文人邀约饮酒谈诗,那个夜晚的情形,于他来说,不过是无数文人聚会中的一场,因每次大同小异,他早就抛诸脑后了。
当时请了一些歌姬舞姬,但他心思全然不在那些女子身上,只因请的都是京城一些较为知名的文人,当中还有父亲同僚的儿子,只因是第一次见面,不敢轻慢,何况文人相见,也多少都会有些暗中较劲的意思,谁都不肯落于人后,因此他只专注于吟诗作对,丝毫没有留意场上那些女子是美是丑。
回忆起来,半晌,他又是难堪又是感概地说道:“姑娘口中所说的,莫非便是区区在下?”
若晴看了一眼外头暗下来的天色,起身点亮了灯,抬过来放在桌上,微微点了点头,“公子,今夜肯为若晴留下么?”
也许是酒意微醺,也许是面前这佳人的痴情让他感动,也许是这小而泛着温暖橘色光的房间温馨得让他心醉,他竟不忍拒绝,迟疑片刻,道:“若晴姑娘,小生已有未婚妻”
若晴抬起手来轻轻放在他嘴唇上,不让他再说下去,温柔地笑道:“我从未指望公子为我脱籍娶我为妻,但求一夕,想必这也是我们这种身份的女子唯一所盼的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周文宾不好再说什么。
若晴自去闩了门,坐在梳妆台前,拿起梳子来一下一下地梳着秀发,仔细看时,她的手竟在微微发抖,周文宾不禁心生怜惜,缓缓走过去,伸手握住了她拿梳子的手,只觉她玉手冰凉,手心里全是冷汗。
这一瞬间,他几乎产生了带她回家的念头,但很快就打消了——他答应过杜燕婷只娶一房妻子,这是他对杜燕婷的承诺,他唯一能报答若晴痴情的,也只能这样。
若晴站起身来,凝视着他,“若晴在公子的眼中,美么?”
周文宾道:“温情腻质可怜生,浥浥轻韶入粉匀,新暖透肌红沁玉,晚风吹酒淡生春。姑娘之貌,令小生惊为天人。”他伸出手来轻抚着她的脸颊,一双黑亮的眸子中满是温情。
说起周文宾的性格,既不比唐寅、祝枝山的风流跌宕,却也不似文徵明般“泥古不化”,颇有些中庸的味道。因家教关系,因此他不爱流连欢场,却从来也不反感厌恶。此时对若晴的态度,多少出于心软,却也表现出他原来也是可以做个风流才子的。
若晴嘤咛一声,扑入了他怀中。
天蒙蒙亮的时候,周文宾还在熟睡。这一夜不曾合眼的若晴秀发披枕,眉目含羞,轻轻地伸出纤纤玉手来,抚着意中人那眉峰眼睛嘴唇。
也许等他走了以后,今生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怎能睡得着?朦胧的香帐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他俊美的面容,她只想深深地印在心里,以此来温暖残生。
她的手抚摸到他的嘴唇时,被他抬手握住了。她羞涩地将脸埋在他怀中,轻轻道:“你醒了!”
周文宾揽着她□的香肩,肤凉如玉,他往上拉了拉被子,替她盖住身体。他酒意已去,这一夜恍如梦境一般,令他感到有片刻的迷茫。
他不是个绝情的人,思忖再三,他还是说了出来:“随我回家罢!我出不起梳拢之钱,却可让你脱籍,无论多少,任那老鸨开价便了。”
若晴低声啜泣起来。
她是因为喜悦而流泪的,他的话告诉她:“这一夕之欢,我不是将你当作青楼女子来看的,因此别提什么梳拢,我只将你当作我的人,一定要带你回家。”有他这番话,她这三年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
半晌,她柔声道:“你如何向令尊大人及未婚妻交待?”
周文宾沉默了,他当然可以对杜燕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杜燕婷允许他纳若晴,但这一来他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人了么?他之所以想赎出若晴,并不是向往三妻四妾的生活,而是这个痴情的姑娘将清白之身交给了他,他怎能放任不管,仍将她留在这样的地方?
“若晴,我得回去了,家父若知我彻夜未归,定要勃然大怒。”他坐起身来,“你别担心,我会设法解决的。”
整理好衣冠,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随口问道:“你昨夜说的你那位异性知己,他是我的好友,但不知姓甚名谁?”
若晴一愣,心沉了下去,颤声道:“公子当真要知道么?”
周文宾很诧异若晴的反应,但还是点了点头,若晴冷冷道:“便是徐祯卿徐公子。”她看着周文宾脸色微微一变,心也随之往下一沉。待周文宾走后,不禁趴在枕头上失声痛哭起来。
她觉得他再也不会来了。
周文宾下了楼去,找到老鸨开门见山道:“为若晴姑娘脱籍需要多少?”
老鸨先是一愣,道:“公子当真要赎若晴?”
周文宾道:“正是。妈妈这话问得好不奇怪,我既然开口相问,自然当真,莫非还说笑不成?”
老鸨叹了一口气,道:“周公子啊,这些年来我这做妈妈的,多少也知晓若晴的心事,虽说她从不曾向人提及,她心心念念等的正是你啊!我不是眼里只有钱的人,我也是肯成人之美的,我只盼公子是真心赎她,否则便让她仍留在这里也罢。”
这番话倒让周文宾十分意外,他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赎了她去便会给她个好结果,断然不能委屈了她。”
老鸨道:“既然如此,公子只须禀明家人,遣人来抬便是,还提什么钱?这些年若晴也为我赚得不少了,我岂能贪心不足?”
周文宾心中憾动,深深一揖,转身去了。
老鸨上了楼去,欢欢喜喜地说道:“周公子很快便来带你回去了,你好好梳洗一番随他去了罢。”
若晴却毫无表情,点了点头,道:“请妈妈让人为我准备沐浴,我这就梳洗打扮,我一定以最美的容颜走这一遭。”
周文宾回到府中,匆匆忙忙地换了朝服,来到顾湘月的房间一看,顾湘月竟然不曾回来。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但此时也不及寻找了,只得吩咐家丁出去寻找,自己赶去上朝。
在宫中见到脸色阴沉的父亲,见面就问:“这一晚,你与湘儿去了何处?”周文宾唯唯诺诺不敢搭腔。
正德皇帝时常不上朝,偷偷带着人跑出宫去玩耍,大臣们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早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早早地散了朝出来,周文宾故意磨磨蹭蹭拖在后头不敢跟父亲同行,怕父亲又追问不休,看父亲跟着同僚走远了,才缓缓往外走。
走到东华门那,一眼就看到迎面而来的朱秀玉与仍扮作小厮的顾湘月,上前道:“这一夜你去了哪里?一个姑娘家夜不归宿成何体统?”
顾湘月被他劈头盖脸这么一责备,吓了一跳,道:“我跟公主在宫里睡了一晚,有什么要紧?准你夜不归宿就不准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周文宾道:“男女有别,知道么!女孩儿就该乖乖在家读书写字学习女红,与公主在一起自然没什么,但一宿不回家,于妇德不合。”
朱秀玉在旁道:“你昨夜去了哪里?”
顾湘月嘻嘻笑道:“他要留宿青楼见人家花魁,将我赶走了。”
“周文宾,你——”朱秀玉火冒三丈,拂袖便走。
周文宾叹道:“你告诉公主做什么?”
顾湘月四周看看,轻声道:“哥,虽然公主是我好朋友,但我并不想让你做驸马,做驸马可辛苦了,要见妻子一面还得请示别人。哪有娶燕婷姐姐那么自在?所以我故意说给她听的,一个经常去青楼的男子哪有资格做驸马?这不正如你所愿么?”
“好罢!”周文宾道:“你究竟怎生跑来宫里?我是不是曾对你说过让你别与公主走得太近?我这做哥哥的说话你半句也听不进去是也不是?”
顾湘月道:“你先老实回答我,是不是留宿在花魁房中了?”
周文宾道:”是又怎样?这不正如你所愿么?”
顾湘月瞠目结舌,道:“你你不还是从未与女子什么的?你怎么这么随便?”
周文宾本就心情不好,道:“是你让我留在绣月楼,如今倒来说我随便,何况世上本无男子贞洁一说,真不知此话从何说起!我不管你留宿公主房中也好,哪里也好,总之你这一夜夜不归宿,便是违了家法,待回去禀过父亲后有你好看。”
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顾湘月,顾湘月呆了半天,又急又气,发火哭道:“我跟你就是驴唇不对马嘴,鸡同鸭讲。好啊,你告诉爹爹,打死我算了,反正我也不是这里的人,我跟你完全不同的观念,什么三从四德,你原来还跟我说你瞧不起那些假道学,如今又来说我,你才是假道学伪君子!”
周文宾道:“别的女子如何与我有甚相干?你既成了我周家的女儿,我就要管你。你休要以为我不舍得对你动用家法,再有下次,你且试试。”
顾湘月哭着推他一把,朝前走去。
兄妹俩虽一路回家,各自赌气不语。
周文宾自去找父亲禀明,只说傍晚的时候路遇公主,公主要拉顾湘月回宫秉烛夜谈,听说是公主拉去的,周上达也就没说什么。
周文宾备轿前往绣月楼接若晴,进去只见一群人哭得个个眼睛红肿,老鸨在当中抹泪不止,见了他迎上前来泣道:“姑娘死了!我不知她生了什么想法,当时公子走后,我上楼让她好好梳妆打扮等着公子,她答应得好好的,沐浴过后,关闭了房门,我只道她在房中换装梳洗,谁知过了一会进去她已吞金自尽了。”
这个消息惊得周文宾两眼一片昏黑,几欲站不稳跌倒在地,他跌跌撞撞地上了楼去,推开房门。但见若晴静静地平躺在床上,身着红色绣花袄裙,妆容一丝不苟,就如一个待嫁的新娘一般喜庆。一双手放在腹部,脸色白得如同新纸。
他坐在床沿,拉起她一只冰凉的手来,不忍目睹她那让一切黯然失色的美丽容颜,沉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无声落了下来。
他记得他说出接她回家的时候,她还很高兴,不知自己哪句话触动了她,令她生了寻死的心。
莫非是自己问她那异性知己是谁么?
是了,定是如此!
徐祯卿喜欢若晴,若晴却喜欢他,徐祯卿是他的至交,如今他要将若晴赎回去,将来他如何面对徐祯卿?她的死,完全是为了成全他,只是为了让他与徐祯卿之间没有芥蒂,让他能够从容地面对好友,她选择了死。
也许对她来说,她可以拒绝赎身,找个地方孤独地了此一生,但她深爱周文宾三年,与他一夕欢娱之后又再分离,大概也不是可以承受下去的,若是厚着脸皮跟他回家,便会给他造成许多困扰,权衡再三之后,她才走了绝路。
她走得很决绝,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谁也不知周文宾走后至她死之间这短短的时间,她内心是经过怎样一番思想翻天覆地的挣扎。
周文宾俯身将若晴抱在怀中,泪如雨下。
他深悔自己多余问那一句,她还不了解徐祯卿,她肯成人之美,徐祯卿又何尝不是?只一句话,成了催命的令牌,勾魂的绳索。
他仔细地想了想三年前,终于想起来,自那次文人聚会的第二日,徐祯卿就接到家书,说母亲病重,徐祯卿赶回家中,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徐祯卿为母亲的过世悲痛欲绝,也许早已将萍水相逢的若晴忘却了吧?
他应该告诉若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