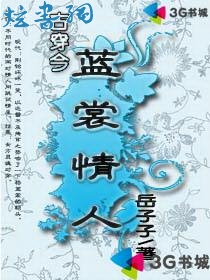明月照古今-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确实有些冷,”文徵明说道,“我叫醒文庆来为姑娘生个火盆,再加床被褥可好?至于泡茶添衣之事,不敢劳烦姑娘。”
“不必叫醒那小刁奴了,这时辰想必睡得熟了,不吵他。”顾湘月说道,“我是不是不能进你房间?对不起文公子,我是不是又不合规矩了?”
文徵明想了想,道:“我的房间就在隔壁园子里门前左右各一丛矮竹便是,衣裳在房中柜子里,有劳姑娘了。”
顾湘月高兴地答应着要走,文徵明轻喊了她一声,道:“天黑路滑,姑娘仔细看路,莫要再摔着。”
顾湘月心中温暖,点了点头。她摸索着来到文徵明的房间,摸到桌前点亮了灯,还观察了一番。他的房间很朴质,无非就是一床一桌一椅一柜,床上的被褥十分陈旧,桌椅的漆都掉了不少。她打开衣柜,翻出夹棉衣裳来,又吹熄了灯,抱着依然回到书房交给文徵明,道:“文公子,你真不像知府公子,文伯伯也不像个知府。”
文徵明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顾湘月又道:“公子素日里也是用火盆吗?这可不健康,因为碳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导致吸入的人上呼吸道感染,昏迷甚至在睡眠中死亡,不能用。最好是用的时候敞开门窗,在火上将被褥烤热铺上即可。”
文徵明怔怔听着,似懂非懂,微微点头,“姑娘言之有理。”
顾湘月笑道:“我可以在这里看你作画么?我帮你剪烛、倒水、洗笔,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缺什么我就帮你拿,我保证不再弄坏东西了。”
“使不得使不得。”文徵明忙道:“姑娘是逸卿府上人,小生怎敢劳烦姑娘?况且夜色已深,你我孤男寡女,须避些瓜田李下之嫌,下午你我书房独处,已然让老祝抓住不放”
“我偏不!”顾湘月咯咯笑起来,“你真是个小书呆!他说他的,管他做什么?在座都不是外人,你还怕他们传出去说我跟你什么什么的?你告诉我下午祝大伯说的相思债是什么?相思我懂,债我也懂,但凑在一起不是很奇怪么?”
文徵明愕然红了脸,呐呐道:“姑娘,非礼勿言啊,姑娘何苦来问”
他越是不肯说,顾湘月越发好奇,不停追问,笑道:“祝大伯拿我俩取笑,我只问你,不问别人。”
文徵明暗自叫苦,心想若是不告诉她,只怕她怎么也不甘心,只好万般窘态地解释道:“老祝口中以及俚曲中的相思债,一向是指指”
顾湘月奇道:“指什么?有那么难开口么?”
文徵明没奈何低着头道:“一般是指男女私定终身,女子珠胎暗结,那腹中孩子便是男子留下的相思债。”
顾湘月登时脸似火烧一般,忙道:“我我不知道才问的,祝大伯好不可恶”她一想起祝枝山晚上拿这个来取笑她和文徵明,偏偏她还回答一句“是她欠文徵明的”,好生难堪。
她满心烦恼,若是放在她那个年代,照她大大咧咧的个性,她会直接问他:“我喜欢你,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但这是讲礼仪守节操的古代,她只能看着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若不表白,他怎么能明白她的心意?
或许她是没法嫁给他,但她就想让他知道她对他的爱慕,起码她不想在走的时候留下遗憾。
她想了想,道:“你看过聊斋志异没有?”话方出口,自己不觉好笑: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写的,她却拿来问明朝的人。
文徵明道:“惭愧,我孤陋寡闻,竟不曾听说过。”
“没听过就对了,是我糊涂。”顾湘月笑道,“这是我们那边的人写出来的,隐晦地嘲讽了当下一些事情,本来是想拿出来让人传看的,又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里头很多不错的小故事,就有像你这样的书生在赴京赶考的时候,因救了一只千年狐狸,那狐狸化作一个女子前来陪他读书写字,你看现在我们可像里头的男女?你相信么?我也是五百年的狐仙,你帮了我,这也是缘分使然。”
文徵明红着脸默不作声,他自幼家教严谨,并且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似好友唐寅、祝枝山等人的风流不羁,从来谨谢不敏,似这般单独与一个姑娘深夜相对,更是头一遭。偏偏这姑娘言行不忌,是他从来也不曾碰到过的,他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但他毕竟年轻,心中不免又有些好奇,忍不住问道:“书中那书生与狐仙姑娘后来如何?”
顾湘月笑道:“当然是大团圆结局啦!书生高中状元,辞官不做,回家与狐仙长相厮守。”
文徵明诧道:“一为人一为仙,异道殊途,如何长相厮守?”
他这句问话其实也隐隐包含了心中的踌躇,试问家教严谨书香门第的他怎么能与出身平凡不拘小节的她在一起?即使他愿意,但世俗礼教父母又怎会允许?
顾湘月叹了一声,道:“文公子,你一定是读的杂书太少了,很多的爱情故事,都是不合礼教的,但却能够感人肺腑,因为男女主人公都是真心地爱着对方,哪怕为对方死了也是愿意的,这样的感情可以感天动地,在这样的爱情面前,礼教就微不足道了。真正喜欢对方,难道没有勇气冲破旧俗么?等以后有空,我再给你说说梁祝的故事。”
她见文徵明低下头来不再说话,便小心翼翼地帮他泡了杯茶放在一旁,自去厨房生了个火盆抬过来,拿来他的被褥,小心地在火上烘烤。
火光中,两人的脸都红扑扑的,文徵明阻止不了她,只得温和一笑,继续未完成的永锡难老图。
他画了几笔,又忍不住道:“方才姑娘说的梁祝,可以说给我听么?”顾湘月一愣道:“不影响你作画?”
文徵明微笑摇了摇头,顾湘月笑道:“那你画,我说给你听。”
她想了想,说道:“从前有个叫祝英台的千金小姐,她喜欢读书,因此求父亲让她女扮男装到万松书院和那些学子们一起读书,她父亲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她带着自己的贴身丫鬟银心去到书院,认识了同去读书的穷书生梁山伯,那梁山伯心地善良本分老实,倒是有些像你。两人同窗三年,并且结拜了兄弟,梁山伯始终不知与他朝夕相处的祝英台是个女子。那书院中还有一个纨绔子弟叫做马文才,是太守之子,他却看出了祝英台是个女子,他喜欢祝英台,祝英台却很讨厌他,于是他先行回家向祝员外提亲,祝员外觉得这门亲事很不错,就在家书中谎称自己生病要女儿回家。祝英台接到家书后,不得已只得回家,临走前,她向一直疼爱她的师母表明了身份,并留下玉扇坠请师母为她向梁山伯说明她的情意。”
她盯着低头作画的文徵明,道:“我说的很乏味吧?”
文徵明抬起头来,轻轻道:“姑娘说得很好,请继续。”
顾湘月笑道:“流水账似的,还说好呢。祝英台告别书院回家的时候,梁山伯一路送她下山,十分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那时他还不知情,只是舍不得这个同窗三年的小兄弟。这里有个名堂叫做十八相送,梁山伯将祝英台送到一个长亭时,在那歇脚时,祝英台便说她家有个小九妹,还未婚配,想说给梁山伯,其实那个小九妹就是她自己,她约了七巧之期让梁山伯上门提亲。梁山伯回到书院后,听师母说出实情,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很心疼很怜惜的弟弟是个女子,他真是喜出望外,一刻也等不及,早早地就下山去了。”
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谁知祝英台回到家中,父亲才告诉她已将她许配给了马文才家,就如晴天霹雳一般,她是吃不下睡不好,一天天消瘦下来。待到梁山伯上门提亲之日,她告诉了梁山伯,两人泪眼望泪眼,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祝员外怎么也不松口,两人相爱,却注定无法结为夫妻了。回到家中,梁山伯就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再也没有起来。祝英台得知梁山伯的噩耗,在出嫁给马文才那天,要求父亲以及马文才答应她,内穿素服,外穿喜服,先去祭拜梁山伯的坟墓再入马家的门。祝员外和马文才没奈何答应了。就在祭拜时,天上忽然暗云翻涌,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一个大口子,祝英台毫不犹豫跳了下去,那墓复又合了起来。等云散天晴,忽然从墓中飞出一雌一雄两只美丽的蝴蝶来,翩翩相伴,形影不离,看到的人都说那一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她吁了一口气,笑道:“我发现我说故事跟白开水似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公子一定听得乏了。”
文徵明沉默半晌,摇头道:“这个故事已然让人五味杂陈,更无须姑娘再加料了。”他微微叹了一声,什么也不说又低下头作画。
顾湘月却嘴闲不住,道:“你看,其实马文才直接向祝员外下聘提亲,这才符合传统的礼教,所以祝员外说师母做媒,女儿与梁山伯私自交换玉扇坠都不作数,但这个故事每个人听来都会替梁祝惋惜,可见有时候真理在大多数人心中,包括那些不识字的老百姓,文公子,你惋惜不惋惜呢?”
文徵明温和地看着她,道:“姑娘一番话正如金玉之言。这个故事催人泪下,徴明听来,岂有不惋惜之理?”
无论顾湘月怎么旁敲侧击,他就是跟木头人一般,似乎完全听不出来言外之意,从头到尾只是就事论事。顾湘月只得作罢。
她觉得自己已经说出来了,至于结果是什么样根本不重要。
作者有话要说:
☆、彻夜相对(2)
画完之后,文徵明将画拿到旁边晾着,重新铺上空白画纸,道:“湘月姑娘,你不是想学画么?来!”
他主动说话,顾湘月很是高兴,小心地将被子挂在椅背上,将火盆放在椅背后不远处烘烤,然后走到文徵明身边。
她的衣服轻轻挨着他的衣服,他浑然不觉,提起笔来边画边道:“姑娘你看,松、竹、柳、梧等画法各不相同,先将树干与旁枝勾勒出来,再加以枝叶。绘枝干须按各种树木不同,以展现弯曲延伸之态,倘若绘秋冬时节,忌枝叶繁茂,若是作贺寿图,则一定要呈现长青常绿的形态,如果绘远山近岭,须得近实远虚,近大远小,近深远浅,近处细中见细,远处则可用粗笔画法一笔带过。至于山水树石安排,讲求错落有致,换言之,你若绘两山,倘若同列且高低相等,则少了真实感,平日尽可能多看多留意”
顾湘月笑道:“我知道,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
“正是!”文徵明指着窗外,“绘湘竹落笔须果断,不可磕磕绊绊,以显竹子简练高直之姿,而松树的树干却苍劲奇特、神态各异,石头也有各种画法,皴法不同,用笔不同”
他认真地教,却没留心顾湘月是不是认真地在学,她时而专致,时而走神。她一时想:我个头到他耳朵,人家说这是夫妻最佳相距高度;一时又想:就这样一辈子在他身边挨着多好,可惜手机也丢了,否则让他帮我录个起床铃声,就能天天听到他的声音了。
这时见他将毛笔递了过来,道:“姑娘且绘几笔看看。”
她吐吐舌头,接过笔来,随意画了个树干,“这样对么?”
文徵明将笔又拿过去,轻声道:”姑娘绘得大致不差,只是树干上下切莫粗细一致,如此与真实不符。你看,树干往往是根部最粗,往上微收”明明他方才已仔细说过树干的画法,但顾湘月画得全然不对,可见顾湘月并没认真听进去,但他并不生气,又耐心地教起来。
顾湘月兴致盎然,抢过笔来专心地画了起来,他在一旁看着,时不时出言纠正。遇到她听不明白时,他索性又重新取一支笔来,自己在旁边画给她看,让她照着画。
两人正画得专注,顾湘月无意一抬眼,看到被子一角已经滑了下去,落在火盆中燃烧起来,她惊慌失措地说道:“失火啦!”
那被子里头都是棉花,一点即着,火势愈发猛,顾湘月抬着笔洗过去将水全部倒上去,也只是杯水车薪,文徵明忙道:“我去叫人来!”
“别去!”顾湘月一把拖住他袖子,道:“你还嫌祝大伯笑我们笑得不够厉害?传了出去又有话说。”
文徵明道:“这可如何是好?”
顾湘月跑到院中拿了长扫帚来,将燃烧的被子挑到外面扔在空地上,回头见那椅子的椅背也烧了起来,忙提着两只椅子脚将椅子也扔了出去,“好烫!好烫!”她甩着两只手。
那被子和椅子因在苑中空地燃烧,周围没有着火点,慢慢地也就熄灭下来。
“姑娘没受伤吧?”文徵明走近前来,仔细地端详着顾湘月,见她耳畔头发烧了一缕,又卷又焦,脸上也熏得发黑,拿起她手来看,左手食指上起了两个大泡,顾湘月看着手上晶莹的水泡,反觉有趣,笑道:“公子你看,这两水泡一大一小,像不像母子?”
文徵明走了出去,少时拿了针线盒与药箱来,取下灯罩来,将针头在火上烤了烤,道:“姑娘请伸手来!”
顾湘月将手缩在袖子里,“要戳破吗?这多有趣,干嘛戳破?”她从小到大身上不曾起过任何水泡,感到新奇,还想留着多看几天。
文徵明温言道:“湘月姑娘,这水泡有甚好玩?还是医治要紧!来,伸过手来。”
顾湘月只得伸手过去,他握住她手拉到灯前,小心地刺破了水泡,挤出水来,上了药。又取了剪刀来,为她剪去烧焦的头发。再去打了水来,拧了帕子来要替她擦脸。
“干嘛?”顾湘月道,“你要帮我洗脸,赶我去睡觉?”
文徵明指着脸盆笑道:“姑娘一照便知。”
顾湘月往盆中一照,见自己一张脸如花猫似的,不由一笑,道:“我自己洗吧。”
文徵明道:“姑娘的手刚上药,不宜碰水,还是由我代劳吧。”
顾湘月叹了一口气道:“文公子,我在你面前真是你看我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画废了、被子烧了、椅子烧了啊哟,那椅子不会是什么昂贵的木头或者是祖传的吧?我可赔不起啊!”
文徵明替她擦着脸,边笑道:“不过是普通椅子罢了,只是姑娘莫在文庆面前说漏了嘴,以免他又絮絮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