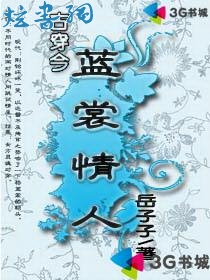明月照古今-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朝可好?”
顾湘月听他说“我与姑娘”,没来由又是一阵脸热,笑道:“那我在这里看着你画行么?”
“姑娘请自便!”文徵明微笑道。
顾湘月噗嗤一笑,暗想他这人也实在有趣,明明她在这里他感觉拘谨得很,但他就是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可见他是多么面皮薄。
她就这样坐着看他画,时而看看他,时而看看画,浑然不知身外之事。忽然腹中咕噜噜响,又是饿了,原来这已是接近傍晚了,中午她装斯文,只稍稍吃了几口,这时却饿得慌,不禁大感难堪,书房中安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到,她肚子造反的声音也太响了。
文徵明放下笔来,道:“姑娘可是腹中饥饿?对不住之至,我只顾自己作画,全然忘了姑娘是贵客,理应奉上糕果茶水供姑娘用才是,姑娘且稍等片刻。”
他走了出去,这番话令顾湘月很是泄气,在她心中,他是意中人,而在他心中,她就只是个客人而已。
他离开后,她转过书案前去看他的画,整体已经绘好了,只差上色。能亲眼看到一个知名的书画家将一幅传世作品一笔笔画出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对于现在的顾湘月来说,这样一幅画价值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
曾经,她对他的字一见钟情,如今同样心仪他的画,她轻轻地用手抚摸着那些线条,就像对着他的人。
“喂——你干什么?”文庆突然出现在门口,大声说道。
顾湘月吓了一跳,忙抽回手来,不想袖子带到了色盘,又拉翻了笔洗,顿时水浸湿了整张画,混着袖子沾染的各种颜色,淋淋漓漓,惨不忍睹。她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文庆叫道:“哎呀,完了!”
文徵明走了进来,手上端着糕点,见书案上一片狼藉,略微一怔,道:“文庆,你去让英嫂备饭,子畏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公子!”文庆急得青筋暴起,“你看你的画被她”
“既已污了,重画也就是了,若非你大呼小叫,岂能惊了人家姑娘?你怎能只知一味责怪别人而不知自省吾身?”文徵明神色如常,文庆无法说下去,只好狠狠瞪了一眼呆若木鸡的顾湘月,转身去了。
“湘月姑娘,”文徵明微笑道,“这些糕点你先将就用了,少时子畏他们回来便可以用饭,我去取套衣裳来给姑娘换下。”他放下糕点来转身要走。
“文公子,对不起!”顾湘月低着头,眼泪夺眶而出,她是亲眼看着整个下午文徵明是如何才将这幅画绘出来的,一笔一画都是他的心血,“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小心弄翻了笔洗我总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文徵明一笑道:“无妨,今夜再绘也就是了。姑娘不必自责,这只是小事一桩,别哭了。”
他语气温和,顾湘月眼泪却愈发汹涌,他态度越好她越是自责。
文徵明有些手足无措,半晌道:“一次子畏作画,老祝恶作剧地甩了几滴墨上去,当时子畏很是气恼,几日后当他重绘时,竟然比第一次更加精妙,他心中感激老祝,便做东请老祝喝酒。我想起方才有处地方画错了,正有意重绘,姑娘反成全了我,待姑娘返杭郡时我谢姑娘一对耳坠如何?”
“少来!”顾湘月还是满脸泪水,却也忍不住笑了,“你明明是安慰我。你不要我赔画就是好的了,我哪敢要你的耳坠?究竟你说哪里画错了?否则我哭上两天两夜。”
文徵明想了想,笑道:“画已不存,姑娘让我指出错处,我如何指得出来?只依稀记得一株松树的位置是不该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由他去!姑娘用些糕点,休要饿坏了。”
他又走出去,过了一会儿拿了一套浅藕色的袄裙,道:“姑娘先将就穿罢,这是清雨的衣裳,她还不曾穿过。”
顾湘月接过衣裳回房换过,这清雨身材与她大概也差不多,穿上甚是合身。
她依旧回到书房,捋着袖子要收拾书案,文徵明忙伸手拦道:“姑娘是客,若做这些事,实是折煞我了。”无意碰到她的手,急忙往回缩,他红着脸道:“小生并非并非有意冒犯姑娘”
顾湘月低头看着自己的裙子,忽然道:“清雨是你的”
文徵明道:“清雨是服侍家母的丫鬟”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忍了忍终究没说。
顾湘月吁了一口气,如若清雨是他妻子,那她宁愿依旧穿着那污了的衣裙。
这时,周文宾三人从外头进来,祝枝山摇着折扇道:“日头竟这般毒,今日就不该太湖泛舟,躲在小文府中乘凉不好?”
唐寅笑道:“方才进门时见文庆跳着脚埋怨湘月姑娘,怎地了这是?”
他朝书案上一看,笑道:“罢了,谁没有错手之时?衡山你何必将人家姑娘骂哭了?至多我们明日去向杜老说你吃坏了东西,腹泻了一夜起不来床就是了,你还省了一幅丹青,我真是羡慕得垂涎三尺!事实上我也不舍得送,无奈找不到托辞罢了。”
“我”文徵明呐呐无语。
顾湘月忙道:“他没有骂我,是我自己内疚。”
“这就是了,”唐寅笑道,“你不知衡山,若是我三人污了,他定要大动干戈兴师问罪,至于佳人所为,那便丝毫无妨,他无非不去寿宴就是,横竖宁负天下人莫负佳人。”
文徵明笑道:“我何曾有之?”
祝枝山道:“小唐,这哪是小文?明明是你夫子自道也!”众人又相视发笑。
经他们一说笑,顾湘月心中的负疚感也减轻了些,跟着笑了。
文徵明看向她,目光温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顾湘月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高兴她不再自责。
只这半日功夫,她已足以了解他的为人——他动辄害羞,绝非风流之人;他不责她污画之过,足见心胸宽广;他这淡淡一笑,更显他心地善良。若说曾经喜欢他的俊秀斯文,那么如今他的人品已让她心如磐石了。
闲聊了一阵,饭已做好摆在苑中。此时华灯初上,天气正凉爽,顾湘月抓了两块文徵明拿来的糕点跟着他们去苑中落座,既然饭已做好,这糕点当然是可吃可不吃,然而这可是文徵明亲手端给她的,岂能不尝?
众人刚落座,苑门外一人笑道:“你们喝酒怎不叫上我?岂不闻昌谷向隅,举座不欢!”
清朗悦耳的声音传了进来,人也随之进了苑。
这是个与唐寅三人年纪相仿的书生,但他长着一张瘦长脸,细眼淡眉、大鼻阔口,相貌十分丑陋,若是不看他的脸,倒也颀身玉立倜傥风流。
众人起身迎他,唐寅笑道:“昌谷,你如今也学着老祝,不到开饭不来。”
祝枝山笑道:“哪里没叫上你?若不曾叫你,你怎会出现在这里?”那书生笑道:“小弟是踏着酒香而来!”
文徵明道:“文庆不曾去府上邀请你么?”
“他是谁?”顾湘月悄悄站在周文宾身后问道,
周文宾还未说话,这书生已一笑作揖,道:“姑娘好,小生徐祯卿!”
顾湘月暗想:名字真好听!笑着裣衽一礼,“徐公子也好,小女子顾湘月。”
周文宾轻声笑道:“这也是我们知交。”
晚上的菜肴比起中午来丰盛了许多,一色樱桃火腿、一色松鼠鳜鱼、一色香菇豆腐、一色素炒虾仁,一个三鲜砂锅,五颜六色,香味扑鼻。
顾湘月望着直咽口水,但见众人都不动筷子她也不能动,只听文徵明道:“这些可还合姑娘胃口?”她忙点点头。
祝枝山笑道:“小文,你素日里装作一副道貌岸然坐怀不乱目不斜视真君子模样,谁知今日一见佳人登时将我等抛到一旁,你怎不问合不合我老祝胃口?湘月姑娘是娇弱肠胃,我等便是铁打的,是也不是?”
文徵明呐呐无语,周文宾笑道:“老祝休得挑拨,我与子畏、昌谷哪似你这般刁钻难以侍候?往常衡山问你,你只说将你当外人,不问你罢,你又怪不关心你,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徐祯卿笑道:“理他作甚?我是饿得慌了,特意空着肚子来蹭衡山这顿饭,抱歉我先用了。”
他先动了手,众人也便先后吃起来,祝枝山道:“小徐,你是饿死鬼投胎么?”
一听这话,夹着好大一筷松鼠鱼的顾湘月手一滞,一块鱼肉滑落在香菇豆腐里。
徐祯卿笑道:“你说我不打紧,却吓了人家湘月姑娘!实则哪是我腹中饥饿?我只是看湘月姑娘饿得慌了,却不便先动。你们没看到她一双妙目只是盯着桌上菜肴,想必心中说‘入我腹中来,我超度你等!’我们几人熟不拘礼也就罢了,怎能不顾及湘月姑娘?”
顾湘月感激地看着徐祯卿,他貌丑心善,比起内心的真善美来,面貌又算得什么?
唐寅笑道:“这鱼乃是瞧着豆腐可心,故来了一出云追月,衡山正如这豆腐,湘月姑娘正如这鱼,你们说是不是?”
两人被他点名,都一愣,相互看了一眼,随即低下头来。
说笑了一阵,唐寅提议联诗,众人说好,周文宾笑道:“我与湘月除外吧,你们多少也须顾念湘月新来乍到,还不习惯。”
祝枝山笑道,“湘月姑娘试试无妨,这又不难。”
“我才不参加呢!没的丢乖卖丑。我知道你们都是出口成章的才子,想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门都没有!”顾湘月抬着下巴,一副打死不干的态度,在座皆觉好笑。
众人都还半饱之时,她已然吃饱了,只看着那酒壶,这酒叫做屠苏,她还没喝过,不知道味道如何,寻思是不是倒上一杯来喝,又怕醉了在文徵明面前放肆,让他看笑话。
文徵明笑道:“何苦强人所难?我们来就是。逸卿既不参与,便出题罢。”
周文宾笑道:“花月。这是子畏最擅长的了。”
唐寅道:“花发千枝月满轮,”
祝枝山道:“一轮新月祭花魂。”
徐祯卿道:“花魂脉脉酬新月,”
文徵明道:“月移花影入金樽。”
周文宾笑道:“还是花月,五十六字。”
唐寅道:“花开烂熳月光华,月思花情共一家。”
徐祯卿道:“月为照花来院落,花因随月上窗纱。”
文徵明道:“十分皓色花输月,一径幽香月让花。”
祝枝山道:“花月世间成二美,傍月赏花酒须赊。”
顾湘月看他们联得好玩接得流畅,抢着道:“江楼。行不行?”
唐寅一笑,道:“雪落空江隐孤楼,”
祝枝山道:“倚楼闲看江自流。”
徐祯卿道:“楼静夜阑江浸月,”
文徵明道:“空楼人去晚江愁。”
祝枝山笑道:“小文,不知是谁去楼空?是你?还是一位佳人?听有人唱‘独倚阁,望空江,骂一声薄幸情郎,是他软语相求,我欲迎还羞,成就那段风流情殇,只教莺癫燕狂,戏水效鸳鸯,留下相思债,怎不令奴断肠?’”
他一壁唱一壁用箸敲击桌子,文徵明满脸通红,直道:“过了!过了!往日由你罢了,今日在座有湘月姑娘,切莫放开情怀说笑。况且我今日又不曾开罪于你,只拿我取笑作甚?”
祝枝山笑道:“你与湘月姑娘整个下午孤男寡女厮守书房,郎情妾意、如胶似漆。我只说两句又怎的?但不知可曾欲迎还羞莺癫燕狂成就一段风流佳话?”
又道:“小文啊小文,在座诸位除却湘月姑娘,谁不知你?你素日一派正人君子模样,但诗词中往往隐然透着春意,到底还是‘又想翻墙寻芳草,又怕被狗咬’,你说是也不是?”
众人哄然大笑。
顾湘月才知道祝枝山拿她跟文徵明开玩笑,顿觉不好意思起来。
唐寅笑道:“我若是衡山,便拿大扫帚将你赶了出去!偏巧我不是当局者,愿老祝多说几句,以供下酒。”
文徵明笑道:“子畏,莫不是还嫌今日这一席酒菜亏待了你?谁要老祝疯言疯语来佐酒,我且记下你。”
祝枝山笑道:“是吧?周老二。”
周文宾皱眉道:“你取笑衡山也就是了,干我甚事?”
祝枝山努嘴笑道:“你身旁不正坐着笔相思债么?只不知这相思债究竟是你欠下的,还是小文欠下的。”
顾湘月一直在琢磨他们所说的话,想看文徵明又害羞不敢看,心中纷乱如麻,只听了大概,心想:他哪里欠我了?我将他画好的画污了,是我欠他才对。抬头说道:“文公子没有欠我债啊,是我欠了他。”
唐寅、徐祯卿、祝枝山连同周文宾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见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唯有文徵明也是赧颜不语,顾湘月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道:“怎么了?干嘛笑我?”众人愈发笑得厉害。
作者有话要说: ①注释,沈周:字石田,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
☆、彻夜相对
这一晚喝得尽兴,聊得也尽兴。
唐寅、祝枝山、徐祯卿走了以后,周文宾与顾湘月也早早睡下了。
睡到半夜,顾湘月冷醒过来,原来半夜变了天,看地上潮湿,还下过雨。她隐见灯光由书房那边透出来,寻思定是文徵明为了赶画还不曾睡。
她走过去,从窗口看到文徵明在那专心致志地作画,不由一阵心疼——若不是她,他也不用熬夜绘画了。
她先摸去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提着水壶轻手轻脚地走近书房,轻声地喊了声:“文公子,”才探出身子去,她只怕三更半夜地吓到了他,他笔端一颤,画再次作废不说,她担着关系倒不要紧,他又得重新画。
“湘月姑娘,”文徵明有些意外,搁下笔来,“你还不曾睡下么?可是缺了什么?”
“变天了,你看。”顾湘月指着外头红红的天,“冷醒了,看到这里有灯光,心想你必定在赶画,就过来了。”
她够着身子看他的画已绘得七七八八了,不敢走近,生怕自己毛手毛脚地又把画破坏了。“我睡不着,就去烧了壶水,我来帮你泡茶吧,还有你穿得少了,我能去你房间帮你拿件衣服来么?”
“确实有些冷,”文徵明说道,“我叫醒文庆来为姑娘生个火盆,再加床被褥可好?至于泡茶添衣之事,不敢劳烦姑娘。”
“不必叫醒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