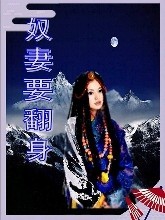三醉误终身-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墅里英式的大吊钟,“当当”的响着,声音撞到墙面上,又被硬邦邦的反弹——铺满红木的房间,显得空旷而冷。
刘朝儒双手交叉在脑后,头一寸一寸,慢慢的搁在臂膀上,他努力睁大眼睛,内双的眼皮,可以看见细细薄薄长长的一层。黑色深潭中,透明的液体慢慢的渗出来,积在眼眶,越积越重,却怎么掉也掉不出来。
12月24日,平安夜,隔壁邻居家呼啦啦的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几个带着火红色的圣诞帽,白色的绒球,重重的垂在下面,时上时下的振动,又有个女孩儿,苹果脸大眼睛,见他同样黄皮肤黑头发,敲了敲窗,哈了口气,歪歪扭扭的写上字:“一起玩儿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笑声闷在胸腔里,轰隆隆的响。压迫着肺部,快要透不过气。
她和昨天身下的女子,长得颇有些相似。丰满的胸,握在手里,满满的仿佛圆润的葡萄酒杯。
他像母亲所诅咒的那样,成了越来越不像话的浪荡子,流连于不同的身体,柔软的腻滑的,男人的女人的,激情过后是更大的空虚,他全心投入,冷然起身,望着黑色的窗,等着天明,等着堕入阿鼻地狱。
只是,今天不行——今天是他的禁欲日。
在这个泰半人都摇曳如花的日子,他唯一的亮光,一曳,被风扑灭,“哗”的一声火星子被扑得满地都是,烫在他的心上,要命的疼。
某个平安夜的傍晚,鹅毛般的雪卷着北京。风撞在破旧的窗棱上,啪啪的响。落了漆的天花板,悬着光秃秃的灯泡,光和影,交错重合——昏黄的灯光,一会儿照在他脸上,一会儿打在她身上,而他们却始终不能,同时浸在光明之中。
——仿若他们之间的一次次错过。她风华正茂的时候,他还不及学会爱;而当他终于长大,她却再也等不起——一些人和一些人,命中注定是要缠绵致死;而另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却始终只能,错过而已。
却始终只能,错过而已。
十四岁后的好多年,刘朝儒都没有再见过陈淑。
他不能,他也不想。
那天,他浑身冰凉的从李宅回来,尖刻的话语仿佛一根根尖且细的刺,根根扎进他的心,仿若童年时扎进指尖的细针,渗不出血,流不出泪,却疼,疼得让人想大叫,想发狂,却始终只能浑身发冷,发不出任何声音。
厌恶感恶心感,一阵阵的向他盖来,几欲淹死。
碎玻璃片碎制片夹杂着红的绿的,漫漫的铺着台阶,平时颇有教养的贵妇,披散着头发,瞪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瘫坐在地上。
暗红色的高跟鞋,一只吊在脚上,一只还勉强的穿着。
她叫道:“你去找那个狐狸精啊你去找啊!”
她嘿嘿一笑:“我早知道她是个骚货!来路不清,高中文凭?怪不得这种人都能当秘书……我平时打电话找你,你就工作工作的敷衍。研究文件?讨论问题?”她仰头呵呵笑了一声,随手抄起烟灰缸砸过去:“研究玉蒲团还是金瓶梅?讨论什么时候去偷情,用什么药,穿什么内衣,放什么片子……”
还没等她说完,背对着刘朝儒的男人,仿佛扬了扬手,尖叫和清脆的巴掌声,一起响起来。
“你闭嘴!”
男人往后一倒,整个身子都挂在了门框上,仿佛是倦极,连声音都无比的苍凉空洞,他说:“没错,我爱她。”
刘朝儒冷笑一声,扭头往回跑,连阳光打在身上,也是冷的。
仿佛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在黑暗里跑着,没有出口没有希望没有光,甚至,都不存在继续下去的意义。这样子,过了一年又一年。时光是怎么流逝的,窗外的梧桐,是怎样从绿转黄复转绿,李家的小霸王是怎样一节节竹子般拔高的,他一概不清楚。
直到重逢。
重逢的那天,天气一样是很好。刘朝儒眯着丹凤眼想了想,他和陈淑在一起的每天,天气无疑例外的是晴天,春天的晴天,夏天的晴天,秋天的晴天,冬天的晴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如同她呲开嘴的笑,一直明媚到眼角眉梢,相忘,不敢忘。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刚刚过膝,领口缀着毛线,大大的领子,像平菇的伞盖,服帖的盖在身上。头发随意的往后一拢,别了淡色的发卡,疏疏朗朗的,不知道怎么的,就让人心疼。
刘朝儒犹豫着要不要上去,却是她先开口。她踮起脚来冲他摆摆手,眼睛细细眯成一条线:“小……刘朝儒。”
不是小鬼,是刘朝儒。没有抑扬顿挫,没有亲昵和喜悦,反而有些心慌和尴尬,带着强自镇定,叫他:
“刘朝儒。”
刘朝儒抿了抿嘴角,犹豫着要不要上去。
陈淑站在原地,盯着脚尖,也在犹豫。
好快。
她在心里感叹,好快。
时间仿佛晃晃悠悠的公交车,明明那么慢,偏偏又早就过了,一辆又一辆。
他知道了吗?
她被赶出公司,她嫁人,她生了两个女儿,细细的眉眼,软香的身子,咯咯的笑起来,会往外噗奶泡。只是后来又离了婚,前夫带走了一个女儿,又……
小立小立……她轻声喃喃,接着心头一痛,脚都开始发软,怎么也站不住,直到有力量,犹豫着托住了她。
这时候,有风细细微微的吹过,陈淑还不及挽好的刘海,拂在刘朝儒的脸上,轻轻的一曳,却像被烧红了的铁丝,烙在他的脸上,温度烫的吓人。
陈淑闷闷的说了声谢谢,规矩的离开刘朝儒的臂膀,快走了几步,保持刚刚好的距离。
所以,她自然也看不见,背后的刘朝儒,绝望无奈而甜蜜的闭上了眼睛。
他想,就这样吧。谁让他爱她?他爱她,即使她已千帆过尽。
只是这场爱恋,却是这样的短。短的就像北京的秋天,刚刚有了些微的凉意,马上就刮起了呼呼的西北风,落下了雪,纯白色一片一片的堆叠,覆盖了落叶和果实,就这样到了冬天。
刘朝儒拉开灯,不例外的看见,陈淑又紧闭着双眼,恹恹的睡在那里。
他走过去,拉开柜子,熟练的挑出毛毯,轻轻的盖在她身上。
他怔怔的看着陈淑的睡颜,出神的想,为什么会爱她?
笑容温暖,心底开朗的女子,他遇见的不只一个。而偏偏就认定了她是他的独一无二,或许是他拥有的太多,而她有的太少,老天爷看不过去,就降下了这样的惩罚。
遇见她不久后,他就知道,她得了病,命不久矣;再之后,她伴在身边的另一个女儿,被李家自说自话的带走;再之后,她的前夫带着新的夫人新的孩子新的房子到她面前耀武扬威,而她只能跪在地上,用骨瘦如柴的手,盖着脸,自言自语的说:“我没有。”
最后的最后,她的身边,只剩下他。
他跑到后海,买豌豆黄给她。
粉嘟嘟的黄色,方方正正的糕体,轻轻一口,含在舌尖,绽开五彩缤纷的味道,一点点的融化,落在心里,好像是蘑菇放出的细小孢子,埋下细细小小的,可以称为希望的东西。
他每天给她沏好一壶明前龙井。
她生在江南,春天满山都荡漾茶香的地方,而偏偏,她不喜欢喝这甜美的绿汤。她总是蹙着眉头,嗤他:“跟煮叶子似的。”
他斜眼看她。他的眼睛很好看,是标准的丹凤眼,眼角斜斜的飞入两鬓,不语却含情。他不顾她的抱怨,把精巧的茶具,一字的排开,手腕一抖,澄澈的液体就落入碗底,仿若,大珠小珠落玉盘。
有一天她忽然赌气,一扬手,打翻了其中的一个:“你真的是个小鬼!绿茶只是预防预防而已!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不喝我不喝!”
刘朝儒淡淡的看她,依旧把新斟好的一杯,送到她唇边。
为了她,他什么都愿意试。北医三又来了国外的某某专家,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去,有几张黑信用卡,有张地契,还有几张存折,他把能想到的都带上,厚厚一叠奇Qīsūu。сom书,塞满了整个公文包,好像带了满满的希望;他从哪本不入流的杂志上,看到有人看了多少多少本笑话,就不治而愈,以前他会把这整件事当笑话,而现在,他会板着脸孔,一本正经的念:“有头公鹿越跑越快,成了高速公路。”;而同样,他听说某某人又说,绿茶可以抗癌,也不管真假,从家里搬来了一整套的茶具,每天每天的为她泡出氤氲的茶香。
到后来,他的爱情,仿佛已经成了信仰。
这怎么可能是爱情呢?从来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哑巴一样的爱情,终究,只能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信仰。
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北京的街头比平常热闹了一些。
他从城市的最中心,开车,倒出车库,将油门一下踩到底,去见她。
他路过长安街,路过纷繁热闹的商业区,上高架,下了,再上。
丽思卡尔顿酒店门口,立了株圣诞树。树顶放射出千万条银色的光链,在黑夜里灼灼的燃烧,酒店门前人迹寥寥,衣着得体的男士和女士,低头匆匆走着,或是紧紧的黏在一起,亲吻亲吻再亲吻,除了他,没有人注意到这真正的火树银花。
这样的夜,却连圣诞树也寂寞。
他觉得心头突突的跳,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不可遏止的从他生命中抽离,让他心慌得不能自抑。银色的车滑入夜幕,风驰电掣,他却闲慢。
副驾驶的座上,放着他要给她的礼物。
一张简单的贺卡,写着:“妈妈,圣诞快乐。”他很久没有去过李家,但这次,他想给她一个惊喜。她的女儿,穿着纯白色的毛衣,修长的腿包裹在合身的牛仔裤里,头发高高的竖起,甜甜的叫李家的男主人:“爸爸。”
他在心底嗤笑,认贼作父,也不过如此。却压着心头的不适,把小女孩儿叫到一边,和气的说:“今天是平安夜,写一张贺卡给你妈妈吧。”
他的声音那样轻,轻的就像是一片在空气中打圈的鹅毛,温柔却抓不到。
女孩一愣,眼光闪了闪,才答道:“好。”低着头接过贺卡,往后倒在沙发上,清脆的叫了声:“王嫂,帮我那支笔!”
他不住的冷笑。真的以为自己是大小姐了么?所以才害怕被人提起,所谓“不堪”又潦倒的母亲?
贺卡旁有一枚细细的戒指。戒指已经有些旧了,色泽也微微发黑,有些暗淡。
他买它的时候,不过十四岁。看它和其它样式繁复的戒指,一起躺在白绒布上,他忽然的觉得,它是那么不同,只有它配的上她。
她曾经笑他:“玫瑰和玫瑰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因为他爱她,所以才以为她是独一无二的那朵。”
她腿上正摊着一本小王子,她笑他学了那么多年的法语,却连这样一部著名的童话都不知道,兴致勃勃的要教他。橙黄色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更加的小,一双眼睛熠熠的闪着光,仿佛漂亮的黑曜石。
他甩上车门,急急惶惶的跑上去。
她住的是一栋老楼,过道的灯,很多都坏了。他就这样在黑暗里横冲直撞,直到看见如豆的灯光,暖暖的耀在前方,他才安心。
她还在。他想,又把戒指放进了衣兜里。
他忽然又没了告诉她的勇气。
仿佛只要不说破,他和她,他们的日子,就可以一直一直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一直到海枯石烂。
如果他早知道是那样的结局,他会不会像这样放弃?
她死后的每天每天,他都这么问自己。他的脖子上系着条细细小小的链子,正中悬着一枚,同样细细小小的戒指。
门吱嘎一声开了,她就站在门口,神情和姿态,仿佛等了很久很久。
像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站在门槛上,犹豫着要不要出去。
她说:“你来了?”
他说:“是啊。”
她笑了笑,说:“真好。”
他递上贺卡,轻笑了一声:“是啊。”
这时候不知道哪家的狗,汪汪的叫了一声,接着是自行车碾过冰棱子的声音,吱吱嘎嘎。
她往门框上一靠:“下雪了呢。”
他说:“是啊。”
她掸了掸他大衣上的雪星子,笑:“怎么老是‘是啊是啊’的?”
他也笑,呵呵的不做声。
她想起什么似的,从大衣的口袋里抽出一张碟:“问小张借的,一直忘了还。”
“他就住在隔壁楼的三层,能帮我送过去一下吗?”
他觉得奇怪,却也没问,答了声:“好。”
门又哒的一声,合上了。
陈淑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离一样,整个的瘫在了地上。
她原本以为她会做不到,她以为她会在他温暖的笑颜前,落下泪来;她怕她会说着说着话,忽然的咳出一口血;她怕她会忍不住的踮起脚吻他;她更怕,她来不及送出那张CD,她唯一可以留给他的圣诞礼物。
而现在她终于可以安心。
她匍匐在地上,一寸一寸的往房里爬。
人死的时候,总喜欢可以有个安稳的倚靠。
而她,只想爬回去,躺在床上,静静的等着天黑,等着死神盖上她的眼睛,等着灵魂终于挣脱身体的束缚,结束这短而长的一生。
地板上有着紫砂茶具的碎片,其中的一片,刮开了她的脚趾,锐利的疼痛让她轻呼出声,但她依然用力的,用尽生命中所有的力气,一寸又一寸,坚定的前进。
地板有几天没拖了,上面有浅浅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是他的,那么大,她两个手都盖不住,她几乎可以想象他走路的样子,矫健的确定的,真真的健步如飞。
她已经这样的拖累了他,她再也不能拖累他。
她这么想着,已经是倦极,喉头一填,嘴角渗出血来。眼眶里,也慢慢的渗出血丝,血迹如同小蟹,缓缓的,缓缓的,爬了满脸——
就要死了呢。
她想。
好不舍得呢。
她又想。
最后,她合上眼睛,把头,轻轻的轻轻的贴在那个脚印上,微微一笑,仿若睡了过去。
血流过她的脸,流过她的耳垂,流过她的头发,流在地面上,一个脚印,终于浅浅的显出形状来。
仿佛,刻在上面一样。
刘朝儒恍惚间好像做了个梦,梦里很温暖美好,他浑身暖洋洋的不想结束。
直到门铃叮咚的响了一声。
两声。
三声。
然后门把手咔的响了一声,寒风呼呼的灌进来,但他还是不想起来,翻了个身,背对着门口。
然后门又关上了。
房子里又是一片温暖。
脚步声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