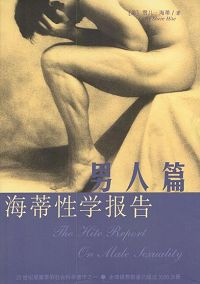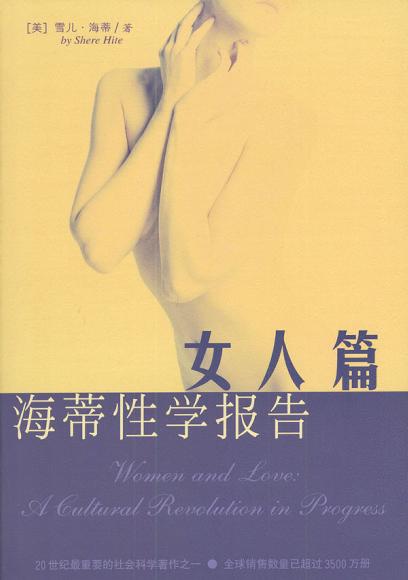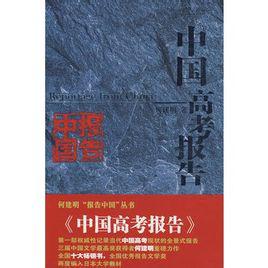食相报告-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冬天到了,住在石屎森林里的文明人,开始感到虚弱,心里面,一个声音骚动不安地高叫着:该进补了。
冬天,对于居住或路过广东的野生动物来说,是一个从野生动物变成野味的季节。根据广东省林业厅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广州人吃过野生动物。为什么要吃?45。4%的人回答说:“能增加营养。”“出于好奇”的占37%,“为了显富”的有12%。表面看来,多数人是为了摄取“营养”而进食野生动物,事实上,这里所谓的“营养”,并不是人体必需的那些化学成分,而是一种野生动物独具的滋补作用。
大多数广州人相信,秋冬是适宜进补的季节。而进补,必然是吃下若干野味、药材之类。“秋冬进补”的理论在科学上是否成立,暂且按下不论,反正,广州的冬天确实让人觉得有点虚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野生动物何以成为秋冬进补之首选,这里面学问可就大了。
前面讲了,准备过冬的野生动物,通常会长得比较丰腴,肉质也较为肥美。不过,进食野生动物毕竟不是吃猪肉,至少在野生动物“爱好者”看来,“肥美说”简直就是对他们智慧的侮辱。迄今为止,尽管尚无任何实验室数据证明野生动物的肉质里珍藏着五谷杂粮所不具备的特殊养分,抑或同一种动物在野生状态下必驯化状态下更具营养而且更容易被吸收,但是,广州人对野生动物的口腹之“爱”,却越来越是狂野,甚至甘冒吃官司的风险。
在我看来,吃野味之动机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实在不是“营养”、“好奇”或“显富”所能概括的,更不是靠一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就能说服的。
人为什么要吃野味?野生动物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比较滋补?我翻了一些书,观察了一些场面,问了一些人,也问了我自己,最后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一、野生动物,顾名思义即是野生野长,采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就体质和肉质而言,其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区别,犹如山野之人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状态,这个道理,是那么朴素直观,那么不言而喻。现在广州市面上流行的“走地鸡”,其实并不是野鸡,而是在半工业化和半野化(或仿野化)环境下养殖出来的鸡,尽管如此,“走地鸡”还是大受顾客欢迎,并且能卖出高价。“走地鸡”让顾客感受到的这番喜悦,其实与一个拥抱着参加暑期野营军训归来的子女的家长之欣慰,并无本质差异。
二、野生,而且稀有,因而更形珍贵。就消费行为而言,即是有意识地拉开距离:猪肉人皆得吃,惟我偏能食猪之在野者也。进食野生动物给人带来的快感,就建立在这种差别之上,亦即周作人所言:“一心想吃个别的肉。”如果你的思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扪心自问:为什么你可以接受野生动物园的门票比普通动物园贵呢?
三、于情于法愈不容,就愈发地有一种触犯禁忌的快感,家花不如野花香,妻不如妾,妾不如偷,都是“野意”在起作用。
四、广东人喜食野生动物之生猛。生猛是广东人对食物的独特看法,“生”就是“活”或“活力”,这个不难,就野生动物而言,要害乃在于“猛”。比方说,一只鸡,也是活生生的,但感觉上它就是欠一点火候,欠了野鸡的“猛”。“猛”是区分野生与家养的关键指标,比之于人,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想从者,皆‘态’之一字为祟也。”正是一种野态,使野生动物变成了野生尤物。
假设野生动物的确滋补,那么,作为饭桌甚至筵席之上的一道大菜,味道也是必须被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否则,不管它有多野,毕竟不可称其为“味”。
进食野生动物的动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凡吃过野味者甚至都会承认,大多数的野味,其实并不好吃。大体而言,除了野兔(与家兔分属两个品种)和野鸭、野猪以及珠江三家洲特有的禾花雀之外,其余的,例如广州常见之乌龟、果子狸,穿山甲之类,滋味根本超不过猪牛羊这等驯养之肉。即使是众口称颂的果子狸,也不会胜过羊脯。
事实上,大部分的野生动物不仅肉质粗,而且带有浓重的腥膻,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至于巨蜥、猫头鹰之类的“上品野味”,其味道就更沉重了。
猫头鹰的烹法,就是加药材熬汤,那一鼎颜色可疑的黑汤,除了能为口腔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陌生感之外,剩下的就全是药味了。
当然,野生动物基本上是一种“别问味道看疗效”的食物。以猫头鹰为例,据说疗效主要是明目。《本草纲目》则说,去毛去肠,油炸,食而能治疟疾,其肝则为法术家所用。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迄今为止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依然是奎宁,不过因猫头鹰有惊人的夜视能力,故“明目”这种象征性的暗示,与驴鞭壮阳、虎骨强关节一样,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思维方式。是啊,“良药苦口”,如果猫头鹰汤真的像鸡汤那么好味,我们反倒要怀疑它的疗效了。
保护野生动物以及禁食野味,是一种外来的主义,捕杀及进食野味,却也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
政治完全正确的动物保护主义正在令广东人甚至全体中国人蒙羞,不过,老外也是吃野味的。区别在于:在英文的餐单上,野味和游戏或者体育运动一样,皆称game,意思是打猎所得之物,是一种游戏的结果。最起码,语意上就淡化了这件被我们视为“营养”的滋补大事,就像他们把吾人心目中关乎国家兴衰、民族危亡的奥运会同样也称为game一样。
作为游牧民族的传人,西人进食野味的风俗源远流长。至于其之所以能待之以“游戏”的态度,估计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此事与滋补或一种额外的营养有关。
不猎所得的肉类,通常是野鸭和鹿,这些东西的“野趣”,除了捕猎过程,更多还体现在烹饪形式之上,即在野地或乡间农舍里生火烧烤之。尽管彼邦的野鸭比我国的苍蝇还多还贱,不过在欧洲,猎鹿还是受到法令限制的,而在遍地麝牛、野牛、野鹿和野山鸡的北美地区,法令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此外,加拿大政府鼓励并且资助国人猎杀海豹的做法,则早已臭名昭著。加国当局每年允许猎杀海豹廿六万头,对远远超出这一数额的非法捕猎更是置之不理,以致每年便有约一万只幼小海豹被杀。海豹的肉,可供人类或宠物食用,皮做皮草。至于环保组织在当地海滩发现的海豹尸体几乎都失去了生殖器官一事,在北京的某些药房里就可以找到答案:壮阳海豹鞭,三千大元一条。
澳、纽一带吃袋鼠和扫尾袋。虽然袋鼠肉已被引进国内多年,但是反响并不见热烈,可能是缺乏文化认同之故,毕竟,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野味。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老外视为文化上的一种“野味”。
()免费TXT小说下载
今之所谓“野生动物”,系相对于“驯养动物”而言。人类在成功驯化了若干食用动物之前所食之肉类,无不取自野生动物,在那个时代,就连人类自己,也统统是野生的。
人类在不断驯养野生动物的同时,也逐渐把自己由野人驯化为“文明人”。故“野生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异化的概念。
文明人对于“野生状态”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自卢梭以来一直具有正面的象征意义。吃腻了宫廷大餐的卢梭,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乡下的野果、牛羊和山泉。蒙田则写道:“我们将大自然本身经过一般的演变结下的果实成为野果……说实话,我倒应把那些被我们认为的损坏而变得特别的东西称为‘野的’。在前者,真正最有用最为自然的品质和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后者,这些品质和特点却被我们弄得黯然失色,仅仅变得适合我们败坏了的情趣了。然而,这些未经开垦地方的各种果实,与我们的果实相反,味道本身的鲜美程度很符合我们的胃口。”
尽管我不能完全依照形式逻辑做出“爱吃野味的广东人就是世界上最热爱大自然的人”这样的推论,也不可以就此断言:野味至上者和环保主义者并无原则冲突,皆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方式各异罢了。但是,不管是野果,还是野兽,合法或者非法,区别无非是此时彼时、某一地区某一资源及其消亡速度的相对而言。换言之,只要“野生/自然”和“驯养/非自然”这一类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一天不得到彻底消解,法律就将永远在跟奔跑着“拥抱自然”的人类后面疲于奔命。在地球上每天有四十至一百四十个物种与人类永别的速度之下,今天是猴子熊猫,明天是猪羊,后天可能就轮到苹果香蕉。
论烤鸭与烧鹅之优劣
烤鸭好吃,还是烧鹅好吃,这是北京人和广州人同桌吃饭时常常争论着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鸭、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一、皆为家禽;二、皆常见食物;三、烹法近似;四、肉质、肉味近似;五、分别是京菜和粤菜之杰出代表。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鸭、鹅在世的时候,外表就很难区分。色彩上,皆不出黑、灰、白三种色调,鹅头之上的那个肉銮,似乎亦不足以单独构成比较明显的识别体系。此外,鹅的体积偏大,不过,这一点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鸭之大者。
最近有报道说,在好莱坞的教育下,台湾的小朋友对于已经消失的恐龙,从谱系到种类、习性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却分不清身边的鸭、鹅。
虽然成语在形容雪片之大是选用了鹅毛,不过,以鸭绒冒充鹅绒(羽绒之上品)制成羽绒服装,则使造假者屡屡得手。中医也认为,鸭、鹅皆具养阴、益气、固肾之效,同时,两者亦同属“发物”。
在香港,男妓的谐称是“鸭”;到了深圳,提供有偿同性恋服务的于是被叫做“鹅”。当地治安部门发现,对于“鸭”和“鹅”的综合治理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那些做“鸭”的,通常都会兼职做“鹅”。比较起来,还是抓“鸡”来得比较容易。
既然如此,烤鸭和烧鹅之优劣,看来并无进行详细比较的必要,这个问题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有一个笑话,说某甲请他的朋友某乙吃饭,吃的是“全鸭宴”,一边吃,某甲一边向某乙不无夸赞地介绍说:这是“芥末鸭掌”、这是“火燎鸭心”、那是“卤水鸭肝”……就这样,一道道“鸭菜”次第而上,上着上着,突然来了一碟鹅肉。某乙遂停箸且一脸奸笑地望着某甲,一心想看他的笑话。不料,某甲却面不改容地说:“啊,这是鸭子的朋友!”
这个不算高明的笑话,本来要说的主题大概是“急智”,不过,鸭、鹅之显而易见的雷同,却使“急智”反而变得有点可笑。
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相似的事物,就越值得比较。而在烤鸭和烧鹅之间进行(或曰强行)比较的目的,乃是为了证明烤鸭与烧鹅之优劣,原来并不在于好吃不好吃。
以整体观之,鹅一开始就输给了鸭子,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做“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鹅在中国饮食中所处的劣势,是历史造成的。由于某种偶然性的缘故,中国在两千年之前成为地球上首个成功驯化了野鸭的民族。
尽管鹅在周代已被正式列为六牲,不过,那种鹅其实是野鹅,即是“雁”,李巡注《尔雅》:“野曰雁,家曰鹅。”
至于欧洲人对野鹅的驯化,我一时查不到具体的年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年份,中国人很有可能已经把鸭子和鹅都吃了个腻。
当然,吃腻了的并不是全体的中国人,而是一小撮的“肉食者”。
元代以前,中国烹饪里与“烧鹅”相似的技术,只有“炮烙”,然后是“炙”,并无今日意义上之“烤鸭”存在。唐代《朝野佥载》倒是记载过官宦人家对鹅、鸭的一种残忍烧烤:“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则回,表里皆熟,毛尽落,肉赤烘烘乃死,”
如果说,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大铁笼里,鹅、鸭还是同患难共命运的一对天涯沦落人,那么,自元代开始,随着欧洲“闷炉烧烤”(即在密封的砖炉里面,利用被烧热的炉壁所释放的热量将食物烤熟,而不是将食物直接放在火上烤熟)技术的输入中国,鹅、鸭之间从此逐渐拉开了距离,并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西式烧烤技术之所以能在元代被输入,并不是史学家所说的“对外开放”的结果,主要是这样弄出来的食物,比较符合已经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口味。
作为三百多年之后再次入主中原的另一支北方少数民族,满洲贵族对鸭子及烧烤的热情丝毫不减。清代皇室在热河狩猎时所猎得纯白野鸭,(此前的烤鸭,是黑色的南京湖鸭)以为吉祥,遂于玉泉山驯养凡二百多年,其后再次由英国人进行改良,才有了今天北京烤鸭选用的“北京鸭”。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烤鸭其实应算是一种西餐(或曰胡食)。当然,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道京师美馔,亦有赖于垄断了当地烤鸭业的山东荣成|人。在荣成|人的努力下,烤鸭由闷炉变成挂炉,面饼、大葱、甜酱和鸭子的卷而食之,也是山东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刚刚即位的载淳的除夕晚餐餐单之上,十七道菜,鸭子竟有六款之多,除了“挂炉鸭子”之外,还有“燕窝万字金银鸭子”“燕窝溜鸭条”“溜鸭腰”“燕窝炒炉鸭丝”等等。除夕晚餐的该吃什么,小皇帝可能并没有发言权,而是由皇宫里的传统所决定。因此,北京的烤鸭店在包装上至今仍刻意制造一种皇室和贵族的色彩。因此,《全聚德史话》才敢说:“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至于进食烤鸭的全过程,更是一步一讲究,细节密布。从食客入厨自选鸭子,在鸭体上挥毫题词,到荷叶面饼,甜面酱,葱段,蒜泥,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