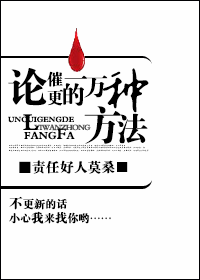八百万种死法-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乐。 我们坐在那儿,讲着故事。如果说“男孩”丹尼有职业的话,那就是搜集信息。你告诉他的一切都会在他的脑子里归档,通过把琐碎的资料拼凑起来后再四处流传,他就能赚到足够的钱让他的鞋子锃亮,杯子满溢。他会安排人们会面,从中收点劳务费。他在很多短期企业都有有限的投资,尽管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多少有些违法,但他总是能做到不惹祸上身。在我还当警察时,他就是我最好的消息来源之一,他这个线人不收费,只是要点信息当作报酬。 他说:“你记得卢?鲁登科吗?他们叫他‘帽子卢’,”我说我记得。“听说过他妈的事吗?”
虹←桥←书←吧←BOOK。HQDOOR。COM←
第10节:八百万种死法(10)
“她怎么了?”
“一个很好的乌克兰老太太,还住在东第九大街或第十大街,我记不清了。守寡多年。她肯定有七十岁了,或许将近八十了。卢多大了,五十?”
“可能吧。”
“无所谓。关键是这个和蔼的小老太太有一个男朋友,一个跟她同岁的鳏夫。他每星期去她那儿两三次,她给他做乌克兰菜,如果能找到一部不是充满Zuo爱镜头的电影,他们就会一起去看。总之,一天下午,他来了,兴奋异常,因为他在街上捡了一台电视机。有人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他说人们都疯了,把这么好的东西扔掉,他擅长修理东西,刚好她的电视坏了,这台电视还是彩色的,而且比她那台大一倍,或许他能帮她修好。”
“然后呢?”
“然后他把插头插上,打开开关看看情况如何。结果,它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而鲁登科太太呢,电视机爆炸时,她就站在它前面,当场毙命。”
“那是什么,炸弹吗?”
“你猜对了。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故事了?”
“我肯定是漏掉了。”
“呃,那是五、六个月前的事儿了。据警方判断,有人在那台电视机里装了炸弹,然后把它送给别人。也许是帮派干的,也许不是,因为那个老头只记得在哪个街区捡的电视机,那能说明什么?总之,无论谁收到那台电视机,都会产生怀疑,把它同垃圾一起扔掉。结果,它炸死了鲁登科太太。我见到过卢,有趣的是,他不知该冲谁发火。‘错在这个他妈的城市,’他对我说,‘就是这个他妈的该死的城市’。但那有什么意义?你在堪萨斯腹地住得好好的,突然,龙卷风来了,把你的房子卷到阿拉斯加州去了。那是天意,是吧?”
“大家都这么说。”
“在堪萨斯,上帝用龙卷风。在纽约,它用做过手脚的电视机。无论是谁,上帝还是其他人,都会就地取材。再要一杯可乐吗?”
“现在不要。”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在找一个皮条客。”
“第欧根尼①寻找诚实的人。你则有更大的寻找余地。”
“我在找一个特殊的皮条客。”
“他们都很特殊。有的简直就是变态。他有名字吗?”
“钱斯。”
“哦,当然。”
“男孩”丹尼说,“我知道钱斯。”
“你知道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吗?”
他皱起眉,拿起自己的空杯子,然后又放下。“他在哪儿都待不长,”他说。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事实如此。我想一个人总该有个窝吧。我不是在这儿,就在普根酒吧。你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至少我上次听说是这样的。”
“现在还是。”
“怎么样?尽管我没见到你,我还是在关注着你。钱斯,让我想想看。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
“对。哦,是星期五凌晨了。”
“别那么精确。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跟他谈谈。”
“我不知道他现在哪儿,但我或许知道十八或二十个小时之后他会在哪儿。如果那个女孩过来,帮我再要一杯酒,行吗?你也再来一杯吧。”
我努力引起那个女招待的注意,让她给“男孩”丹尼再拿一杯伏特加酒。她说:“好的。再给你倒一杯可乐吗?”
每次坐下来,我的小酒瘾就断断续续发作,现在,我喝酒的愿望就十分强烈。一想到还喝可乐,我就反胃。我告诉她这回要姜汁汽水。她把饮料端来时,“男孩”丹尼还在打电话。她把姜汁汽水放在我面前,又将伏特加放在他那边。我坐在那儿,努力不去看那杯酒,但我又无处可瞧。我希望他回到桌子这儿来,把那杯该死的东西喝掉。 我深深地吸气,又呼出去,呷着我的姜汁汽水,努力不去碰他的伏特加。最后,他终于回来了。“我说对了,”他说,“明天晚上,他会去麦迪逊广场花园。”
“尼克斯队①回来了,我以为他们还在巡回比赛呢。”
“不在主赛场。实际上,我想那儿要开个摇滚音乐会。钱斯会去菲尔特拳击场看周五晚上的比赛。”
虹←桥←书←吧←BOOK。HQDOOR。COM←
第11节:八百万种死法(11)
“他常去?”
“不常去,有一个叫基德?巴斯科姆的次中量级拳击手在预赛中名列前茅,钱斯对年轻人挺有兴趣。”
“他在他身上下注了?”
“可能吧,也许只是职业兴趣。你笑什么?”
()免费电子书下载
“想想看,一个皮条客竟会对一个次中量级拳击手产生职业兴趣。”
“你从没见过钱斯?”
“没见过。”
“他可不是一般的皮条客。”
“我也开始这么觉得了。”
“问题是,基德?巴斯科姆肯定会去比赛,但并不意味着昌斯肯定会去看,不过我看可能性很大。你想跟他谈谈,花钱买张票就可以了。”
“我怎么知道谁是他呢?”
“你从没见过他?对,你刚才说过的。你即使见到他也认不出来?”
“在看拳击比赛的观众堆里当然认不出他来。里面一半是皮条客,一半是拳击手,我根本认不出。”
他考虑着这个问题。“你要跟钱斯谈的这个事儿,”他说,“会惹火他吗?”
“我希望不会。”
“我指的是,如果有人把他指给你看,他会恨这个人吗?”
“我看他没理由这样。”
“那么,马修,你要付的就不是一张票的价钱,而是两张。庆幸吧,这不是主赛场的拳王争霸赛,而是晚上拳击场的一场小比赛。拳击台旁的位置才不过十或十二美元,就算远处的位置是十五美元,那我们的票钱最多不过三十元。”
“你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不呢?三十元买票,五十元买我的时间。我想你的预算承受得起吧?”
“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就得承受。”
“跟你要钱我很是抱歉。如果是看田径运动会,我不会收你一分钱的。但我向来不喜欢拳击。要是曲棍球比赛的话,我至少要收一百元,或许这能让你感到安慰。”
“那我该谢天谢地了。你在那儿等我吗?”
“就在门口。九点——那样的话,我们的时间会很充裕。怎么样?”
“很好。”
“我会看看能否穿点与众不同的衣服,”他说,“好让你一眼认出我。”
4 他是不难认,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外套一件亮红色马甲,白色礼服衬衫上打着一条黑色针织领带。他带着墨镜,暗色镜片镶嵌在金属框架中。每当太阳出来时,“男孩”丹尼就尽力睡觉——他的眼睛和皮肤都无法承受日光——除非在像普根酒吧或顶尖酒吧这样昏暗的地方,他连夜晚也戴着墨镜。几年前他曾对我说过,他希望这个世界有调光器开关,按一两下就可以把一切关掉。我记得当时我想,威士忌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使灯变暗,音量降低,棱角变圆。 我夸了他的打扮。他说:“你喜欢马甲?我好多年没穿它了。我想显眼一些。”
我已经买了票。前排的票十五美元一张。我买了两张四点五美元的票,这个票的位置使我们离拳击台比离上帝还远。进大门后,我把票出示给前面的领位员,并将一张折起来的钞票塞到他手。他把我们领到前面第三排的两个位子上。 “也许过会儿我还得请两位挪挪,”他说,“但也许不用,不过保证你们能坐在拳击台边。”
他走开后,“男孩”丹尼说:“总有后门可走,对吧?你给他多少?”
“五美元。”
“这样你只花了十四美元,而不是三十。你猜他一晚上能赚多少?”
“这样的晚上赚不多。要是尼克斯队或游骑兵队比赛,他捞的小费或许是薪水的五倍。当然,还得花点钱打点某人。”
“人人都有利可图。”
“看来是这样。”
()好看的txt电子书
“我是说每个人。也包括我。”
他在暗示我。我给了他两张二十元和一张十元的。他把钱放好,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环顾观众席。“呃,没看到他,”他说,“但他可能只在巴斯科姆比赛时才露面。我去转转。”
“好。”
他离开座位,在场中四处走动。我环顾四周,倒不是为了认出钱斯,而是看看观众都是些什么人。有很多男人昨天晚上就在哈勒姆区的酒吧,都是些皮条客,毒品贩子,赌徒,以及城里其他行当的混混,他们大部分都有女人陪着。还有一些白种流氓,穿着休闲服,珠光宝气,不带女伴。在票价便宜一些的位置上坐的观众是任何类型的赛事都能见到的那种大杂烩,有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有孑然一身,有成双成对,也有结队而来,他们吃着热狗,喝着纸杯里的啤酒,聊着,开着玩笑,偶尔瞧瞧拳击台上的动静。时不时能看到那种从场外赛马下注店里直接移植过来的面孔,这种扭曲的、表情变幻不定的百老汇式面孔只有赌徒才有。但并不很多,现在谁还在拳击上下注呢? 我转回身,去看拳击台。上面是两个西班牙裔男孩,肤色一浅一深,两人小心翼翼,惟恐受重伤。他们看上去像是轻量级选手,肤色较浅的孩子步伐灵活,频繁出拳。我开始有了兴趣,在最后一个回合,肤色较深的那个找出了如何避开对方快拳,顺势进攻的办法。铃声响时他赢得了胜利,看台某处传来阵阵嘘声,我猜是落败选手的亲友。 “男孩”丹尼在最后那个回合时回到座位上来。裁判宣布结果后两三分钟,基德?巴斯科姆翻过围绳,打了一通空拳。 过了片刻,他的对手进入场内。巴斯科姆皮肤很黑,肌肉发达,肩膀下削,胸肌健硕。灯光照射下,他的身体闪闪发亮,像是涂了一层油。同他对打的男孩是来自南布鲁克林的意大利人,叫维托?卡内利。他腰上有些赘肉,看上去像面团一样软绵绵的,但我看过他的比赛,知道他是一个以智取胜的选手。 “男孩”丹尼说:“他来了,中间过道。”
WWW。HQDOOR。COM▲虹▲QIAO书吧▲
第12节:八百万种死法(12)
我扭头看去。拿我五美元的那个领位员正领着一男一女入座。她大约五英尺半,赤褐色垂肩长发,皮肤就像细瓷。他六尺一、二,重约一百九十磅,宽肩细腰窄臀,头发较短,非洲发型,亮棕色皮肤,身穿驼毛运动夹克,法兰绒休闲裤。他看上去像是职业运动员,或炙手可热的律师,或前途无量的黑人实业家。 我说:“你确定?”
“男孩”丹尼笑道:“跟一般的皮条客不同,对吧?我确定。那就是钱斯。希望你的朋友没把我们安排在他的位子上。”
他没有。钱斯和他的女孩的位置在第一排,靠近中央。他们坐下后,他给领位员一些小费,几个观众跟他打招呼,他回礼示意,然后走到基德?巴斯科姆所在的拳击台角,跟那个拳击手及其助手说了些什么。他们协商了一会儿。然后,钱斯回到他的座位坐好。 “我想我得走了,”“男孩”丹尼说,“我真的不想看这两个傻瓜打个你死我活。你不用我引荐吧?”
我摇摇头。“那我在伤害罪开始实施之前最好溜走——我是指台上。他不必知道是谁指出他的吧,马修?”
“我不会告诉他的。”
“很好。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服务——” 他走到过道,看上去想喝去上一杯,但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酒吧没有冰镇伏特加。 广播员正在介绍选手,报出他们的年龄,体重和家乡。巴斯科姆二十二岁,从未失过手。看来卡内利今晚不会改变这一记录。 钱斯旁边的两个位子空着。我本想坐过去,但一直没动。警告铃响起,然后第一回合开始的铃敲响了。这个回合两个选手动作缓慢,若有所思,谁都不急于亮出实力。巴斯科姆出拳强劲,但卡内利总是成功地避开。谁都没有实实在在地打到对方。 这个回合快结束时,钱斯边上的那两个座位仍空着。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专心地看着拳击台。他肯定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不露声色。 我说:“钱斯?我叫斯卡德。”
他扭过头,看着我。他棕色的眼睛闪着金光。我想起了我委托人的眼睛,那虚幻的蓝色。当我昨晚在酒吧打探消息时,他没事先通知便去她的公寓收钱。今天中午,她打电话到我的旅馆,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害怕,”她说,“我想,要是他问起你,问我一些问题,那怎么办。但还好没有。”
他说:“马修?斯卡德。你在我的联络处留话。”
“你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认识你,我不给不认识的人回电话。你一直到处打听我。”
他的声音低沉浑厚。听上去像是受过训练、上过播音学校。“我想看这场比赛。”
他说。 “我只想跟你谈几分钟。”
“比赛时和中间休息时都不行。”
他眉头皱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