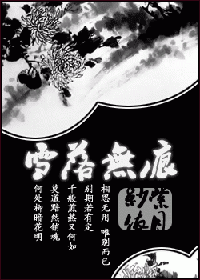雪落马蹄-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笑声:“老夫如有意与尔等为敌,谅你们寿期无多!”
星月之下,晏星寒借着淡淡的月光,看清来人是一个十分衰老的老儒模样的人物。
白面长须,穿着一身宽大的灰布长裰,腰系丝绦,身材枯瘦,一时确实想不出武林中有这么一个人物。
晏星寒在武林中,垂享盛名已有数十年之久,一身软硬轻功夫,确实亦非“沽名钓誉”之流所可比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心服?一股无名怒火直冲脑门,他仰空一声长笑:“好!我晏某不知自量,朋友,今夜我要斗一斗你,你先把小女放下来!”
说着他单手一提长衣,正要纵身而上,那树梢上的怪人,却已如同一只大鸟似的“呼”一声直落下来。
晏星寒闻声向外一纵,只觉头顶冷风一扫,那怪人发出一声长笑,等到晏星寒倏地回过身时,对方已远在十丈开外,倏起倏落,直向墙外翻去。
晏星寒一生几曾受人如此戏辱过,不禁老脸一红,怪啸了声:“穷酸!你哪里跑?”
他口中说着,足尖向前一点,用“龙形乙式穿云步”,向前弹了有丈许远近。就在他身子略一沾地的刹那,口中冷叱一声“着!”随着右手向外一翻一扬,“哧”的一股尖风,一枚“五云石”,直朝着那人脑后打去!
那老儒身子正要腾起,闻声回头一笑,一探右手,以袖沿把五云石兜在了袖中,嘻嘻笑道:“还有四块,都来吧!”
晏星寒不由吃了一惊,对方竟知道自己手中尚有四块五云石,他不及思索,以“反身观腕”之势,把四枚五云石以“一钉一”的打法,振腕打出!
他这种打法,堪称武林独步。江湖上以此为暗器者,虽不乏人,可是能像晏星寒这种打法的,却仅此一人。四枚暗器出手,成为一线,由前面看,只见其一,这种打法,真可称得上“高明”二字。
那酸儒高叫了声:“好!”
只见他仍然一手夹着晏小真,只把身躯矮下半尺,直伸右手,像风车似的,旋转着大袖,只听得“叭叭叭叭”四声脆响,全数落入他的袖中。
发暗器者绝,接暗器者更绝,只此一手,已把晏星寒吓了个面无人色。
他自知自己这一身功夫,和这怪人比起来,尚还差着一段距离,所谓“光棍一点就透”,晏星寒在这点上来说,还是一个自量的人。
这一惊吓,酒也全醒了。
他后退了一步,瞠目道:“朋友!你报一个万儿吧!我晏某人所会的,可全是成名露脸的英雄!”
这人发出一声怪异的短笑:“晏星寒,老夫如不看在当年你和那老尼姑一念之仁,饶了罗化后人一命,今夜岂能如此开恩!”
他又是一声低笑,接道:“要是换成朱蚕或是裘海粟二人之一,今夜我定叫他血溅当场!你苦苦问我作甚?”
说着他正要再次纵身,晏星寒忽进一步道:“你是……”
这人倏地回头,两弯淡眉一分:“南方有怪鸟,有时也北飞。晏星寒,放过今夜,来日再会,老夫可不会如此便宜你了!”
他说着回身纵起,倏起倏落而去。
晏星寒口中念着:“南方有怪鸟,有时也北飞”,忽然打了一个冷颤,脱口道:
“哦,南海一鸥!”
他猛然纵身而前,口中叱道:“桂春明,你回来,老夫有话问你!”
淡月疏星之下,只见那老儒回身一声冷笑:“晏星寒!好歹由你,老夫言尽于此,令媛且随我去,老夫保她不死!”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再不停留,如星丸跳掷似的,翻出了围墙之外。
晏星寒跃上了墙头,茫茫黑夜,早已失却了此老的踪影。他站在墙头上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长叹了一声,心知即使是追上他,也是枉然,或许受辱更甚。他发了一会儿呆,才转身回宅而去。
心存必死的晏小真,做梦也没想到,竟会突然蒙人所救,虽然她在这人腋下,感到异常羞辱,可是在此生命攸关之际,也只好暂时忍耐了。
她耳中听到父亲与此人的对白,知道这人定是江湖中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可是她却没有机会与这人说话。
直到离开家,飞驰了一阵之后,来到了一片树林之前,这人才停住脚,松开了手笑道:“姑娘你活动活动身子,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小真目含痛泪往下一跪,叩头道:“难女多蒙老前辈搭救,恩重如山,只请老人家赐告大名,以志不忘!”
这人嘻嘻一笑道:“小姑娘,你站起来,我们不是外人!”
小真怔了一下,心存疑惑地站了起来,一双妙目在这人面上游视了一番,只见这人一张惨白无血的瘦削面孔,一双深凹的眸子,两道秃白的眉毛,头上稀疏疏的一束头发,绕着一个书生的发髻。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士打扮,却总觉不顺眼。
他那一条瘦如旗杆的躯体,看来真有点“弱不禁风”,如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实难相信此人竟负有一身绝世奇功。
她眨了一下眸子,面色微红道:“弟子也许太……太健忘……你老人家是……”
这酸儒嘻嘻一笑:“你原本就不认得我啊!可是我说一个人,你总不会不认识!”
小真呆了一呆,嗫嚅道:“前辈清说来!”
老儒点了点头:“在府中承当帐房的那位谭啸,就是老夫的得意弟子,姑娘你认识他吧?”
小真不由倏地一惊,当时又惊又喜,忙要往下拜,却为这老儒一把扶住了,他笑了笑:“你不要多礼,我那可怜的徒弟,如非姑娘相救,焉能会有命在?老夫却应向你致谢才是呢!”
小真不由含泪道:“弟子技艺浅薄,以致令谭兄险丧生命,老前辈不要见罪!”
南海一鸥长叹了一声:“姑娘何出此言?老夫太惭愧了,小徒投府之时,老夫曾多次往探,更得悉姑娘对他一片见爱之心,满以为短时不致有所差池……”
说着又叹了一声:“却想不到,令尊及其老友,意欲斩草除根……如非姑娘,小徒不堪设想了!”
小真为桂春明这几句话,不由触动了伤怀,想到了谭啸的无情,一时忍不住热泪籁籁而下。
桂春明看在眼中,早已心中了然,不由微微一笑道:“姑娘你不要伤心,你们之间的事我都知道。你放心,徒弟虽糊涂,师父却心里有数!”
小真不由玉面一红,忙收敛了眼泪苦笑道:“弟子只是感叹自己身世,倒不是为别的!”
桂春明笑了笑并不说破,他看了一下天道:“你先随我到钟楼休息休息吧,一切事情明天再说。你放心,现在有我在你身旁,你爹爹或是他那几个朋友,都不敢把你怎么样!”
晏小真点了点头,偷偷地看了他一眼:“老前辈……你老的大名是……”
桂春明笑了一声,爽然地道:“我姓桂,名春明,人称南海一鸥。”
晏小真不知武林中有这么一个人物,点点头恭敬地记在心中,改口道:“桂伯伯,你头里走,我跟着你,不要紧的!”
南海一鸥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功夫挺不错,我知道!”
他说着身形纵起,似有意试探一下她轻功如何,一路倏起倏落,向前飞驰而去。晏小真也施展开轻功提纵之术,在后紧紧追随着,起先倒还能跟上,谁知驰出两三里以后,她可就显然落后许多了。这时心中不由暗暗羞急,忽念到,连父亲那么好的轻功,尚还跟不上他,我怎么行呢?
可是却又不好意思出口请他等一等,只得咬着牙拚命地赶着。
她这一运全功飞纵前驰,确实也十分惊人,身形倏起倏落,宛如脱弦之箭。无奈何前面的桂春明,远远地不十分用劲地行着,一任自己运出全功,仍是差着一段距离;并且这距离尚在继续增长之中。
等到绕过了乱石山坡,竟然失去了桂春明的踪影。晏小真不由怔怔地站住了脚,急得直想哭。
忽然,头顶上一声长笑:“不错!不错!一个姑娘家有这种功夫,已是极为难得了!”
小真转身看时,却见南海一鸥不知何时竟坐在自己头顶丈许高下的一片石坡上,两只手抱着膝盖,正自点头微微笑着。
晏小真不由玉脸绯红,羞涩地叫道:“桂伯伯,你老人家别取笑我了!”
桂春明飘身而下,哈哈笑了两声,他似乎对这姑娘印象特别好,点着头道:“是真的!有工夫时,我教给你两手,你再勤练练,以后就不得了啦!”
小真不禁大喜道:“谢谢桂伯伯!”
这时南海一鸥眯着一双小眼,用手向侧处指了指:“你看见没有?那是个钟楼,我们上去吧!”
他说着吸了一口长气,用“蜻蜒点水”的功夫,一连三个起落,已到了那钟楼下面;然后再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蓦地拔身上了钟楼,黑夜里真像是一只凌霄大雁。
晏小真看在眼中,心中不禁大为折服,当时也跟着以“一鹤冲天”的轻功拔上了钟楼,可是总觉得险得很,脚下所踩的瓦面,都生了青苔,再被雨水一淋,十分滑溜,踩在上面,可真有些提心吊胆!
这时“南海一鸥”桂春明已由窗口翻了进去,小真也跟着进入里面,只觉楼内地势甚大,四面开着洞窟,风吹进来“嗖嗖”直响,连灯也没法子点。
所幸小真内功甚佳,夜中视物功夫也颇不弱,只见里面有一张木床,一张破木桌子,床上空空的没有被褥。桂春明叹了一声道:“这地方不比中原,我这异乡客来到这里,只有在这地方将就了!”
他指了一下床道:“姑娘,你等会儿可上床去睡,隔壁还有一间空房子,我到那边去!”
小真讷讷道:“这床还是伯伯你睡吧,弟子到隔壁去也是一样!”
桂春明摇手笑道:“你不要与我客气,按理说,应该找一家客栈住下,只是怕你父亲又去找事。”
晏小真不由低下头,她紧紧地咬着下唇,想到了这种遭遇,她真想哭。
桂春明叹道:“你把背上包袱解下来吧!你也用不着伤心,有些事情,是预料不到的。试想今夜我若不把你救出来,你不是要死在你那狠心的爹爹手里了?”
晏小真点头轻叹了一声,她解下了背上包袱,把它放在床上,见那张破桌上,有一个瓦罐和两个茶碗,桂春明笑了笑:“喝吧!那水是干净的,我白天灌的!”
晏小真倒了两杯,为桂春明送去一杯,自己呷了一口,坐在床上,秀眉微微皱着。
桂春明见她这个样子,不由笑了笑道:“天明以后,你打算如何呢?”
晏小真茫然地摇了摇头:“伯伯!我不知道,我没有地方去!”
她看着桂春明,嗫嚅道:“伯伯!我跟你去好不好?”
桂春明嘻嘻一笑,连连摇头道:“那怎么行呢?你跟着我太不方便了,我一个人也是去无定所,而且……”
他龇牙笑了笑:“以后的日子,我给你爹爹和那几个朋友还有得好扯呢!你跟着怎么行?”
晏小真不禁淌下了泪来,她仰着脸问:“我爹爹他们,和谭大哥到底有什么仇呢?
你老人家知不知道?”
南海一鸥看了一下窗外,冷冷一笑,说道:“再也没有我知道得清楚了……唉!这真是一段不可化解的宿仇旧恨啊!”
晏小真听得心头怦怦直跳,当时催着问,桂春明认为没有瞒她的必要,就一五一十把昔日一番经过说了一遍。直把晏小真听得胆战心惊,冷汗直流,她抖颤颤地道:“伯伯!这么说,即使是我父亲不杀谭大哥,谭大哥也会……”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点了点头道:“我想是的!”
晏小真不由吓得猛然站起道:“哦……这太可怕了……桂伯伯,你……你……还是叫谭大哥忍一忍吧!”
桂春明侧视了她一眼,叹息了一声道:“姑娘,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谭啸二十年来忍辱偷生,为的是什么……这是办不到的!”
晏小真不由神色大变,她讷讷道:“那……那怎么办呢?”
桂春明立起身来,来回走了几步,哼道:“姑娘!血债必需血来偿还。且不论罗化当年是否该死,可是谭啸身为他后人,绝无不报此仇之理!”
晏小真失神地又坐了下来,这一刹那,她才想到为什么谭啸对自己,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的原因,以如此世代血仇来说,自己和他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人,那是彼此绝不能相容的。
她这么想着,宛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一时冷汗涔涔而下。
桂春明似已洞悉了她的心,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大可放心,你对谭啸只有恩没有仇,他不是一个糊涂的孩子……”
小真苦笑了笑,低着头不发一言,她原来想随着桂春明去找谭啸的心思,不由顿时打消了一个干净。倒不是她对谭啸有了成见,而是她羞于再看到他了。试想一下,自己父亲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呀,自己怎好再去找他?
她又想到了依梨华,如今生死未定,如未死,此刻定必和谭啸在一起打得火热,自己更不必再去自讨无趣了。
想到这里,她真想扑倒床上大哭一场,心中说不出的酸甜苦辣咸,像倒了一个五味瓶似的。
桂春明见她只是坐着发怔,自己也不好同她多说什么,叹道:“姑娘你休息吧!天不早了。”
小真只管发着呆,似乎没听到一般。桂春明摇了摇头,自己慢慢走了出去,到隔壁一间房中歇息去了。
辗转在木床上的晏小真,由于过多的心事,怎么也没有办法入睡,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又躺下,眼泪把她那个用来当枕头的包袱都打湿了。
钟楼外正刮着狂风,呼呼的风由四面八方灌进来,真有点凄惨的味儿。
这个时候,晏小真轻轻下了床,她把那个当枕头的包袱重新背在了背上,咬着唇儿发了一会儿呆,心里一再鼓励着自己:“走吧!还是走了好,要不怎么办呢?我还能去见谭啸吗?”
想着又流了几滴泪,偏头听了听隔壁,静静地没有一点鼾声,她又想:“不要吵醒了他,还是我自己走吧!”
于是她下了决心,就手摸了一块木炭,在桌面上摸黑写道:“桂伯伯,弟子还是走了得好,不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
她没有留名字,虽然脑子里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一时却也只好这么写。写完了她把黑炭收入百宝囊中,用手揉了一下惺忪的睡眼,听到远处有人敲着梆子,“笃!笃!
笃!笃!”响了四下,她知道已四更了,天不久就亮了。她理了一下乱发,又紧了一下腰上的带子,悄悄地走到窗口,探头看了看外面,月亮照得倒还明亮,只是这附近是一片树林和乱石岗子,冷清清没有人家,野狗汪汪地吠着,听着真有点怕人。
别看她有一身功夫,可是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