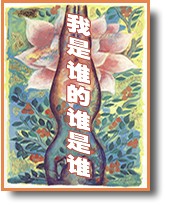谁的爱情不上锁-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表婶眉开眼笑:“好啊!”
从此以后,素贞和她姐姐每月往家捎钱,还接她娘上青岛逛街,给要出嫁的三姐办嫁妆。这件事轰动了全村,都羡慕焦家有两个能挣钱的闺女,纷纷效仿她们去青岛淘金。临村老万家的儿子大魁也随着这股潮流,挤进了小鲍岛的大杂院。
素贞再不是那个扎着小辫的乡下小嫚了,她的手飞快,一大摞“大鸡”和“婴孩”牌香烟的包装纸在她手里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码一码的香烟。她学会喝斥旁边案子上10岁的小栓,不准他们钻到案子底下弹玻璃球,她学会教育11岁的根儿不准玩火,一旦烧了手,就把他抱到厂医务室。素贞已成为大英烟草公司数得着的熟练工人。
转眼到了1941年夏天,厂里“歇伏”的日子,六月十三这一天,素贞沿着辽宁路,走过和兴利油坊去厂里领工钱。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来了。
她这天穿着粉红色的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白纺绸裤子,小脚上裹着一双银缎绣花鞋,打着白底花洋伞,腋下别着水绿洒花湖纺手巾,腰上娇俏地露出一小节大红腰带的流苏穗头。现在的素贞,已经一口气窜成身高1米65的大姑娘,转眼就21岁了,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青岛大嫚。
大柳树下坐着华北火柴公司的股东徐维礼,他穿了一身白苏罗夏衫,摇动一把白团扇,眼前紫榆百龄小圆桌上,摆着刚沏好的西湖龙井。他瞟了远远走来的素贞一眼,用带宁波口音的官话对丛大老板说:
“侬青岛妹妹蛮漂亮。”
“当然,这是大英烟草公司的人,就是摩登,哪像我们火柴厂的?青岛有句话叫:”大英出摩登,火柴出妖精。‘“
“哈哈哈,好个摩登,好个妖精。”徐维礼这个略微发福的中年人“哈哈”笑着站起说,目光一直追着素贞。
焦素贞此刻正走到跟前,啐了一口,不高兴地说:
“你说谁妖精?”
徐维礼再次“哈哈”大笑,盯着这个细高挑的青岛大嫚走出老远,看一条大辫子一甩一甩地拖在她身后。
从此以后,素贞每走到这里,便看见那个南方男人在柳树下喝着大茶,偷窥她的一颦一笑。
好景不长,素贞很快不在路上走了,日本人在青岛登陆,接管了烟草公司。工资减了,馒头变成了橡子面窝头,工人开始往家偷烟,日本人就大批开除工人,让偷烟的女工脖子上挂满香烟游厂。
终于,连大鼻子彼得都被日本人软禁起来了,在《青岛新民报》这份日伪报纸上,“英”、“美”两个字的右边被加上了大大的“犬”字,作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声援。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全部被赶回家,另换一批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付给她们低得可怜的工资。
素贞消失了,爱看她的南方人也消失了。
街上满马路日本膏药旗,美国轰炸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家家要挂红黑两层的防空窗帘,玻璃上用胶布贴着“米”字,门口放着准备灭火用的沙子和水桶。素贞她姐姐已嫁人,她也要收拾铺盖卷在大魁的护送下回乡。
身高马大的大魁早已是火柴厂的老工人,当年焦家大娘曾将素贞的四姐淑英许配给他,可是淑英进城不久就嫁了人,大魁就一直未娶。眼见着素贞越发出落得像她姐姐,而且身材高挑,比她姐姐还水灵挺拔,大魁打心眼里喜欢她。可他一个穷工人,住在6平方米的工人房里,只有窗棂子和封窗纸,他哪里配的上“大英”的女工。
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日的青保游击队在谦祥益绸布店门口放下定时炸弹,还在大麦岛杀了日本顾问乔智星,日本人疯了一样地大搜捕。日本兵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大姑娘,就围上去调戏,嘴里咕噜着:“花姑娘,花姑娘。”素贞她们都把大辫子藏进青色竹布棉袍里,脸上抹灰,打扮成中年妇女的模样。
反正青岛是呆不下去了,素贞今天要去火柴厂,大魁在那里等她一起坐火车回高密。
兵荒马乱中离开青岛,素贞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是为了怕回去过苦日子,而是她已经彻底融进了这座城市。她习惯了去湛山寺烧香,习惯了逛台东萝卜会,习惯了吃金诚包子铺的包子,还有劈柴院的豆腐脑,“西大森”的油炸糕。她现在说一口青岛话,用牙粉刷牙,连高密大黄牙都不黄了……
这一切马上就要消失了,怎么让她不伤心。
这一天,她朴素得像个村姑,穿一件二蓝色仁丹士林布棉袍,依旧像来时那样挎着蓝花包袱,只是包袱变得很大很沉。里面不光有给她娘买的珠羔里子的小皮袄,还有给她侄儿做棉袄面的品蓝摹本缎,甚至还有几斤万春盛的点心。东西再多,怎么也装不下她眼里的青岛。
大魁却很高兴地直搓手,他一见素贞就想,和她一起回去,添置两亩地,过老婆孩子热坑头的日子他也知足了,他也打谱不回来了。这一辈子,能娶到焦素贞,就是他的最大愿望。
在火柴厂院里,素贞先从怀里把大魁的照片拿出来,羞答答递给大魁。为了回家,两个人每人在辽宁路照相馆照了几张相。大魁红着脸说:“你收着吧,反正回家还有的是时间看。”
可是,正当素贞跟着大魁要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一个带南方口音的男人突然在背后大声说道:
“大英出摩登,火柴出妖精。”随后是一串爽朗的大笑。
大魁赶紧行礼:“徐先生,你好。”徐维礼身穿古铜色银花缎长衫,不理会大魁,却径直走到素贞面前,笑吟吟地问:
“请问小姐贵姓?”
“你不是叫俺妖精吗,还问什么?”素贞认出来眼前的男人,不高兴地要拉大魁走。
“慢,小姐能不能赏光看样东西?”
素贞迟疑地跟徐维礼进了帐房,空留下大魁站在院子里不安地向上张望。
()
徐维礼回到帐房,桌面上乱堆着些青布面、梅红签的帐簿,他从底下拣出一个画轴。素贞正疑惑,徐维礼“哗”地展开了画轴。
展现在素贞眼前的,是她夏天穿着粉红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的白描仕女画,旁边端端正正盖着徐维礼的大印。
不用再说,徐维礼这类模仿《牡丹亭》那类才子佳人的小把戏,唬住个北方小脚姑娘绰绰有余。
“你把俺画得真俊!”素贞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
徐维礼把画轴卷起来,又仔细用红缎带扎好,郑重送到素贞手里。素贞惊慌地连连往后退,一边摆手,一边说:“徐先生,俺哪敢要你的东西,俺不知怎么谢你。”
徐维礼哈哈大笑说:“谢什么?小姐如何称呼,侬告诉我,这就是最好的答谢了。”
素贞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抬眼偷偷看着徐维礼说:“俺叫焦素贞。”说完,抱着画轴转身跑下楼。
徐维礼在楼上看着素贞和大魁肩并肩走出厂门,惋惜地摇了摇头。
素贞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这趟回乡是要跟大魁成亲的,她们闯荡青岛的这帮童工,都二十多岁了,早该成家了。
大魁坐在火车上一路瞅着素贞笑,弄得素贞不好意思,嗔怪他:“看什么,看进了眼里扒不出来了?”大魁幸福地直搓手。
好景不长,车到蓝村站就停住了,车下一排一排的日本兵让大魁再也笑不出来了,日本人在胶济铁路沿线查青保游击队,决不放过一个人。
一个矮胖的日本兵在车厢里横冲直撞,查每个人的良民证,查到素贞时竟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掐了掐她的腮帮子。大魁火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干什么?”素贞小声说:“算了算了。”大魁刚坐下,一只肮脏的大手冷不丁向素贞的胸脯摸来,大魁一把抓住这只穿日本军装的胳膊,反手就拧了起来,日本兵痛得哇哇大叫:“青保的干活!游击队!”正在盘查的日本兵马上一拥而上,车厢里大乱,大魁抢起胳膊左右出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满脸是血,被日本兵押上卡车,往市里开去。
素贞在混乱中逃下火车,等她辗转一路回到小鲍岛大院时,吓得一头扑到她表婶身上,表叔一听大惊失色,青保游击队刚杀了个汉奸,大魁被抓去了那可是死罪啊!
果然,枪毙告示很快在日本宪兵队贴出来了,大魁列在其中。素贞她表叔带回这个消息时吓得上下牙直打哆嗦。
素贞一听,吓得几乎瘫在地上,她表婶正在那儿重新收拾素贞的东西,拿着画轴突然惊喜地说:“素贞,你认识徐大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可能大魁还有救!”
素贞顾不上哭了,抱起画轴就跑出去。
果然,徐维礼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应酬。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了日本宪兵队的植广健太郎和几个汉奸,还让仆人抬上一小箱银元作见面礼,又出重金请顺兴楼王老板求了清末遗老的字画送礼,酒足饭饱后,徐维礼陪他们逛了平康里的上等妓院,好一通忙活。
大魁遍体鳞伤地被放回来了,和素贞抱头痛哭,不是哭他的死里逃生,而是为素贞——为报答徐维礼的救命之恩,她答应做他的外室。
1942年初冬,焦素贞坐着徐维礼的汽车去新南京开记理发馆烫了头,然后和他去天真照相馆照了结婚像,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婚礼,她嫁的是火柴公司大股东、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商人徐维礼。她要住的新房是胶东路标准的公馆房,两层,带一个院落,有观海露台,是徐维礼按照他在上海福熙路的公馆图纸盖的,很有气派,洋味十足。
新房里摆满柚木家具,8个大樟木箱,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梳妆台上摆着银粉盒、银漱盂、银花瓶,屋中是一张带帐子的宁式大床。这张红木大床,有描龙雕凤的床门,铺着舒适的棕棚,三面镂空花板下还有好些小抽屉,纱绡帐子上绣着仙女,床前还有绒脚凳。这是徐维礼专门从出产宁式床的浙江乌镇定做后,用轮船运来的。
至于珐琅自鸣钟、留声机、缀有小绣球的墨绿色窗帘等稀罕物,全是从上海采买来的正宗货,甚至素贞穿的软缎绣睡衣、小金表、垂脚面的十几件乌绒阔滚软缎长旗袍,也各有品牌和出处。
喜得素贞她表婶子说,这侄女是掉进“福墩子”里去了。婶子给素贞穿上上海买来的洋婚纱,扶她坐上花车,高兴地闭不上嘴,直唠叨:
“‘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大太太在上海,当个二房一点不寒碜。俺家素贞算是熬出头了。”大杂院里的人都很巴结地叫她“二姨”,让她享福别忘了老邻居。
果然,徐维礼对他的北方“二姨”宠爱有加,下班一回来就教素贞跳舞、识字、打麻将,还带她到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牛排馆,吃两元钱一份的正宗德式牛排,到青岛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跷,跑旱船,赏钱是每天两块,直耍到正月十五,那时他就回来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徐维礼“悉悉嗦嗦”挑开帐子下了床,从柚木大橱里翻出个紫檀匣子。他小心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让素贞张大了嘴的宝贝。那是一串金光灿灿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挂着带有宝石的小金锁,徐维礼娴熟地把小金锁下面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一拧,鼓鼓的心形小锁“哗”地开了,就着台灯的弱光,素贞接过来仔细一看,惊叫了一声:
“我的天,真是稀罕人。”
金锁里左右两瓣各镶着徐维礼和焦素贞的小像,更绝的是那把小金钥匙小到比小手指甲还小。徐维礼告诉她,这是早年从英国首饰商那里买来的,南非的黄金,巴西的天然水晶,米兰的金匠打造的,这东西连大太太都不知道。然后,他扣上金锁,撩开素贞的长发,仔细挂在她玉一样的长脖子上。又亲昵地趴在她耳朵上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态度郑重。
素贞惊讶得半宿睡不着觉,以她的经历,她只知道青岛的东镇、西镇,连四方都不大去,这些绕嘴的外国地名,她听都没听到过,还有老爷耳语的秘密,让她心里直跳。
但是,小金锁凉凉地躺在她的胸前,老爷说过,这件宝贝是专门为她置办的,名字叫情人锁,这是她惟一能理解并记清的。
一大早,徐维礼就穿上皮袄,戴上羊皮礼帽,坐汽车走了。素贞从观海露台上目送她男人离去,竟有永别的感觉。
果然!徐老板一去3个月没有音信,这期间曾让厂里的账房送过两次钱,其中一次大魁还跟着来过。素贞一见大魁,眼圈发红,大魁急得搓着手问:
“‘二姨’过得不好吗?”
素贞忙给他使眼色,当着外人她没法说什么。越这样,大魁就急得满屋子乱转,眼瞅着素贞噙着泪,却只能跟着账房先生走了。
过了几天,大魁给她送来一小车地瓜、炒花生、苞米面等家乡土产。素贞不知该说什么,趴在露台上目送大魁的背影,胃里直涌酸水。
徐维礼不在家,素贞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每天除了看看海,让杏花去买菜、做饭,买回些大虾在院子里晒干,捎给她娘;或者回小鲍岛的院子里蹓跶一趟,看看她表叔表婶子。
再闲得无聊,她就去看隔壁林公馆家林律师两口子。这两人因为无儿无女,空守着大房子,就开始无休止地繁殖猫和狗,还要给这些宠物像孩子一样过三日过百岁,向邻居们挨家送长寿面。有一次生了只小母狗,取名小花,直接就送来徐家。素贞整日瞌睡,也懒得管。偶尔让杏花陪着去永安大戏院看看京剧,也提不起精神。
终于,徐维礼离开青岛3个月零20天的时候,坐着汽车回来了。素贞吓了一跳:徐维礼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还不到50岁的人,就佝偻了腰,拄上了文明棍,而且身后还多了个说上海话的仆人阿宽。阿宽一进门就教训杏花说,老爷生了病,大太太亲自把他送到飞机场,以后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