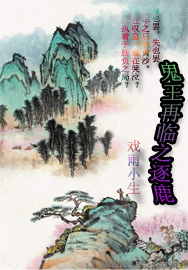惊雷逐鹿-第6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感觉,西北统治者的举措都是在以邻为壑,祸水外引。他在不停的对外扩张中,将内部潜藏的祸端隐患,一点点地疏导引流向外。他甚至于不惜将‘分封’这种,在中土历史上多次被证明了的,很容易引发大帝国内乱甚至崩溃的封爵制度重新拾起,稍加改良,就打着复古的旗号,有条件的逐步推广施行开来。我看,这是因为以他们现有的力量,还不可能完美掌控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地区,用中土先贤的话来说,就是‘鞭长莫及’。在那些远离腹心、远离中枢的偏远地区,他们必然依赖分封的贵族来统治地方臣民。”
两名传教士的探讨,肆无忌惮的谈论西北的最高统治者,彼此对话都是以义大利亚的方言,倒也不虞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先期到西北治下传教和做官的那些西洋传教士,已经在信件中提到,西北官方还是有些人懂得拉丁语的,尽管数量很少,两名传教士这时当然会谨慎一点,只用义大利亚南方的方言交谈。
“西北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很喜欢财货,不过——想要让世界上掌握着权力的人不爱财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当权者的他有着更大更远的目标。
西北现有的局面,听说是在战乱之后近乎于废墟一般的情形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期间还经过多次血腥清洗。或许这才是关键,这才是西北得以撇开儒学、儒生,另起炉灶,‘重辟鸿蒙’的关键。”
罗务禄在一大堆义大利亚方言中,夹杂了一个中土汉人的词语‘重辟鸿蒙’。不过,他用中土官话说的这个词,哪怕是中土帝国的京畿人士也未必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义大利亚腔调的中土官话,谁能轻易听得懂呢?也许只有最熟悉他的石明楷,能够知道他想表述的意思。
两名教士谈了一会,石明楷仍继续记录他的膝上笔记,而罗务禄则在一旁乘凉,当然他说这是‘先睹为快’,话说石明楷的一手花体字还是非常漂亮的,让人欣赏起来有着一种愉悦之感。
“西北似与中土他处有所不同,此地的‘佃工户’——不是佃户——每年可领到口粮、花红,每月还有工钱、赏钱可拿,一如作坊的‘雇工人’或者是这里人说的‘长工’、‘短工’,他们不是佃田耕作的‘佃户’,而是纯粹出卖劳力和农艺技能来维持生计的‘佣工’。西北出现这种状况,似乎是因为这里的人口不足,劳力短缺,虽然中土帝国的人丁绝对是非常之多。马耕、牛耕以及各种农具都因为人口不足而在西北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石明楷在膝头上如斯记录着,这是他踏上西北土地以来,从形形色色的各种路人角色那里,从听到的各种情况中,整理归纳出来的一种看法,至于这看法是对是错,还有待于以后的验证。
“听说西北有很多大农庄、大牧场,渭北数万顷官地就全部由一个大银庄‘包租’。
我还听说,西北地方,散在的自耕农户、中小地主,也很有不少。这些人大部分是获得了军功爵的军人家庭,而且他们为了与大农庄相抗衡,多半加入了某种合伙联营形式的农庄,是自耕农户与中小地主的合伙经营,通常雇佣着一些管庄头目和雇工人。
听说在这种农庄干活的佣工,‘东家’们会定期发给口粮、工钱,也有‘花红’,我想这应该是某种赢利分成;据说农忙的时候,干活好的人,能拿到东家的赏钱;这种合伙农庄,合伙人也可能同时就是管庄头目和雇工人,据说有的农庄还有‘身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可能是与‘花红’相似的某种赢利分配方法;本地很多人,很多与我们从潼关出发的旅客,还有从长安出发的旅客,都说西北幕府会不断地派出人员指导庄田如何经营,也许是真的。他们提到的‘农学馆’、‘商学馆’,似乎应该是西北统治者的官办学校。
但是西北仍然存在佃户,他们有‘永佃之权’,而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则有着‘田骨’、‘田皮’等说法,非常复杂,我只能是肤浅的了解,留待以后细问。”
罗务禄在旁边细看一页毛边纸,是石明楷已经写好的笔记。石明楷在拼写和语法上,虽然是以拉丁文为主,但其中又夹杂了大量‘义大利亚’、‘法郎思’的方言俚语,以至纸上所记有一半左右,他人较难索解其中真实含义。这其实是个防止泄密的小伎俩,并不非常可靠,只要是比较熟悉石明楷的人,多花点时间大概也能解读石明楷在纸上所记的内容,譬如罗务禄阅看石明楷的记录就毫无困难。
“你还漏了一样,‘代耕互助社’,它是受到官方重视的。西北的很多农庄除了自己雇佣的工人,也经常雇佣‘代耕互助社’耕作。”
罗务禄顺手指出一样被石明楷遗漏忽略的事,心中却在暗想,以我们途中所见所闻来看,中土现在是国穷民困,虚弱空乏到了极点,不过欧罗巴各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法朗思’,虽然是欧罗巴的大国,而且还刚刚在战争中取得了欧罗巴霸权,国中却到处都是贫穷与饥饿的景象,它的国都葩蕊,这个二十万人口的城市中,臭水横流,垃圾遍地,瘟疫不绝,医药无方,又哪里象是欧罗巴霸主的国都?
罗务禄微微叹了口气,欧罗巴历次十字军东征,只是一次又一次消耗着罗马教廷的名望与威信罢了,而黑死病在欧罗巴的此起彼落,基督教会的茫然无措,也让教会的威望和信誉在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感到失望之后直接降到了谷底。到了现在,贫穷困苦得让人绝望的欧罗巴各国,人民对天主的信仰无疑也衰落到了极点,英吉利、法朗思等强国都与罗马基督教关系不睦,贵族以奢靡和纵欲嘲笑着基督,平民以麻木和诅咒质疑着教廷,迷途的羔羊们心无所寄,信仰缺失,只能选择崇拜金钱。与眼前充满着希望的西北相比,深陷于苦难中的欧罗巴还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在西北,在这里几乎没有信仰天主与基督的人,或者可以说满眼都是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在这里传教,真的会有效么?
罗务禄转念之间,还是将心底的疑虑深深的隐藏起来,侍奉基督的传教士不应该软弱,哪怕西北的统治者并不亲近天主与基督。
当来自西洋的传教士怀揣着传播天主福音的心思,一路向西,向着西北行都河中府进发的时候,还有同样一群向西进发的人们,也在关中原野上迤俪前行。
秋收秋种,这时正是农夫非常忙碌的季节。
中土北方旱地耕作,多是两年三熟轮作复种,如果春种豆(春播)、粟、高粱等,秋收后则播种冬小麦,等到次年五月收麦,又播种粟、豆(夏播),可有三季收获。
关中大部分灌区,在今年夏收之后收割了上年的冬播小麦、冬种油菜,就复种了荞麦、糜子、谷子、(麦后夏播)大豆、花生等作物,到这时候便是收获季。而轮作玉米、高粱的田地,也是差不多要在这时候收获,在秋收之后还要接茬儿播种下年轮作的冬小麦、冬油菜,而留着不播种冬小麦的地,也要育绿肥以蓄养地力,比如种上苜蓿,既可作草料,还可养地力。
秋收复秋种,正当忙碌时。
农夫扶犁扬鞭,呵牛耕田,耕牛奋力向前,也有的农夫正在深施厩肥作为‘垫底’(底肥),还有三三两两的儿童妇女,提篮随墒撒播种子,关中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类似的景象。
关中毕竟是秦国故地、两汉腹心,八百里秦川天府,尽管曾经衰败破落,尽管尚未完全恢复旧观,但历代以来官民修建水渠灌溉自有规模,重新疏浚恢复之后的生机活力,仍然不是什么人可以小觑得了的。
关中东部,有郑国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漕渠等渠系;关中西部有成国渠、灵轵渠、湋渠等渠系;黄河诸套也是水渠纵横,可以说现在的关中,虽然说不上丰年饶足,但也称得上比较安康,秋粮收成好坏就在地里,光天化日之下是瞒不了人的。
在关中原上如长蛇一般迤俪前行的逃荒饥民,无比羡慕的一看再看,一步三回头,恨不得这关中沃土,都是自己家的,那谷子,那糜子,那高粱,那已经成熟的果林,是何等的诱人呵
怀着西出潼关无故人的心思,很多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中原流民,被人哄骗着,被人裹挟着,被人逼迫着,被人招募着,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在饥荒不能果腹的压力下,都是这么一年接一年,一批接一批的向西迁徙,一路涌入潼关,他们的目标,除了向西,还是向西,饥饿与战乱,让自古安土重迁的中原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徙西域,不知梦魂何处是故乡。
惶恐的中原移民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在被一一安置下去之前,在被安顿妥当之前,是不会心安神定的,尽管有屯垦学校的连续指导、连续训练,尽管有在屯垦学校训练过的亲戚乡党,指挥着他们这些逃荒逃兵移民一路上的行止,并且西北宣称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分地授田之外,一切宿营、定居、筑垒、建堡、开垦、团结防卫、防病、耕种牧养、商贸等事皆有西北官府出面扶持帮助,然而对未来的不确定,仍然会让人心中惴惴,难以自安,哪怕是曾经饱读圣贤书的所谓读书人也不能免俗,忧虑是难免的。
“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队伍中儒衫破旧,曾经进学的童生老秀才,虽然是潦倒艰困,仍然有些‘穷且益坚’的气概,在前行跋涉的移民队伍中,也忘不了掉书袋,“关中能有如斯富足,吾民之幸也”
旁边有同样进学入廪的廪生接腔,“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千年前的关中,真是令人悠然神往,却不知我等被迁往西域,会分到何处?能分到什么样的地?”
七嘴八舌中,又有人又叹息曰:“北方连年大旱大蝗、鼠疫成灾,以至人户尽空;南方大水大涝,粮食绝收,饥民死亡十之五六,倒是西北景象,看上去还算丰饶少灾,民丰人阜。
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不知道,那些藩镇诸侯,都弄得无粮无口了,这时还争的什么?”
“也不是别人要争吧?只要到了那个位置,你不想争也得争一争,由不得你了。村夫愚妇都知道,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啦。”有人不同意了,“这天下藩镇蜂起,诸侯割据,总归是朝廷失德,气数已衰,方能出此乱世之象。哀哉吾国痛哉吾民”
正说的热闹,铜铃响丁当,蹄声从队尾而来,渐驰渐近,烟尘飞扬。
“好象是蒙古人”
“啊,是鞑子。”
“可能是‘义从民’吧?一般的鞑子,绝不敢这么大模大样的。西北律例,驰马驿道,要是不慎撞了人,坐监之外还要罚银、赔偿。赔不死他,我都倒过来姓。”
“不一定啊,归化蒙古人听说也放得很宽,待遇跟‘归义胡’差不多,一样可以从军、做官、放牧、经商、做工。”
中原移民虽然故老相传,都听过很多蒙古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故事,但是这会儿却是无惊无恐自顾走路,因为他们现在可是一个个精穷赤贫,身无长物,唯一的用处似乎只有去做粮食当两脚羊一途。那些传说中特别喜欢掳掠人口为奴的蒙古人,恐怕都不愿意抢劫他们这些死穷鬼,浪费粮食不划算就不说了,当作两脚羊豢养或者杀了腌成肉脯都嫌不肥,不但吃口不好,还特别费盐费火,这般儿没盐淡味,抢来作什么使?折本的买卖做不得也。
中原移民们,在队伍里七嘴八舌的说着不着四六的话儿,却是根本不怕碰上什么深入关中掳掠的鞑靼游骑。一者,西北的官爷都说了,塞外的鞑靼人都叫公爷给打怕了打残废了,现在都成了公爷的治下之民,一个个老实得紧呢,不敢撩事生非的;二者,除死无大难,他们这些人已经一无所有,就现在一天两顿吃的嚼谷汤饭,还是靠西北官府‘借’给他们的粮食,用西北官给‘粮串子’提票,从沿途的米行粮栈提取粮食,虽然官府不收他们分毫利息,但是人不死债不烂,还到玄孙辈,他们在官府手中‘借’的这些米粮也得还清了,所以说他们就不怕被人抢劫,该担心的应该是‘借’粮食给他们的西北官府才对,要是他们被抢劫了,这‘粮串子’提票损失得算到劫匪上。
烟尘卷起,铁蹄起落,六匹马和三个蒙古袍服的男子从移民队伍身边一掠而过,毫不停留。
这个时候,移民就看清楚了,这三个蒙古人可算是全副武装,弯刀、角弓、斧头、箭囊、标枪、套马索、长矛,还有柳条盾,他们的蒙古袍子里还露出皮甲的边缘。
有人看不惯了:“这是什么人啦?任由夷狄之辈带刀带枪,官府也不查禁查禁?”
“可能是赏金客,也可能是标师、标客吧,在官府报备审核之后,他们这是可以携有兵器的。”有人猜测道。
一般人当然不太了解,西北在赏金会馆、标行的规例中,专门制定了一些吸引赤贫而蛮勇的蒙古牧人,踊跃投身赏金客、标师行业,从此后放弃游牧的‘隐匿’条款,象‘义从民’、‘归化蒙人’(移居于汉人聚居地,但又还够不上‘义从’资格的蒙古炫)携带兵器,巡捕营、锄奸营等衙署就暗中有意的放宽、简化了报备审核条件。加上在西北的其他施政举措中,也考虑到了蒙古牧人的情况,专门量身制订了一些吸引蒙古人从塞外草原离开,迁徙到其他地方去安居放牧的条款,这些条款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缓慢而深刻的改变着塞外草原的人口对比。另外,西北还有不少扶助中土商民去塞北经营牧场的奖励举措,对以畜牧商社形式经营牧场并且定居常驻的畜牧商行,给予减免抽分及徭役、对其畜产优先采办、官方低息放贷等扶助,而且也不限定商社成员都必须是汉人,他族亦可。从塞外草原引出蒙古人,同时又以其他措施鼓励输入各族人口,这一出一入,可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反正塞外草原上的蒙古式封建诸侯,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游牧部族慢慢瓦解乃是必然的,甚至许多蒙古台吉、蒙古那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