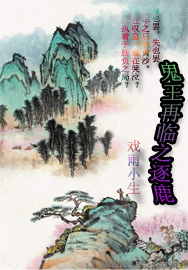惊雷逐鹿-第5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李虎在教中的资历、功劳、势力、人脉、传承、修为也是没人敢给他脸色看的重要原因。李虎本身修的是‘弥勒转生诀’,但也得了鲜少外传的李氏‘六如诀’传承,而且皋兰派心法修为也颇为深厚,他一人而兼有三家之长,且又得到龙虎大天师李大礼这等大宗师的指点,三家融会贯通之后,修为在新弥勒教中也是少有敌手,加上他在教中的资历、功劳、势力、人脉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雄厚,谁愿平白无故扫了李虎的面皮,给他脸色看呢?在座的几位,都是胸有城府的精细人,又不是那等没眼色的人,‘一家人’自然和颜悦色,再有什么不快也得藏着。
人齐上菜,自家的产业倒也快当,碗儿盘儿须臾就摆放齐整。
各色菜肴品类不须一一细说,其中最可称道者,便是‘脆鳝’,物美价廉。鱼一端上来,饭庄的堂倌即用草纸合起来双手一压,客人把来下酒,迸焦酥脆,咸淡适口,极是好吃。这菜本来是帝国江南淮扬一带吃早茶,下酒拌干丝两相宜的佐餐之物,‘江南春’在缅国做生意,却要顾着汉人客商的口味,倒与帝国差不多少。
另有一味菜品,却是醉蟹。缅国清溪河所产本地大蟹,肥腴鲜嫩不亚于中土江南的阳澄湖名产。把那大蟹一雄一雌草绳扎紧,上秤一称,正正十六两的一斤‘对蟹’,尤为名贵。本地汉人酱园拿酒做醉蟹,一坛两只,膏足黄满,浓淡适度,下酒自是妙极。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干李姓人氏直喝到酒酣耳热,方才唤了饭庄堂倌另上茶食,慢慢聊些闲话,说些教中事务。
话说弥勒教在缅国王族陷于混乱之际,已经迅速行动,着手部署,要趁着缅地动荡的时节,将弥勒教香军改头换面,以护法、标客、庄丁、家人、伙计等等身份掩护,重新编组起来,一心要在西北幕府的南边方略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他们这些主事之人已经将缅国视作新弥勒教立教传道的根基之一,绝不允许肥肉旁落。
李越、李虎、李碧瑶这些新弥勒教的核心骨干,对缅国当下的乱局,也各自有些揣测。莽应昌的被刺、他隆的突然薨逝,为新弥勒教的教务扩展带来了重大的契机,他们也敏锐的抓住了缅国内乱的机会,但是对整个局面的未来趋向把握并不清晰。他们也是想借着聚会,好生合计合计,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群策群力的道理谁都懂不是?
其实在座的这些李姓人氏,各自也有些私心小算盘,都想争取立下一份大功,以便在/‘文/缅国为/炫‘/自己谋取/‘书/到一处可/网‘/以世袭且实领的采邑封地和相应的世袭爵秩,攒下富贵传诸子孙的心思大概是谁都会有的心思。从云南经略府、云南镇守府中传出的若干风声,不由他们不动心——云南经略府帐下的东行营、西行营,其提督将帅基本上都是前弥勒教出身,想让他们稍稍透点口风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其实说起来,除了西北幕府在甘霖六年以前敕封给臣僚部属的那些采邑和食邑以外,在甘霖六年以后分封的采邑、食邑,只要是西北方面以官书契、委任状、敕封纸、(采邑)食邑文牍等官给文牒正式承认的实领(半实领)世袭封地,其实多半都分布在官方力量鞭长莫及的蛮荒异域,比如北疆的岭北蛮荒,西域的苦寒荒僻寥无人烟之地,而且这种实领(半实领)世袭封地的田亩通常也都不会太大。但凡官方可以看顾过来的地界,大多数的敕封领地,现在都已经是那种不能实领的世袭食邑或不世食邑,即所谓‘名义’食邑。名义食邑所谓的百户千户万户,虽然说不上是‘虚封’,但受封者也就是食邑名义上的领主。这样的领主对其食邑领地上的居民,通常并无多少实际上的领主权和辖治权,至于食邑领主私人所有的家仆奴隶则又另当别论,食邑领主对食邑领地唯一的权力就是监督其该得的食邑租税不被任何衙署以及任何个人贪污截取。当然例外的情形也有,某些世袭或者不世袭的食邑领主,也可能对食邑上的居民合法拥有不完全的领主权和辖治权,但即便是这种不完全的权力也必然受到官府衙署的限制、监督、约束以及审察和监视,而且根据敕封之际君臣签署的采邑(食邑)契约之规定,西北幕府还有权依据双方订立的采邑(食邑)契约,在某些情形之下永久剥夺食邑领主这点并不完全的权力,但其食邑一般并不受此影响。当然,西北治下所有的采邑、食邑,不管是实领采邑还是‘名义’食邑或‘虚封’食邑,也不管是世袭还是不世袭,都必须每年向西北幕府缴纳一定贡赋,这是西北治下特有赋税,有着浓厚的‘复古’意味,帝国境内可是鲜少见的。
尽管现实如此残酷,想要以大功换取实领的世袭采邑并不容易,还是有许多人梦想着有裂土封疆的这么一天,哪怕是降格以求的食邑也好过普通的田舍翁;尽管在西北做纯粹的地主比获取采邑、食邑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但采邑、食邑所拥有的那份荣耀以及减税、免役等若干连带特权却不是区区的地主就可以比拟的,也就难怪世人羡慕,而新弥勒教的这些李姓要员也要为之动心了。
在座的一干‘兄弟’‘姐妹’,虽然都姓李,各自的心思却未必都一样了。
“他隆不死,缅国内乱难起。”
&炫&带着阴森杀气的声音,与龙沙清秀的相貌毫不相称。
&书&军帐当中,油灯摇曳,昏黄一片。
&网&云南的冬天,虽然气候还算温暖,但山中还是有些冷,厚厚的毛毡并不能挡住所有的寒冷。
这时距离东吁王他隆的突然薨逝已经有一月有余,缅国乱局愈演愈烈,形势躁动不安。
为了以防不测,云南经略府合议定计,调兵遣将备御南边,除了王金刚奴、孟化鲸领率的东行营,韩太湖、唐云峰、邵福领率的西行营陆续向南开拔以外,明石羽麾下的苗瑶军团,陈好麾下的山地追剿军团,也从曲靖府南下,进驻车里军民府、景东府镇沅府、威远州、普洱城等处水陆关隘要地。
身在苗瑶军团大营驻地,龙沙这位巫门三十六脉中鬼灵一脉苗疆野麻岭出身的年青一代高手,就这样不管不顾的将他在缅国做下的惊人勾当说了出来,直白无隐。
野麻岭的大师兄麻无鬼不动声色,打量着相貌清秀温文的龙沙,哼了一声:
“龙沙,这是师尊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龙沙闻言反问:“我自己的意思,怎么啦?”
麻无鬼合上手边的公牍,正色说道:“龙沙,你可知道,他隆一死,缅国立时争权内乱。如今缅国他隆所生诸子,纷纷遣使西北,翼求西北援应,其中干系非小,你怎可妄自揣摩军国大事?莽应昌被刺,不会也与你有关吧?”
龙沙笑道,“大师兄,你也太看得起我龙沙了!莽应昌被刺的事情,与我可没有一点相干。那东吁王也是命该如此,谁让他当年斩草不除根,留下后患来着?我不过是顺水推舟,帮了朋友一把,教了他一个下毒的法子而已。而且,我这朋友报了血海深仇,觉得生无可恋,也都自行了断了。”
“哦?”麻无鬼依然平和沉静,追问道:“什么血海深仇?你的朋友又是怎样自行了断?”
“当年东吁王他隆东征南讨,做下的血腥事情可是不少。我在缅国认识的这个朋友,便是他隆的仇家,却是不知怎么的被他混进了他隆的王宫,还步步高升,想必暗中也有一些势力并不想让他隆好过。”龙沙显然还不糊涂,知道自己认识的这所谓朋友,也是别有用心之辈,面对麻无鬼的追问,倒是实话实说,“……他想利用我,我就让他利用一下又如何?他隆一死,无论谁想在缅国这潭浑水中摸鱼都行,我们巫门诸脉也可以趁势南进,在缅国分上一杯羹。新弥勒教仗着他们经略府的人脉势力在缅国肆无忌惮的扩展教务,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至于我这位朋友的自行了断,哼哼,乃是因为被我擒拿之后,熬刑不过才自尽而死的。”
“你知道什么?”麻无鬼站起身来,在帐中缓缓踱步,“这里面牵涉太多,搞不好就会让你,让我们巫门诸脉成为别人的替死鬼。你以为平虏侯的谍探都是吃素的?还是以为别人都是傻瓜?”
龙沙猛地抬头,阴冷地逼视麻无鬼的眼睛。
麻无鬼压低声音,说道:“龙沙,你刚才还笑东吁王他隆斩草未除根,可是你看看你,犯了与他隆同样的错。既然你那朋友没了,那他背后的那些人知道不知道你的存在?如果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如果他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经略府或者平虏侯知道,或者透露给缅国他隆家族的人,你可知道你的麻烦有多大?死了他隆一个不要紧,但是缅国这一乱,云南驻军和徭役民夫,几十万人都要跟着动起来,花费钱粮不说,原来的部署全都没用了,都得跟着变。你不觉得,这等于是你一个人绑架了整个云南经略府和云南镇守府,还有云南执政府?如果西北幕府深入追究此事,你将如何自处?我巫门诸脉又将如何自处?我野麻岭又将如何自处?你想过后果么?”
龙沙呼地站起来,喝道:“大师兄,我龙沙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了不起?”
“龙沙,你以为我不能杀你吗?”麻无鬼冷笑一声,又道:“说得也对,这确实没什么了不起。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杀,杀人就要杀彻底。你二师兄龙图火,前些日刚巧带人去了缅国的南边,我会飞鸽传书给他,让他先准备好人手。龙沙,你即刻动身回缅国,到了那边,听你二师兄的指挥,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做干净了,一定要把那些人彻底灭口。就这样吧。”
龙沙按捺住心里的烦躁,拱手一礼,转身出帐,到了军帐门口又突然回身:“大师兄,这回我一定杀彻底!一定!”
江岸边的驿道上,长长的骡马车队逶迤向前。
车轮转动,咯吱声尖利刺耳,显然骡车满载吃重!
当先开道一面土黄大旗,上绣“广源标行”几个大字,分外显眼。
大旗后是四五十号骑士,一律悬刀挂剑,携有硬弓长箭,骑着云南滇马,翻山越岭,穿越丛林……
骡马车队从岬口出来,前面庄堡巍然在望。
远远看去,但见那处庄堡飞檐重叠,屋宇连绵,气势不凡,山风吹拂带来檐下铁马叮咚之声。
骡马车队就在庄堡前停下,激起一片烟尘。
一个戴着汉阳巾子,穿一件怀素褶子的壮汉翻身下了马,身形看上去粗壮结实,步态勇武,宛如一头凶恶猛虎行进在丛莽之间,睥睨自雄。
如果有帝国江南黑道上的私枭在这,一定能认出这个壮汉是谁。话说当年‘黑角岭’的二当家‘恶虎’燕小弋,黑道上也是一号人物,不合看守不力,在一场恶战中丢了黑角岭的公库银两,自己觉得没脸见人,只得净身出户亡命江湖,谁知竟是辗转流落到了缅国地面。(见于第五十六卷 第六章 月下刀光寒)
‘恶虎’燕小弋辗转来到在这异国他乡,倒是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只是换了营生,不再**原来走私的老本行。他先是做起了打家劫舍的没本钱买卖,筹到一大笔本钱便洗手做了良善之民,与人合伙买下了缅国西北丛林中的一处翡翠矿场,一处铜矿场,后来又在云南买下一处银矿、一处锡矿,慢慢的买田买地,置办农庄、种植园,开起了客栈、货栈、作坊、店铺、炉房、当铺、印局,拥有了自己的标行、标船,在云南、缅国之间来回贩运。如今的恶虎,怎么看都象是帝国的乡绅员外,而不是曾经的江湖私枭。
缅国东吁王廷迫于西北幕府陈兵云南的强大威慑,不得不与西北方面通商通驿、互派使节以彰友好之谊,并允许中土商贾在缅国自由往来迁徙,允许中土商贾在缅国买田买地建立商站货栈开办作坊商号(当然商税之类是必须缴纳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燕小弋才得以在缅国顺利立足。
燕小弋有感于自身遭遇,所以他将自己的庄堡‘燕家堡’,完全建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作为其根基之地。
暮色四合,‘燕家堡’华灯初上。
庭院小巧,花木葳蕤,精舍轩敞,窗明几净。
天竺奴已经在在这院落里头,生活了两年。她也不觉得日子太长,两年宛如一瞬。
作为堡主燕小弋房中的女人之一或者说‘小妾’之一,她原来的姓氏当然不是‘天竺奴’,只不过她信佛,又来自古天竺印度,别人叫她‘天竺奴’,那就‘天竺奴’罢,反正她年青娇媚,又能生养,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只要燕小弋还在,她在燕家堡的地位就是稳固的。
燕小弋对天竺奴也不差,供养无缺,什么珍馐美味、金玉绫罗,从不亏欠于她。
对镜卸妆,天竺奴将一只缨络金项圈撂在妆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那是赤金打出的八宝螭龙,蜿蜒相对衔住一颗大珠。
天竺奴不由想起燕小弋上次买给她的珍珠头面,这会儿也不知搁在哪个柜子箱子了?燕小弋待她很慷慨,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妆奁,反正就是女人难以抗拒的晶晶亮、闪闪光的那类东西。
天竺奴撂下金项圈,拣起一对看起来简朴的坠子戴在耳上。
猫儿眼,碧绿晶莹,幻变着奇丽的光色。
燕小弋来到了她的身后,天竺奴反臂搂住身后男人的脖颈,闻着她熟悉的味道……
看着铜镜中美丽的俏脸,十八岁的美丽,燕小弋却是有些担忧——当然不是担心天竺奴红杏出墙,也不是担心今儿晚上他能不能金枪不倒。燕小弋对自己的睿智机敏很自信,而他也从未有过房事不举的尴尬,他现在正处在男人体力的巅峰岁月,精力充沛之极,夜御十女也不是太夸张的说法。
他现在担忧的是当前缅国的乱局,他在担忧这种紧张局面会不会继续蔓延恶化,他还在考虑是不是暂时撤回云南以避可能的兵祸。不管燕小弋是如何的自信,也不管燕小弋天生神力是如何的勇猛,也不管燕小弋的武技是如何的高明,他终究只是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的争战攻伐,他也无力与抗,只能远遁逃避。
燕小弋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兵祸的血腥味道,但是他有点迟疑不决——
毕竟他在缅国赤手空拳打天下,白手起家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