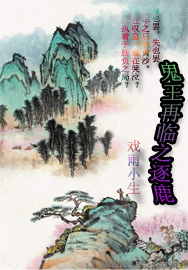惊雷逐鹿-第50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至于一应阵亡及突围将士,各计功罪爵秩,死后哀荣,抚恤荫庇不提。
青山处处埋忠骨,马革何须裹尸还?
遵照雷天星生前所留地遗言,死后葬于阿尔泰金山南麓,萧寒在迁往哈密的‘杏林大医院’继续养伤之前,到雷天星地坟茔前祭拜,并将雷天星的神位牌迁出,以便他日伤好东归,奉安于长安的“忠烈祠庙”之内。
回首西望,山岭苍茫。
萧寒坐在几个印度仆从抬的肩舆上,被家丁扈从着,慢慢儿下山去。
“寒日征西将,萧萧万马从。 吹笳覆楼雪,视满旗风。 枪垒依沙迥,辕门压寨雄。 燕然如可勒,万里愿从公。 ”
山风将萧寒随口吟咏的五律,送往苍翠山林的深处。
低声吟咏的萧寒,很有些英雄迟暮地失落,西征大营对七河地区的报复性扫荡掠袭已经开始了,但千军万马中已经没有他萧寒的位置,以后也不会有了——他身上的伤,不但伤到了手筋,还被伤及肺腑,现已是做不了重体力活,横枪跃马征战沙场自然就更不可能了。
不能万里觅封侯,只能归为田舍翁,胸中万字平戎策,都且换作东邻种树书。
河谷中,马队迤俪前进,小驰走马,蹄声得得。
坐骑都是高大雄骏的西域战马,与塞北蒙古矮壮而耐力强悍的蒙古马相比,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坐骑上的骁勇骑兵,一个个目光冷漠,身上一股子血腥杀伐之气,显得极是剽悍,是真正经过血战恶战磨砺地战士。
骑兵手中的刀枪,看上去打造精良,只是刃口上有着这样那样的豁口或者卷刃,一派烽烟战场的气息,想来是刚刚经历过激烈的杀戮战斗。
山坡上出现了另一拨骑兵,他们的认军旗中同样飘扬着黄金龙旗和雷字大。 这显然表明,他们也是西北幕府地平虏军麾下骑兵——不同地是,他们的坐骑有矮壮的蒙古马。 也有高骏的青海骢,而狼头则表明,他们是青海蒙古部的游牧骑兵。
两队骑兵互相之间似有默契,向着相同的方向进军,途中并不停留。
马队西行百余里,天色将黄昏。
两队精悍骑兵,一出现在地平线上。 就开始策马以快步接近目标,逼近到数百步开始驰步冲锋。 目标直指一个游牧部落的宿营地。
骑兵冲锋,雷霆万钧,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以东流到海不复回之势直冲而去,铁蹄踏破苍茫,大地发出震天地轰鸣,声势惊人。 慑人魂魄。
冲锋的马队距离部落营地只有不到三百步了,一转眼间,骑兵马队就已经冲到眼前,速度如狂风闪电,洪流奔泻。
马蹄声声,轰隆如同闷雷,越来越大。
部落地男人们握紧手中地刀枪,手心额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冒汗。 他们甚至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战马背上,那些骑兵眼中,嗜血冷酷地光芒。
箭雨倾泄,飞蝗翔集。
一马当先的骑兵马队绕营而进,利箭不断抛射到空中,划出一条弧线。 呼啸着从天而降。
部落营地中,不断有人在骑弓手的箭矢急速攒射下丧命。
第二拨的骑兵,紧随跟进,飞驰中纷纷射出箭矢。
箭雨密集,部落中剩下地男人,斗志很快消磨崩溃,开始有人惨号着四散奔逃,防线立刻乱作一团。
第三拨的骑兵不再是轻骑弓手,而是浑身披甲勇力过人的陷阵重骑,这时侯趁着部落营地的纷乱。 冲进了部落营地。 展开屠杀。
陷阵重骑也只是相对于各类轻骑兵而言,他们内着锁子甲。 外披鱼鳞札甲,围脖、战靴都内衬了钢丝网甲,陷阵冲锋时都使用长大粗重的兵器,如马槊、铁枪、狼牙棒、铜锤、劈山刀,通常一人配有多匹战马。 平虏军的精锐重骑,一人通常有四五匹战马轮流换乘,同时还各自带着弓箭、标枪、投斧、套索、、乾坤圈、飞爪、火铳、小号佛朗机等兵器军械,他们的马匹都是精挑细选的战马,不但负重力大,耐久战驱驰,而且短程冲刺地爆发力也相对较好,因此主要就是在前锋轻骑以多拨密集箭雨打乱敌方防守阵形之后,适时发起陷阵冲锋,趁热打铁撕开敌方的密集防线,突破敌方部署的防御阵形,搅乱敌方阵脚,使己方军队得以跟进,迅速扩大战果,从而达到最终分割击破敌军,战而胜之的目的。
重骑兵的武器长大沉重,用来冲撞敌阵最合适不过。
恐怖地标枪、投斧,被冲锋重骑借助马匹冲锋之势,掷入部落营地当中,风雷狂啸,急如冰雹,部落中相继有人惨号着倒地不起。
冲锋重骑随后趁势冲击营地,挥刀舞枪,迅猛进击,鲜血飞溅之间,惨号与吼叫声此起彼伏。
这完完全全是一面倒的大屠杀,如宰猪羊一般,胜券已然在握。
在平虏军西征大营主力奔袭乌兹别柯汗廷,寻敌决战的同时,西北幕府辖下各路偏师也在七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清剿扫荡、长途掠袭,比如对这个边境部落的奔袭,只是大规模扫荡掠袭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幕罢了。
对七河地区的清剿、掠袭战事,其中又以伯颜察尔家族名下的‘狮鹫十旗’军团、顾始汗名下的青海蒙古部骑兵的扫荡袭击最为犀利、血腥和残暴。
‘狮鹫十旗’军团在叶尔羌战事基本结束之后,即将驻防任务交割予西北地步兵军团,全数调往葱岭以西地区征战,这一次便是与青海蒙古部联手对七河地区地边境部落进行扫荡掠袭,不管是萨非伊朗的边境部落,还是乌兹别柯汗国地边境部落,凡是不望风请降者,一律予以扫荡灭杀。
而青海蒙古部中的瓦剌骑兵,对扫荡乌兹别柯部落最是下力气,毕竟他们一直梦想着重返被乌兹别柯汗国占据的草原故乡。
大大小小的矿场主、牧场主、农庄主、工场主、作坊主们,从内地出嘉峪关,万里迢迢跑到西域开牧场、办农庄、建工场、设商号,都是为了发财,但一直苦恼于奴隶做工人手的不足——大量的叶尔羌精壮人口被西北幕府编遣为奴隶军团,虽然也时不时向外发卖一些桀骜不驯的奴隶,但这并不能让各家财东们满足和满意。 他们需要的是温驯而不那么桀骜难驯的家伙,比如奴隶商人从印度贩卖来的奴仆——现在战端一启,他们可是乐坏了,这下做苦工的奴隶都有着落了。
矿场主、牧场主、农庄主、工场、作坊、商社、商团纷纷向赏金会馆开出一张又一张的捕奴大单,甚至直接向奴隶商人开出了定金若干,抢先订下奴隶若干;甚至还有胆子大,自忖武力不弱的东家,自己组织牧工、农工、护院,追随在军队后面,就地收买军人们俘虏的奴隶或者搜捕部落中逃出来的零星壮丁。
为了丰厚的赏金,除了奴隶商人的捕奴队到处出没之外,许多‘标行’也耐不住真金白银的诱惑纷纷而动,甚至几家标行联手起来,以‘随军清剿,从征不臣’为名,趁着战端开启,形势纷乱之机,大肆掳掠部落奴隶;那些平常喜欢跑单帮的赏金客,这时也纷纷临时联手,成群结队,四下抢掠奴隶和财物。
整个西域,一时血腥纷乱,人命贱如鸡狗,对于当位者而言,在兵荒马乱的大势下,有很多lun理道德根本顾不上理会,一切苦痛哀伤和血泪屈辱都在胜利与荣耀的名义下被人忽略、忽视,乃至淡忘,直至不复存在!
在时代的浩荡洪流之下,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许许多多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就象那木炭一样,在时代的洪炉中燃烧,爆发出灿烂耀眼的光和热,但是那光和热所照亮的,所温暖的,却多半不是小人物自己。
天下风云多变幻,小人物的自身,或迟或早都会成为时代的灰烬,最后被人彻底的遗忘!
谁还会记得一粒尘埃呢?小人物的呐喊,小人物的愿望,总是那么微不足道!
能够被人在青史之上记上一笔两笔的,多半不会是芸芸众生当中的某一位平常百姓。
第四章 弱肉强食
雄师出西域,铁骑破楼兰。
铁与血,剑与火,生与死的搏杀较量,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履胡之肠涉胡血,只为汉道昌!
西征大军在西域东征西讨,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年头。
甘霖四年的春天,西北的风沙如期而至,但已经没有了往年肆虐的凶威。
现如今的西北,平虏侯赋予堪舆署的权力相当之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 比如堪舆署立碑划定布告四方的风水龙脉、禁伐山林、禁牧草场、封育山林、狩猎区、禁垦的土地、禁挖沙的河段、禁起房的地方等等风水禁区,那是绝对不许任何人触碰的禁律。 在堪舆署划定的禁区内垦牧砍伐,如果被人检举或者被官府衙门查获,倾家荡产、充军劳役是唯一下场。
司马翰当年上呈雷瑾的〈堪舆策论〉,数年以来依托于专责官署‘堪舆署’的设立而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非但如此,平虏侯雷瑾还认为,“无文难以行远”,所以在命令堪舆署设立“堪舆学院”传道授业以及著书立说编次颁行之外,又令堪舆署设立报房,刊行《阴阳师》和《堪舆地理》两份报纸,将风水形势宗的‘形法’、风水理气宗的‘理法’,一概不分派别,细加阐发,以达到发扬光大、广传周知的目的。 雷瑾还专门批示,要求西北各学院、学园、学宫、书院研修探讨堪舆风水方面的学术时,必须务去虚妄、切求实际。 不得故作神秘,应使士庶黎民明白晓识其中道理,皆得教化,俾使大众在营造建筑、生活日用等事上,都可以遵循堪舆风水之道而自为之、自用之,臻于我无为而民自化地境地。 堪舆署提领大使司马翰亦为此专门移文交涉,与通政司和内务安全署会商议事。 从堪舆署派出专人在通政司‘巡演局’挂名,与通政司、内务安全署直辖的说书弹唱优伶艺人们结伴巡游于西北城乡山野。 专事传播堪舆风水形势之学。 同时,司马翰又上书请得雷瑾的允准,以“无规矩不成方圆”为由,着令堪舆署官吏在水利、河渠、堤坝、河工、驿道、屯垦、畜牧、山林、狩猎、农牧用水等多方面,依据堪舆风水形势之学,制订出相关各项律例法令,报送审理院核准定案后。 由雷瑾批准颁行于西北幕府治下各府州县,以为政务之规范。
在堪舆署、水利署、农牧工商署等衙署通力合作的努力下,西北河陇边塞的风沙一点点见少,而曾经破败壅塞的水利河渠则一天天修葺完备起来,每年旱灾、蝗灾、风沙造成的粮食、牲畜损失因此降低了一大截,关中、汉中、河西、青海每年地粮食收获虽然还算不上什么丰收,但比之当年钦差税监‘梁剥皮’把持陕西政务人事之时,已有了极大改观。 人丁六畜逐渐兴旺,再加上四川云贵和哈密、土鲁番、亦力军民执政府所辖地域的粮食、畜产,西北府库逐渐充盈,连年征伐地军资也能勉力筹措,这等成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堪舆署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是绝然不能忽视的。
虽然堪舆署、水利署数年间治水治山的成效很大,甘霖四年这个春天的风沙也远比往年少而且弱,但包括雷瑾在内,西北士庶仍然习惯性的减少了出行在外地次数,毕竟谁也不愿迎风吃砂子,春天风沙大起的时候,呆在家里是最稳妥的。
在平虏堡“幽篁里”,栖云凝清、倪法胜两人恪尽职守,扼守在攻守路线上的前后关节点,遥遥望着伫立于沙盘之前默然静思的雷瑾。 脸上带着几分忧虑的神色。 却不敢过去打扰他的静思。
最近几年,西北府库充盈。 甲兵强盛,实力见涨,信心自满,上上下下都不免有些浮躁自满、自高自大的风习,平虏军早几年在七河之役中蒙羞之事,现在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此情形下,西北地一部分幕府官员、青翰词臣、儒林士绅、地方豪强们屡次想要上表‘称颂’盛世太平,甚至有人劝进称王。 如果不是雷瑾再三强力压着这股势头,这部分僚属臣民早就按捺不住,不知道会掀起什么风浪,搞出什么事情来——虽然对于独霸西北的平虏侯雷瑾来说,现在若是头脑一发热,应了这部分人之请,在西北边陲一隅僭号称王,自诩什么太平盛世,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倒也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 名实相符的成为西陲之王,这事说容易也容易,但是俗话说的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地情形下,为了一个虚名勉强行事,势必成为天下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选择。 以长史蒙逊的话来说,就是‘都什么人啦?刚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
对此,雷瑾还是比较清醒的,这部分上言表章一概留中不发,并私底下对一干心腹近臣‘吹风’,表明心迹:“京师帝室尚存,幼主正位,天下人心犹奉皇甫氏为正统;幼帝既非昏聩失德而致天怒人怨之辈,为人臣下者悖逆叛国僭号称王,是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天下人必将鸣鼓而讨之!劝进诸生,是何心肠?欲误本侯么?况而今天下,已是群雄并起之局,兵戈四起,沧海横流,何来太平可言,又何有盛世可言?如此时局,小康之世尚是奢望,惶论其他哉?此等事体,诸君诸僚切勿再提,宜各守本分职司,谨慎做事为要。 ”
此言一出,雷瑾才算耳根一清,得了些清闲。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方诸侯。 都不是那么好做的,都要付出相应地代价和牺牲。
栖云凝清等却也知道,雷瑾虽是贵为主上,但以一人之力与众多部下僚属的意愿较劲,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逆势而行,又岂是易为?而对僚属地劝进之声,悍然压制或者轻率顺应都非上策。 自古皆言堵不如疏,但真个事到临头。 其中堵与疏地火候又哪里有那么容易把握呢?堵或者疏,都是令人费心伤神,需要手腕和权术摆平的事情。
在雷瑾面前,是一个庞大地沙盘,而在前方地粉壁上还挂着一张大地图。
在粉壁与沙盘之间,摆放着由工匠精心制作的大号天体仪、地球仪各一座,这是在西洋传教士指点下。 详加考证才制作出来地东西,比起几十年前西洋传教士利马窦第一次送给帝国官员的天体仪、地球仪要精致得多。
伫立于沙盘之前的雷瑾,其实并没有象栖云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