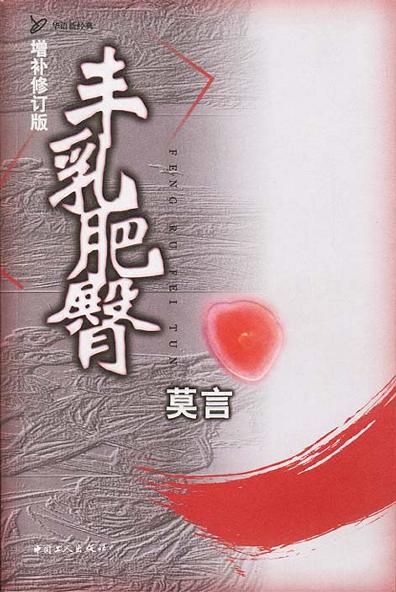莫言丰乳肥臀 重见天日-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幸担阂焖廊嘶瓜纭K行胺ㄗ樱苋盟廊诵凶摺8呙芏毕缛丝退浪纾颓胨チ旎乩础M獾厝擞兴涝诟呙芏毕绲模睬胨突厝ァR桓瞿苋盟廊斯怨孕凶撸焦酵蛩娜耍烁也痪次罚克砩嫌涝渡⒉甲乓恢止殴值钠叮钚酌偷墓芳怂惨芽裢奈舶图性谕燃洌伊锪锏靥优堋K诠迅竟暗陌宓噬希斐隽硕种浮9迅居胨蚴质疲芸炫靼姿粤铰迨觯皇浅粤礁龌蚴嵌觥9迅敬颐Φ匚急赴樱蛭飧龃蠖亲邮晨偷牡嚼矗牧成匣婪⒘斯獠剩员叩奶鞫劬锓懦隽寺坦狻N移笈巫潘强冢刀室材岩郧丝堑淖臁! ≌盘齑途簿驳刈牛劬Χ⒖垂迅静僮鳌K乃制骄驳厮吃谙ヒ嫔希镄吕匆桓谏牟即2即镒白攀裁矗膊恢馈I钋锢锼苛艘黄鸫蠡疃岩桓隹退涝诟呙芏毕绨鸫宓姆仿羝嘶夷昊墓囟倘诉夯厝ァ9囟倘说亩痈噶思矍袅说刂罚阆韧坊厝ィ急赣印4艘宦贩皆搅耄蠹叶脊烂耪盘齑突夭焕戳恕5撬乩戳耍囱痈崭栈乩础D呛诓即镒暗氖乔桑克诺抛乓凰评貌豢暗穆槎菪冻隽怂南裥〉毓弦谎蚀笾渍偷慕胖海褂兴南衽9展悄敲创蟮孽坠亟凇! ☆烦娴拿妹眯毖刍ūё乓豢醚┌椎拇蟀撞耍犹Ф芬徊嗦饭K欠缜橥蛑值暮谘劬π鳖┳盼摇K孔〈蟀撞说氖侄车猛ê臁K饭怨迅镜墓笆保迅镜氖滞蝗痪缌业夭镀鹄础K鞘浅鹑讼嗉滞庋酆臁5庋纳狈蛑鹨参茨苋谜怨迅疚ケ常把┘辈凰祷暗钠踉肌5铱吹剿慌鹕辗辛说难涸诩铀傺贰7吲晃笞錾猓饩褪钦怨迅镜某ごΑK岩宦绕谔诘陌硬揭桓霭咨拇蟠膳汤铮说秸盘齑兔媲啊U盘齑蜕斐鍪帧U怨迅居行┟H弧5砩暇兔靼住K糜湍宓陌驼婆淖哦钔罚硎径宰约菏杪┑那丛稹K印龉拮永铮×肆酵贩蚀蟮淖掀に猓旁谡盘齑褪掷铮⒂靡恢恍『谕耄⒘艘煌胫ヂ槔苯酚停鑫乇鸬姆钕祝旁谡盘齑兔媲啊B粝哪腥嗣遣宦乜纯此们嗌哪抗馀雷潘徒嵴盘齑偷奶取U盘齑托陌怖淼寐跛估淼匕糯笏猓却虐拥睦淙础K托牡匕寻拙坏乃獍甓凑沾笮〈涡颍帕性诜棺郎希诔梢桓龅チ凶荻印K共皇钡氐髡沉桨甏笮∠喾碌乃獍甑奈恢茫恢卑阉堑髡骄×亢侠淼某潭取:罄矗蔽页俗奶Ф纷桨撞耸猩鲜保以对兜乜吹剑嫒苏盘齑涂汲园恿恕K园拥乃俣瓤斓镁耍肫渌凳浅裕蝗缢邓谕桓龃罂谔匙永镒疤睢! ∥已彩印把┘钡娜挝裢瓿闪恕N奚睦侄影盐乙嫉剿啊M跏闲值苈湎绿Ф罚盐壹艹隼础N腋械剿人崧椋盘鄣貌桓艺吹亍LФ防镉惺杆菪褂幸恍┌乖嗟闹狡保庑┓钕赘把┕印钡那疲脊槲宜校俏野缪荨把┕印钡某昀汀! ∠衷诨叵肫鹄矗把┘逼涫凳桥说慕谌眨┫癖蛔诱诟谴蟮兀么蟮刈倘螅杏┦巧嵌斓南笳鞲谴禾斓男畔ⅲ├戳耍畈拇禾炀涂缟狭丝ヂ肀汲哿恕! ∷掠幸患湫⌒〉木彩遥彩依锩还┓钊魏紊裣桑涫倒┓畹木褪鞘彝獾乃>彩依锷兆盼兜赖诺南呦恪O懵坝幸桓龃竽九瑁枥锸锹摹⒚晃廴镜陌籽E韬笥幸桓龇降剩馐恰把┕印钡淖弧N易先ィ砩暇拖肫鹆恕把┕印钡淖詈笠幌钭盍钗壹ざ闹霸鹆恕C爬系老破鹉堑腊丫彩矣胪獗唠实馗艨陌咨疵帕保呓础K靡豢榘壮褡樱勺×宋业牧场W裾账孪鹊闹龈溃抑涝诼男兄霸鸬氖焙虿荒芟瓶饪榘壮瘛N姨剑崾智峤抛叱鋈チ恕>彩夷谥挥嘞挛业暮粑⑿奶拖呦闳忌盏纳簦彝猓嗣遣妊┑纳粢惨荚嫉卮础! ∫桓銮崆蔚呐俗呓戳恕M腹成系陌壮瘢夷:乜吹剿纳碛俺ご蟆K砩嫌幸还扇忌罩碜椎奈兜馈U獠惶赡苁谴罄复宓呐耍锌赡苁巧沉鹤哟宓呐耍歉龃謇铮幸患抑谱雒⒆拥氖止ひ底鞣弧2还苁悄睦锢吹呐耍把┕印倍加Ω靡皇油省N伊⒓窗阉植宓矫媲暗难┡枥铮檬ソ嗟难┫慈ノ沂稚系奈刍唷H缓笪野咽志倨鹄矗吧烊ィ凑展婢兀切┢砬罄茨晟拥呐耍切┢砬竽趟ⅰu房健康的女人应该撩起衣襟,用她们的Ru房来迎合“雪公子”的双手。果然,两团温暖的、柔软的肉,触在了我冰凉的手里。我感到一阵眩晕,幸福的暖流通过我的双手,迅速传遍我全身。我听到面前的女人发出无法遏止的喘息声。那两只Ru房像热鸽子在我手里稍做停留便飞走了。 第一对Ru房还没摸够就飞走了,我有些失望,更充满希望,把手伸进雪里,让它们恢复干净和圣洁。我有些焦灼地等待着第二对Ru房。第二对Ru房迎上来了,这次可不能让你们轻易飞走。我用僵硬的手,一下子就抓住了它们。它们小巧玲珑,说软不软说硬也不硬,像刚出笼的小馒头,我看不到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很白,很光滑。它们的头儿很小,像两颗小蘑菇。我抓着它们,心里默念着最美好的祝愿。捏一下,祝你一胎生三个胖孩子。捏两下,祝你的奶水旺盛像喷泉。捏三下,祝你的奶汁味道甜美入甘露。她低声地呻吟着,猛地挣脱了。我帐然若失,情绪受到沉重打击。心里感到差愧难当。为了惩罚自己,我把双手深探地插到雪里,我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盆底,直到双手和半截胳膊麻木了,失去知觉了,我才把它们抽出来。“雪公子”举着纯洁的双手,为高密东北乡的女人祝福。我的情绪沮丧,两只晃晃荡荡的袋状Ru房碰到我的手。我摸了它们,它们像不驯服的母鸡一样咯咯地叫着,皮肤上起了一层细疙瘩。我用手指夹了一下那两只疲倦的大奶头,便缩回了手。这个女人嘴巴里呼出的铁锈味喷到我蒙着面纱的脸上。“雪公子”一视同仁,祝你实现愿望,想生儿子就生儿子,想生女儿就生女儿,想要多少奶汁,就有多少奶汁。你的Ru房可以永远健康,但想恢复青春,“雪公子”却无能为力。 第四对Ru房像性情暴烈的鹌鹑,羽毛黄褐,嘴巴坚硬。脖子粗短有力。它们坚硬的喙连连啄击着我的掌心。 第五对Ru房里,好像藏着两窝马蜂,我的手一摸上去,那里边就响起嗡嗡嘤嘤之声,因为马蜂的冲撞,Ru房的表面变得灼热滚烫,我的手麻酥酥的,把很多美好的祝愿献给它们。 那天我抚摸了大概有一百二十对Ru房,若干的关于Ru房的感觉和印象层层叠叠,像一本书,可以一页页翻阅。但这些清晰的印象最后都被一只独角兽给搅乱了。这家伙像一只犀牛,乱拱乱戳,在我的记忆库里搞了一次地震,也像一头野牛,冲进了菜园子。 当时,我伸出因为肿胀感觉变得迟钝的双手,完全是为了履行“雪公子”的职责而等待下一对。Ru房没来,我就听到了极为熟悉的哧哧的笑声。红脸膛、红嘴唇、黑豆眼……独|乳老金,这个年轻风流的女人的脸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左手摸到了她肥大的右|乳,右手却摸了个空,于是我确凿地知道独|乳老金来了。这个开香油铺的风流女寡妇险些在斗争会上被枪毙,后来,她嫁给了村里最穷的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叫花子个眼方金,变成了赤贫农的妻子。他丈夫一只眼,她一只|乳,真是天生的一对。老金其实不老,关于她的独特的Xing爱方式,在村里的男人口里流传,我似懂非懂地听到过多次。我左手握着她,她抬起左手,把我的右手也引导过去。我双手捧着她的格外发达的独|乳,感受着它沉甸甸的分量。她指挥着我的手摸遍了她Ru房的每一寸皮肤。它是一座孤独的山峰,横生在她右胸上。上半部是舒缓的山坡,下半部是略微下垂的半球体。它是我摸过的Ru房里温度最高的,像生痘的公鸡一样,灼热,嗤嗤地冒火星。它是那么滑溜,如果不是灼热它会更滑溜。在下垂的半球体的顶端,先是有一块倒扣酒盅状的突出,突出部的突出就是那微微上翘的|乳头了。它时而硬时而软,像一颗橡皮子弹,几滴凉凉的汁液粘在我的手上。我突然想起村里那个去遥远的南方贩卖过丝绸的小个子石宾在草鞋窨子里说过的话,他说老金是个浪得像木瓜,一动就流白水的女人。木瓜像老金的Ru房吗? 我至今末见过木瓜我凭感觉知道木瓜太丑陋又太魅人了。“雪公子”履行的神圣职责渐渐被金独|乳引入歧途。我的手像海绵,汲取着她独|乳上的温暖,而她仿佛也在我的抚摸下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她像小猪一样哼哼着,猛地把我的头揽到她的怀里,她的燃烧的Ru房烫着我的脸。我听到她低声喃喃着:“亲儿……我的亲儿啊……” “雪集”的规矩被破坏了。 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 在门老道门前的空地上,停着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从车上跳下四个身穿黄军装、胸脯上佩戴白布标记的公安兵。他们动作敏捷,像豹子一样蹿进门老道的房子。几分钟后,手腕上戴着银色手铐的门老道被推推搡搡地押出来。他悲哀地看看我,一句话也没说,顺从地钻进了吉普车。 三个月后,反动道会门头子、暗藏的、经常站在高坡上打信号弹的特务门圣武被枪毙在县城断魂桥边。他的盲狗在雪地上追逐吉普车时被车上的神枪手打碎了头盖骨。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九章
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从睡梦中醒来。金黄的油灯光芒涂满油亮的墙壁。母亲坐在灯下,抚摸着一张金灿灿的黄鼠狼皮。她的膝盖上搁着一把青色的大剪刀。黄鼠狼蓬松的华尾在她手中跳跃着。炕前的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土黄|色棉军装、满面灰垢、状如猿猴的人。他用残缺的手指,苦恼地搔着花白的头颅。 “是金童吧?”他小心翼翼地问我,那两只漆黑的眼睛里射出可怜巴巴的亲切光芒。 母亲说:“金童,他是你司马……大哥呀……” 原来是司马亭。几年不见,他竞然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想当年站在松木搭成的瞭望台上生龙活虎的大栏镇镇长司马亭哪里去了?他的红彤彤的像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哪里去了? 神秘的骑马人打破司马凤和司马凰脑袋的时候,司马亭从我家西厢房的驴槽里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尖锐的枪声像针一样扎着他的耳膜。他在磨道里像一匹焦躁的毛驴,嗒嗒地奔跑着,转了一圈又一圈。潮水般的马蹄声从胡同里漫过去。他想:跑吧,不能躲在这里等死。他顶着一脑袋麦糠翻过我家低矮的南墙,落脚在一摊臭狗屎上,跌了一个四仰八叉。这时他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他急忙爬行到一个陈年的草垛后藏了身。在草垛的洞洞里,趴着一只正在产卵、冠子憋得通红的母鸡。紧接着响起沉重的、蛮横的砸门声。随即有几个脸蒙黑布的彪形大汉转到墙边,他们穿着千层底布鞋的大脚把墙边的枯萎的野草踩成细末,他们手里都提着乌黑的匣子枪。行动威猛,肆无忌惮,翻墙时犹如黑色的燕子,看样子很像大人物身边那些阴冷的保镖。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遮掩住面孔,后来得到司马凤、司马凰的死讯时,他混沌的脑子里才闪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似乎明白了许多事情。他们蹿进了院子。司马亭顾头不顾腚地钻进草垛,等待着结局。 “老二是老二,我是我。”司马亭对灯下的母亲说,“弟妹,咱们各论各的。” 母亲说:“那就叫大伯吧。金童,这是你司马亭大伯。” 在沉入梦乡之前,我看到司马亭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勋章,递给母亲。我听到他瓮声瓮气、羞羞答答地说:“弟妹,我已经将功折了罪。” 司马亭从草垛里钻出来,趁着迷蒙的夜色,逃出了村庄。半个月后,他被拉进了担架队,与一个黑脸的青年合抬一副担架。 我听到他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的传奇经历,好像一个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编造谎言的少年。母亲的头颅在灯影里晃动着,脸上像涂了一层黄金;母亲棱角分明的大嘴微微地向上噘着,形成了嘲讽地微笑着的神情。 “我说的都是真的,”司马亭委屈地说.。我知道你不相信,这大勋章,不是我自己造的吧?这是用脑袋换来的。” 响起了剪刀剪破黄鼠狼皮的声音,母亲说:“司马大哥,谁说是假的了?” 司马亭与黑脸青年抬着那个胸膛中弹的团长跌跌撞撞地在野地里奔跑。飞机闪烁着碧绿的光在空中飞行。炮弹和子弹拖着明亮的尾巴划破夜空,交织成一片密集的、变化多端的火网。炮弹爆炸的镁光像绿色的闪电一样打着哆嗦,照亮了他们脚下崎岖的田埂和收割后的、冻得僵硬的稻田。抬着担架的民夫散乱在稻田里,腿忙脚乱。不辨方向,胡乱奔跑。伤兵们的凄惨叫声在寒冷的暗夜里此起彼伏。带队的干部是一个留着二刀毛的女人,她拿着一只蒙着红绸的手电筒,站在田埂上大声地喊叫着:“别乱跑!别乱跑!保护伤员……”她的嗓音嘶哑,像用粗糙的鞋底磨擦干燥的砂烁。炸弹的镁光照绿了她的脸。她脖子上围着—条脏污的毛巾,腰里束着一条皮腰带,腰带上悬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和一只搪瓷缸子。这是个生龙活虎的女人,白天时,她穿着那件酱红色上衣,率领着担架连,在火线上飞来飞去。她像只不合时宜的花蝴蝶在火线上飞来飞去。成千上万发炸弹爆炸时掀起的灼热的气浪把冰封三尺的严冬变成了阳春,白天时司马亭看到在被热血烫融了的积雪旁边盛开了一朵金黄的蒲公英花朵。壕沟里热气腾腾,士兵们围在一起吃饭,雪白的馒头,鹅黄的大葱,咔咔嚓嚓,吃得欢畅。香甜的味道让饥肠辘辘的司马亭馋涎欲滴。民夫们坐在折叠起来的担架上,从干粮袋里抓出冻成冰渣的高粱米饭团子,愁眉若结、大口小口地吃着。他看到在前边的战壕里,蝴蝶一样的民夫连女连长正与一个腰挂手枪的干部谈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