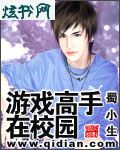疯狂游戏 by 楚云暮-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见面的地点约在离学校足足有两条大街远的星巴克,她挑了个掩映在一盆巨大的盆栽植物之后的位子,估计一会我和她要是一言不合由她或者我向对方脸上泼咖啡的行径也不至太多人目击。
“你知道了吧。”她咬着下唇,打断我的胡思乱想。
“啊。”我只能发出一个无意识的音节。沉默了好久,才说:“为什么。”
“你对我很好。可是阿祁,你有真的关心过我吗?”她垂下眼睑,“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在想什么在忙什么,从来不对我的事情感兴趣——我们之间甚至连共同话题都没有!”
我迷惑地眨眼,也不是啊,她生日时候我带她去赛特挑了一只BABY…G的时候,她和我可有共同话题了足足聊了三个小时。话在我脑中转了几圈,出口的却是:“那萧峰和你就有什么共同话题了吗?”
她象一下子被人踩到了痛处:“是,他对我没你那么大方,可是他有理想有追求,我想什么他都能理解!而你却只是吊儿郎当地混,我对你太失望了。张祁我真的爱过你,可却被你的漫不经心一点一点地磨平!”
我反应了很久才接受她血泪交融的控诉——原来弄了半天她不是嫌我哪里比不上别人,而是说我不够上进,不够和那般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的龟孙子同流合污?!原来她想和我分手只是我不能够象高中那样再罩着她护着她而已?
“没意思。那就分手吧。”走到这一步,我心里倒还算平静,只除了那一点点的失落和愤慨。
感情呵,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她脸色一变,为我的轻易出口:“你早就想甩我了是吧?张祁,我知道你一向很花,但是没想到你真的会这样对我!你反正对我无所谓何必还要装着假惺惺的样子?!你简直没救了,萧峰比你好上一百倍!我和你就这样完了!”她愤然离开,今年情人节我送她的NINEWEST女鞋的鞋跟在地上发出急促的敲击声。
我把桌上已经凉了的咖啡一饮而尽,想了想,又把对面吴亭亭连喝都没顾上喝一口的咖啡拖过来也喝个干净——总不能浪费吧,二三十一杯呢。
或许是喝多了,弥漫在舌尖的,竟是挥之不去地苦涩。
我在外面逛荡了许久,徐然打电话找了我几次,我都没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逛,到了江心公园,我走累了,买了两罐青啤就走了进去。坐在江边,被冷风一吹,思绪一下子空空荡荡起来。
人之百年,究竟是为了什么?若是抛开名利只为着得意尽欢,我为什么还是难以餍足?所谓人生,本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为什么还是不能潇洒走过?!
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我回头,终于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这样也能被你找到?”
徐然在我身边坐下:“你不接我电话我就知道你心情不好,从小到大你心情不好只会去一个地方。”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里曾经是我儿时的乐土,到如今也已经被周围钢筋水泥的建筑群侵占吞噬地差不多了,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角,龟缩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央。
他没有说一句话,自顾自地开了一罐啤酒,和我就这样闷喝着。
然后他问我:“易拉罐就是不经喝。还有么?”
我笑了,站起身来,顺手也把他拉起来:“就两罐,没了!哥出去给你买。”
“好啊。”他跳起来,笑容一如往昔。
小然子,永远不会说一句安慰我的话,我不需要,他也不需要。我永远是他强悍的保护者,在他面前,我不存在脆弱。
出去时我们顺着最繁华的解放路往学校走,买了两罐啤酒边走边喝,直到徐然突然一拉我,我差点被口中的啤酒呛到,埋怨地瞪他一眼。他忙把我拉到一边的阴影处,直到不远处两人勾肩搭背地招摇而过。
我定睛一看,才冷笑了一声,骂了句操,这都是些什么人那。
我看见吴亭亭她那个服装班的马艳丽和我们院里的书记走在一起,两个人旁若无人大包小包一脸惬意亲密无间幸福美满合家平安地走在一起我顿时想到了四个字——人面兽心。
徐然哼了一声,把手里的易拉罐重重一捏,丢进垃圾箱里:“走吧。别让他们发现了,到时候尴尬。”
我点头,没走几步,只听见徐然开口道:“阿祁。你看女人的眼光实在不怎么样。”
我揉揉他的头发:“你吗的连女人都没碰过知道什么啊。”
他不服气地争开:“谁不知道萧峰据说已经内定了下任的学生会长啊。就说从前, 她和你在一起就真只为了爱么?”
我无语,所以吴亭亭选择了萧峰,就象还长的人模狗样的马艳丽和那个发疏齿摇一看就知道是性功能障碍的书记在一起?因为我配不上她跟不上她了?屁!
谁说女人自古痴情?在当今这功利社会,女人一样势利。只可惜,我却不是她的跳板,她用过即丢的保险套。所谓的感情实在是荒谬的笑话。
心中有一个狂热的想法一闪而过。
那时的我却不知道,就是这一念之差,那样深远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到宿舍已经十二点多,我看着小然子进了他的宿舍,也打开门进去。今天是周五,江同的床上空无一人,估计又摧残国家幼苗去了,叶方回家,林恒和文学青年早睡死了。我着魔地盯着我的下铺看了许久,突然将床帘掀起,钻了进去。
如果人生如梦,我为什么不能再疯狂一点?我没有未来没有前途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追求,可我为什么不能放肆地快乐?太多的感触一下子压断了我仅有的理智。我本轻狂,有什么不可以?我只知道不能让别人任意辜负,睚眦必报从来是我行事准则,萧峰,或者我,都不会属于吴亭亭。
感情?太沉重。
我只要一场感官游戏!
萧峰正睡的迷迷糊糊,被我一吓,立时惊醒:“谁?!”我一把捂住他的嘴,压低身子:“别说话!”
他挣开我的手,压低声音:“张祁?”
黑暗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他周身散发出的热力,混着他或粗或细的鼻息,烧的我都有些眩晕。“你说你只喜欢我,是真的吗?”
他拧紧眉,声音又低沉了几分:“你是什么意思?”
在我没时间反悔或者思考的时候,我突然一口咬在他的嘴唇上,重到隐约渗出了几丝血腥: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一个疯狂游戏。”
9
在我没时间反悔或者思考的时候,我突然一口咬在他的嘴唇上,重到隐约渗出了几丝血腥: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一个疯狂游戏。”
黑暗之中,他嗤笑出声:“你这算什么?张祁,心血来潮下的游戏?”我也笑了,带着那么点的疯狂:“你不愿意?萧峰,你玩什么不是信手拈来,就没胆玩这个由你开始的游戏?!”
他的眸色又深了几分,几乎与黑夜容为一体。“这是你说的——张祁,你跑不掉了!”
我想说我根本没想逃,他突然逼近我,带着十足凌厉的气势把我往后压去,我促不及防,一个重心不稳,脑袋重重地叩在床板上,好大的声响。床帘外传来林恒将醒未醒的咕噜声。我心又跳快了几拍,竟有一种近乎偷情的紧张感。
“疯子!”我咬牙骂道,“你他吗的不会轻点啊!”
他蹬开棉被,把它整个盖在我们头上,我顿时动弹不得,任由他撕扯着我的衣服,在那个窄小而炽热的空间里纠缠着摩擦着,临界沸腾。
他突然松开我,黑暗中我只能感觉到肢体摩擦的热度与声音,而后下体一湿,我刹那间弹起身子:“啊——”——天,他,他居然——我什么也看不见,围绕着我的仍然是一片深重的黑暗,可就是因为这该死的看不见,我在脑海里开始想象他为我口交的淫荡画面。我闭了闭眼,想冷却下这种另类却更加沸腾的快感,但是——我往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大力地挺送:“你这混蛋——吗的——太爽了”我兴奋地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身上一处处都是火烧火燎的欲望在燃烧。我开始痉挛,窒闷的空间让我呼吸不畅,我只能更加放肆地喘息着,野蛮地抽送,想缓解,想平息,又想颉取更大的高潮——我发抖着喊:“操。。。要,出来了。。。萧峰——你这变态——放开!”他突然离开,重又压回我身上,微凉的双手接替嘴巴的工作,我几乎被他压成一个恐怖地角度,那快感却没有丝毫减弱,直到他咬着我的耳垂,含糊不清地说道:“很爽吧?那他吗的也小点声叫床——真想把所有人都闹起来?!”
就在这一刹那,我很丢脸的在他手里泻了,喷射了一道又一道,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脑中已经是缺氧似的空白,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掀开被子,剧烈地喘息起来,就在这时萧峰又欺了上来,低头赌住我的嘴,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腥檀味道在我和他唇齿间弥漫开来,热浪席卷,我只觉得脑中一片充血,羞耻感使我别过头,摆脱他的纠缠,低声骂了一句他吗的。
他笑了,我忍不住回头怒视,却被他的笑容震住,他的双眼在浓黑的夜色里是那样的光华流转,璀璨晶亮。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片刻的失神。
其实我和他,说到底,也就是互相充当了对方的右手,去执行一个本来不可能的任务。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背德的情欲游戏中,我却有那么多的快感。和女人做完全不同,我没有任何责任任何义务更没有任何退缩,想要就要,肆无忌惮——男人永远都最明白男人需要的是怎样的爱抚和快感,更何况,萧峰与我,都算是久经沙场。即便已经过了三天,我依然在回味那晚的激情。
我盯着自己的右手看了很久,直到另一只手在我面前死命晃悠:“阿祁!你发什么愣啊!”
我堪堪回神,一把打开他的手骂道:“谁发愣了。”
徐然笑嘻嘻地偏头说:“阿祁,你不对劲啊,刚才起就盯着你的右手死命看,干吗?看手相啊,张半仙?”
我毫不客气地再次抓烂他精心打造的发型:“去去去,我是半仙就不来趟这混水了。”
可以说美术系是整个学校里最西化的学院,所有关于西方的思潮从性解放到消灭处女再到虚伪的小资情节都学了个囫囵吞枣。据说从建系起,就开创了圣诞舞会这个阴阳怪气的传统,妄想遏止住大家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势头,坚持肥水不留外人田,坚定地支持第一任院领导关于催发系内男女体内荷尔蒙分泌的正确指导。估计第一界举办地颇为成功,不少学生弥补了受伤而空虚的心灵,再次青春焕发,令领导们大有成就感,之后年年如是,只有文革时停了六七年,据说那时候改为所有领导即学生代表集体朗诵沁园春…雪。
我张祁怎么说也是个社会主义好青年不是,怎么能被这种资本主义流毒侵蚀?所以坚决不去,奈何左右两个小人死命对我精神洗脑,终于和平演变自我解体,被徐然王毅死拖了来,参与这个全民造爱运动。其实王毅拖我来情有可缘,他家小丽要上新东方,没空领略他的舞台风采,他伤心失意之余,只好拉我来当垫背的,可徐然也死命拉我来就说不过去了,难不成他还想和我跳啊?!
院多功能厅还是挺豪华的,够的上上面那班人腐败的标准,新生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不免有些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就算我们院里的女生多属印象主义,男生们——特指目前还没法花开并蒂的孤独少年们,顿时有了成为新时代莫奈的勇气,不一会,倒也是将舞会的气氛吵的红红火火。
我坐在位子上咋舌看着王毅和另一个女生跳的起劲,仿佛瑞奇马丁附身,一下子把新东方的小丽忘到爪哇去。
“你怎么不找人跳啊?你看人王毅。我以前都没看出这小子这么有花心的资本。”我开了罐可乐递过去,徐然接了,撇嘴道:“找谁啊?把兄弟撇下与狼共舞我才不做。”
我乐了,感情他要在这舞会上陪我一晚上啊。“那你这么死拖我来干吗?”
他喝了一口可乐,才缓缓说道:“阿祁我希望你开心点。出来转换转换心情也好啊。你这些天都没怎么理我们。。。”
我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他是想安慰我呢,原来我应该还处在失恋的状态下,觉得了无生趣,怅然若失啊。“小然子你还真是。。。”我又想感动又想笑,“你看哥我象是会为了个女人失落的人吗?小弟弟一个还安慰我?”我又习惯性地抓他头,玩的不亦乐乎。
他顿了一下,也就愣我玩去:“那你这两天怎么都没来找我?打你电话也常关机?”
我不由心虚,脸一红,掩饰地骂了句:“哪有。你他吗就是多心。我好的很,啥事没有!”
这两天我都和萧峰撕混在一起了,哪还记得其他的事。
我两只眼全场乱瞄,萧峰正和一个足以包揽后年雅典奥运柔道组冠军金牌的女生跳舞,我不禁哑然,萧峰是我们班班长兼学生会副主席,所有两委工作他好象都插了一脚,这个紧要关头要充分发挥组织的优越性与主动性,充分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冲他这么勉为其难还要身先士卒共赴国难我也得对他说个服字。他这收买人心还真是贯彻的十分彻底。一曲终了,我看见一直作壁上观的吴亭亭下了舞池,走向萧峰。我感到身边徐然的身子一僵:“阿祁。”——他怎么比我还敏感啊。说一点不难受是骗人的,吴亭亭这样做等于当众让我没脸,我多少还是有点不是滋味。“男人拿的起就要放的下,你瞎操心什么?萧峰还不一定看上她了呢。”
徐然不说话了,闷头喝水。
萧峰带着吴亭亭转了几圈,面对我的时候,突然勾起嘴角冲我邪邪一笑。我哼了一声,别过头和徐然搭话。没一分钟,他就放开吴亭亭,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走下舞池,转向我这个方向走来。我分明看见她的脸在这一刹那变的惨白。他在我面前站定,笑的就象一个领导在视察工作:“张同学啊,你怎么不下场跳呢?”
我爱理不理:“不想跳。”
“那你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他笑的更假了。
我故意凑近徐然:“小然子,你告诉他,我们刚才在聊什么?”
徐然有些紧张,他显然以为我和萧峰的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是为了那只母孔雀。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啊。”
一只手悄然伸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