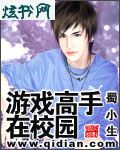疯狂游戏 by 楚云暮-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过我怡然自得嬉笑怒骂的惬意人生,井水不犯河水。
“张祁。还不起床,又要迟到了。”林恒敲敲我的床板,我拉开床帘,所有的人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颓然躺下:“不去了。。。头痛。”
“最近严打啊,你又不去?这样旷法找死啊。”林恒一脸不赞同。
我别过脸哼了一声:“理他呢。出事再说。”
我是真有点不舒服,也没咳嗽,就是头疼的很,喉咙一阵一阵的烧。估计最近寒流来袭我还是懒的加衣服的缘故。正好明目张胆有恃无恐地翘课。
叶方在门口叫了一声:“林恒,你走不走?”
“来了。”他从来不是个话多的人,自然不会为了我破例,也就是随口一句:“那有点名我尽量帮你哦。”
是啊。我与谁有什么交情,人和人之间,从来是一片漠然。
我拉上床帘,背过身就睡了。
昏昏沉沉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迷糊中听见有几个声响。我想起身,却觉得头越睡越沉,勉强转过身来,只见床帘上印出一个熟悉的轮廓。或许是睡迷糊了,我一个激灵,来不及细想就一把掀起床帘,和他对目而视。
萧峰怔了一下,抓在手上的药不知道拿还是放,一手还提着一袋白粥。
“你干吗?”我的声音说不出来嘶哑,自己听的都象是痨病鬼。
如果我没猜错,他的脸上那一闪而过的神情叫做尴尬。
但萧峰毕竟是萧峰,用我后来形容他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脸皮要不是厚到一定程度,还真演不来他这种两面讨好的角色。他虽然没想到我会突然清醒,却还是一脸泰然地开口:“把粥喝了,之后红色药丸吃两粒蓝色一粒。”
我哼了一声,不是说谁也不欠谁么?假慈悲什么。
“要你管。”我自己都觉得语气有些幼稚,甚至象还在报复那天晚上他的出言不逊。
他淡然看着我:“你放心。张祁。。。下课后我会叫徐然来照顾你。”
这和小然子有什么关系?我莫名其妙。“叫他干什么?”我不会在徐然面前表现出一丝的弱势。
他脸色微变,把东西一扔就转身出去。门关上的时候,发出碰的好大的声响。
神经病。我无力地躺下,愤然骂了一句。
这次却是怎么也睡不着。展转反复了好久,时至中午,宿舍楼里渐渐地人声鼎沸起来。
宿舍门被打开,一个声音道:“妈的那老处女越来越变态了,一天点上三次名,最后还把黄宾也给叫过来了。”
我听出那个声音是江同,他翘课记录没比我逊色多少,所有时间全贡献给那一 片如花似玉的祖国花朵身上了。
叶方在旁搭腔:“是啊,据说要开始整顿美术系逃课的风气,从重处理呢。”
江同从鼻孔了哼了一声:“那也不是。有人就不怕这个。”
“你说的是——”
“张祁咯。今天他也是照样不去上,谁知道现在上哪混去了。人家背后有人撑着呢。”
“操。你别说。萧峰那么会钻营,上上下下哪个人不对他服服帖贴?这次他上了一半就翘了,哪个老师怀疑了?真相信他病了。我只是不明白,他怎么就对张祁特别照顾?每次都帮他点名,今天查的那么严,林恒答应了还屁都不敢放一个,他也敢替他喊到,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叶方的声音忿忿不平,象对于这种替点的现象疾恶如仇。
“那你就不知道了。”江同的声音顿了顿,压低了道,“你知道张祁家里条件不错吧,人家的爸爸做进出口贸易的,妈妈又是什么大官,你看他怎么一副公子哥的样儿,去哪都是他出钱请客,了不起似的,徐然还有隔壁班的王毅都绕着他转,萧峰也是看着人有钱想巴结巴结呢,以后找工作也想方便方便。”
我知道江同一向是拜金的,从他身上那成堆的假CK,假GUCCI就可以看的出来。却没想到他他吗的心里这么肮脏,比他身上的假名牌还要恶心。
叶方听了他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的一番高谈阔论,吃吃一笑:“那我还听说另一个版本呢。。。萧峰是在补偿张祁呢,你知道吗?他和——”
到如今我才知道男人的嘴糟蹋起人来一点不比碎嘴的女人差,反而有过之无不及。我刷地拉开床帘,从上铺爬下。
他们的脸一下子变的惨白,估计看上去比我还象个痨病鬼。
“人的嘴是用来吃饭的,不是他吗的用来喷粪的!”
我抽出牙刷毛巾,碰地一声又把洗手间的门踹开。
去死吧。
都是些什么肮脏的东西!这个学校根本就是藏污纳垢的下水道!
我后来还是很没气节地吃了萧峰送过来的药,好吧,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丢份,但怎么说也比病着强不是,咱中国人的古训不就是有奶便是娘吗?
尽管在我未知且知道的话也一定不愿意的时候,萧峰帮过我不少忙,作为我们院里风头最劲的翘课积极分子,我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批准火线入党,首当其冲被召进党支部面谈。
黄宾同志坐下来看的时候,其实那海拔与常人并无二致,所以为什么人大政协开会总坐着,一是因为耗费的时间太长以至于人的耻骨联合不足以支撑骨盆以上的身体重量,二就是为了从海拔高度上灌策统一政策。
“张祁。”他严肃地点点头,示意了下,“坐。”
我立即正襟危坐。
“你知道这学期你已经旷了多少节课了?”
我摸摸头:“不大记得了。”
“不记得?”黄宾的反应其实有点大惊小怪,就差拍案而起,“你说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话,谁知道究竟哪些课有人帮我点,哪些没有啊?
“那我告诉你,你已经缺了20多节课了,很多同学都有反映你学习散漫,影响不好。你知道旷课20节要受什么处分吗?”他点点桌子,“是大过!你想清楚了没?大过!”
我乐了,这小男人的口吻怎么和我妈象了个十成十啊,想当年我妈改造我时那个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啊。我立即诚恳地恩了一声。
“当然,我们学校领导不会不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进来时的成绩是院里第一,怎么想都是有前途的。你要重新做人。。。”
他究竟说了多久我没印象了,总之我的屁股坐的火烧火燎的痛,象长了痔疮一样。我只知道事情有了转机,立即涕零泪下坦白从宽,说自己怎么就油脂蒙了心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我怎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等等,这都是我面对我妈的围剿惯用的游击伎俩,再次信手拈来自然得心应手。黄宾倒被我唬的一愣一愣的最后反而安慰我肯回头就是好的,社会不会放弃一个失足青年的改造。
我出来的时候,徐然王毅已经靠在榕树上等的快睡着,徐然一见我出来就有气无力地一句:“又创新高啊。”我走过去揉揉他的头发,“不是,这次的时间主要用来预演《我的自白书》,由于演出反响强烈,不得已在观众要求下加演三场,以至于耽误了一点点时间——”
徐然笑着一脚过来:“你再贫啊。怎么弄到黄宾也来找你麻烦?翘课的人多去了呢。”
我冷笑一声:“有人打小报告暗整我呢。不说这个,那些人除了嘴碎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我们一会上哪打球去?”
“校篮球场咯,一个人才两块。”王毅插嘴。我斜了他一眼:“拉倒吧,你还不是因为校场离外院宿舍近些,一会好去接你的小丽。”
他笑的很是花痴,我一脸恶心地扭过脸去:“德行!看你那出息!”
我们走着就路过院里,一楼的展厅里人潮涌动,象都在忙活什么。
“这又是干什么?”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搜寻一个身影,随口问道。
“院里一个教授办个展,所有两委的人都去凑份子献殷勤了,阿祁,咱们快走吧,这有什么好看的。”他开始推着我走。
“哦。”我本来就要走,他这么一催促我倒诧异了,他没事催什么。身边王毅一声叫唤,“哎哟,这不是嫂子吗?祁哥,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啊?”
徐然一个眼神凌厉地过去,逼地他立即消音。我更狐疑了,又抬眼看去,只见大冬天的还穿着个花枝招展的吴亭亭飞到了萧峰身边,又是送水又是擦汗。去他们的!大冬天还擦个屁汗!
没想到他萧峰还真是水陆兼容所向无敌啊,还是说他是个兔子根本就是诓我的?!
虽然隔的远听不见他们在绵什么,可这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还用的着猜吗。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声音不大却十足阴沉。
王毅再不敢说半句。徐然叹了声,才道:“也就这几个星期,他们走的很近,传言几乎。。。传遍了。”
我突然醒悟那天在宿舍里那两个混蛋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
“。。。萧峰是在补偿张祁呢,你知道吗?他和——”
操。我觉得我被耍了。19年来还没一个人敢耍我!
入夜的时候我一反常态地没有出去夜游,而是在萧峰回来必经的楼道上等他。
无论如何,我也要个理由。
没男人被戴了这么顶绿帽子还咽的下这口气的!
我看见他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我开口的声音竟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暴跳如雷。
“萧峰。你出来下。”
他微怔,随即也跟着我到宿舍楼后面的角落里。
“你不错嘛。”我从兜里掏出一只烟,点上了,眯着眼吞吐了一片的乌烟瘴气,“真是个带把的——玩我女人?!”
他眉头一下子拧了起来,或许为我侮辱性的言辞或许为我挑衅似的态度。“你说吴亭亭?”
“你别装蒜,事都传遍了就瞒我一个!”
他哼地一声笑出来:“我找她?你没毛病吧?!是她自己粘上来的,你吗的不说她自己放贱。”
我一把扯起他的衣领:“吗的你嘴巴放干净些!”我一向护短,再怎样我也不让人说我女人下贱!
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象用尽全力,“你找女人真他吗的没眼光。平常找机会套近乎就算了,还他吗的老贴过来说她和你之间早就怎样怎样了,说她很寂寞希望人关心。操,这不叫倒贴叫什么!”
“闭嘴!”我又是一拳过去,叫我怎么忍受我曾经喜欢过的女人这么放浪的行径!这监视是对我的侮辱!“你明明就是故意的!你要和我争!”
他被我打的后退两步,抬起头来,突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我故意的?和你争那种女人?张祁,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被他的气势吓住了,一时无从辩驳。
他走进一步,扬起拳头,狠狠地还击,“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他吗的对你怎么样你自己知道!我要的从来只有你!”
我被震地跌坐在地,好久都没能正常思考——他,他方才说什么?!
8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她吴亭亭究竟是哪里抽风了想甩了我和萧峰在一起?我怎么看都不至于人老珠黄成这样啊!我也很想发扬国粹阿Q似的自我安慰说其实她不懂我的好可我就是咽不下着口气!男人都是要面子的,发生这种事简直象一个过气的玉女明星终于下定决心拍三级,脱光衣服之后导演告诉她身材太差不让拍,两个字概括就是——丢脸。
我整天吃了睡睡了吃,剩下的时间除了想这个问题就是泡在电脑游戏里,谁说虚拟网络害人的?他知道个屁!它挽救了多少个象我这样一腔愤恨无从发泄的边缘青年啊。要不是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能对天天在我身边进进出出的人视若无睹吗?
那天晚上我真的被吓住了,转身就走,一时把面子问题都给放在一边。现在想来,真应该给他补上一拳。小爷我是被他白打的啊?!当然我死不会承认我那个行为是不知所措下的落荒而逃——如果你他吗的被一个和你一样都是带把的男人告白了,你还能镇静自若地站在原地,合计着应该还他一拳,那只能说你比我牛。我还真做不到这点。所以我逃了,毫无尊严地逃了。
一个不留神,我就被那怪物一阵乱射,顿时元气大伤。同队的人直寒骖我:你不是吧,就这个级别的你就挂了?操!老子纵横江湖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最近没有新游戏可玩我开始玩近来很红的魔力,上线之后才发现这个游戏之所以红,也是因为它是广大男男女女为了增强水乳交融的紧密性而发明的一种可以在所谓浪漫的环境下增进感情指数的方法——最关键的是这种环境还是免费的。于是有无数人趋之若骛,奉若神明。
我干脆ESC了,电脑恢复清明之后我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奋战一日我只喝了一杯果奶,仔细想想还是徐然前天留下来的。不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怎么说也不能饿死在在这给咱们国家国际形象抹黑啊。于是摇摇晃晃出门,没走几步,就在走廊上和他狭路相逢了。萧峰在几个男生的簇拥之中,低声讨论着什么,直到抬眼看了我,忽然住口,意味不明地哼了一声。
完了。现在没有电脑的掩护,我怎么面对他?心里一阵急切地乱想,仿佛不是他烧我后院而是我让他戴了绿帽。他那边是人群簇拥热闹非凡,我这里是形单影只冷冷清清,外加面有菜色举步维艰。怎么看都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先天低他一等。
我不自觉地挺起脊梁,冷淡地将头别向一边。
他那晚最后说的话又袭上心头:“张祁,如果你真是个直的,为什么不真的和我断个干净!”
什么直的弯的我不知道,但是那句话我是真的记住了——我为什么真的不能和他断个干净?!若是换了其他人,我或许已经大打出手,揍的他变形为止。可为什么惟独对萧峰——?!
只觉得周围的声音瞬间小了下来,估计我和他之间的暗流是人都看出来了。
我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多多少少报了一箭之仇。
我的面无表情在到达食堂之后立即土崩瓦解,在对那我原本认为是猪食一样的饭菜奸淫掳掠之后,我才稍微恢复了一点人样,开始真正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总不能就这样拖下去。如果吴亭亭真想脚踏两只船我也不愿意当个冤大头让她耍。游移不定不是我的性格,其实很多事情早就该有个结果。
于是我拨通了那个号码:“亭亭?是我。出来聊一下好吗?”
我们见面的地点约在离学校足足有两条大街远的星巴克,她挑了个掩映在一盆巨大的盆栽植物之后的位子,估计一会我和她要是一言不合由她或者我向对方脸上泼咖啡的行径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