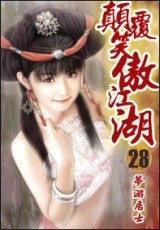江湖 作者:萧拂-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我根本就不该生得如此美丽。如果我能飞,飞起来又够高,足以驾月横天驰骋长空,那么生得美丽,还可以说是不负浩浩长风与朗朗月华,可是如果我最多只能在崆峒山上吹吹风,并且时常因为别人为我争风吃醋而被打断,那美丽就不能不说是蛇足。
因为美丽,我也不能在藏经阁里多呆。藏经阁一般来说是个清贫的地方,里面大多是刚入门的弟子和背运的长辈,虽说穷了一点,也还有些别样的好处,譬如说一本剑谱拳谱要练个透熟,平均起来总得三五年功夫,三五年的功夫每个人只借一本书,闲自然也闲得可以。然而自我来了之后,这清闲二字也就谈不上,来藏经阁借书的人开始多如季节来了往海里回游的鱼群。有些人早上借了剑谱,下午来还。又有些今天借剑谱,明天借拳谱,再后天借内功心法。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可以料想崆峒派不久就可以跨越少林武当峨嵋昆仑而雄视武林,但是我师父对崆峒派的前途并不关心,不久就遏止了这种疯狂的势头,叫我去记崆峒武林日志。
记武林志是个简单的工作,并不需要实地考察,起码不需要我自己去实地考察,只是在江湖上发生的事情传入崆峒的时候,记下来就行了。凡名门正派及一流高手的种种事迹,都在记录之列。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武林志里居然发现了丫头,就记在一流高手艳阳天之死条目下面。
再次见到丫头的心情是复杂的。这个熟悉而充满生气的名字仿佛是在验证我的生活不知所云,无论是貌似天风的山风、季节鱼群、争风打架,还是这个武林志本身。丫头现在在峨嵋,不知是否还生气如昔?也许一切都诚如我当年所说,逝者如斯?
那个时代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天际连绵飘忽的飞云,河边青了又红红了又青的枫林,都再也不回来了。
如花之一
窗户换了。现在的窗外不再是一片市声的茶馆,而是一条平缓流动的河,河水里面倒映着碧空白云与岸边的青青枫林,风景很好。开出窗去,也不用再怕见到茶馆里那拔麻木不仁的人了。可是我仍然不太愿意开窗。当窗外是茶馆,我怕望出去,见不到他。当窗外是河,我怕望出去,见不到他的影子。一个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的世界是陌生而不能想象的。
但是他喜欢开窗,开着窗看风景。结婚之前我曾经以为他不是爱看风景的人,现在看来是个误会。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或许是太多了,多到让人都懒得再去深究。同样一个惫懒,为什么我不喜欢,丫头会喜欢?同样一条河流,为什么看在我眼里,一定不同于看在他眼里的?同样一双眼睛,他以为毫无疑问是自己的,可怎么知道我总是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他?
他开窗,我就走开。走开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他还站在窗口, 一眼看过去,宽宽的身影嵌在以窗口为框的优美风景画里,宛如一个刺眼的败笔。
阿紫之一
原来爱上一个人,根本就不象英雄比武,可以从容不迫地施展浑身解数。比如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只能是瞪大双眼盯准了他,象一个傻妞,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流态度。
我不知道具体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他的。是他勾着手叫我从队列里站出来和他对剑?是他绞飞了我的剑又接住剑递过来?是递过来之后又叹息说你这个笨丫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鬼鬼祟祟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只能是瞪大眼睛傻看着他了。
鬼鬼祟祟,是他自己的说法。他说没想到爱一个人就象是做贼似的。其实别人相爱未必就也象是做贼,只有他的脸皮薄成这样,说是身为大师兄,得在师弟妹们面前保持尊严。
为了他的这份尊严,我不得不经常在山坳里独自徘徊,等待着他甩脱师弟们的纠缠前来赴约。有时候他能顺利脱身,有时候他脱不了身。脱不了身的时候第二天他总会找我对剑,绞飞我的剑,又再递给我,然后趁机说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总是给他机会,没有要求剥夺他莫名其妙的尊严。也许男人害羞是件好事,也许男人倔性也是件好事,也许恋爱的女人总是心太软。
丫头之二
断臂师伯和我一起伏在窗口上看云。我寻思着该用什么理由走开才好,这云很没味?无意中扭头,却发现身后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看着,遇上我就又掉开,连师兄也不例外。我掉转头,若无其事地又再看云,白云飘浮之中很久之前的那个梦境宛如一幅陈旧画卷倏然打开,黑夜、沙滩、鼓声、火把、执着各样兵器的人呼啸着在追,我奔逃。
其实我知道断臂师伯为什么单单要找我说话,甚至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对我来说他意味着什么。他就是那口圆圆拱起的铁锅和那根快要坠断了的葫芦藤的峨嵋派翻版,无时无刻不在以其圆圆直直的姿态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攻击。但是又与铁锅和葫芦藤不同,师伯是活的,我可以为免受诱惑而另辟蹊径,绕开铁锅和葫芦藤,却无法绕开师伯。准确地说,不是无法绕开,而是我还没有打定到底是绕还是不绕的主意。如果不绕,则我对铁锅与葫芦藤实施打击,就会立刻品尝到欲望得逞的强烈快感。然而快感过后可以想象马上会有无数人马敲着碎锅片冲杀过来,这又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如果绕开,恐惧是没了,可又品尝不到欲望得逞的巨大甜美。
左思右想,难拿主意。如果主意拿定了倒也一切简单,不绕开就不说了,要想绕开的话,至多对师伯吼一声也就万事大吉:死残废,滚开!当然,师伯跟我无冤无仇,这么着吼他于心不忍,不过回过头来想想,我与师伯也无冤无仇,他干嘛要这样诱惑着凑上来害我!?然而如今看来,事情又不是或绕或不绕这么简单,还没等到我打定主意,第三条道路倒出现了。甜美的滋味还没见影踪,恐惧就已经露出狰狞面目。那么会不会还相应地存在着第四条道路,只品尝甜美而不遭遇恐惧?
很简单,只要我练成风云剑法。只要练成了剑法,我就可以不再恐惧,在沙滩上立定脚步转过身来,横剑冷对杂沓的追逐者。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第四条道路和第三条实质是一条道,只是在时间上有些差别。区别只在于我是先练成风云剑法呢,还是先被追上。理智点看,先被追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追兵已经从后赶来,而峨嵋派缺乏灵气的飞云却使剑法的练成变得遥遥无期。事实上,就是峨嵋派的云充满灵气,我也无法练成剑法。从刺艳阳天的那一剑来看,风云剑法的真谛应该在于没有恐惧然后才能随心所欲,然而我想的却是只要练成剑法,我就将不再恐惧。
师伯一天天地凑过来,如同一口巨大的活动的铁锅向我步步逼近。我一天天地努力看云。有时候我看见云,有时候我看见他。他在提笔写字,字在纸上发抖。我恨他。
龙儿之二
关于丫头杀艳阳天的事,武林志是这样记载的:丫头自小是个热心肠的人,自艳阳天贴出对联之后,就有心挽救同胞于危难之中,于是不顾自己身处下联这一事实,历经千辛万苦率先找到艳阳天,诱而杀之。
这种记载是奇怪的。不过武林志也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书,一般来说,写的人不信,而懂的人也根本就用不着看——说来说去,无非江湖诡谲四字而已。具体到上面这条记载,诡谲之处在于乍一看,以为是说丫头英雄,再一看,原来是在维护艳阳天,说他并无违约。那倒也是,堂堂一个一流高手,怎么可能出尔反尔?
我就是在记着这样的武林志,挥毫落墨的时候山风从窗户里灌进来,吹得我衣袂飞动凌空乱舞,这景象就是丫头看见了,也不会再说我不象仙子了吧?何况崆峒派与红花会万里迢遥,我的衣带上也早就没了那朵玫瑰。
如花之二
坐在窗前,最多的时候我是往回想,想那个甜蜜而又倒霉的十四岁。其实我一生的运数从那个十四岁也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十四岁的时候,女孩子们差不多都在想和裘马翩翩的浊世佳公子花前月下,而我偏偏在茶馆里爱上一个算命的瞎子,多么不现实。十四岁的女孩子为了爱人哪怕是赴汤蹈火都不会皱一皱眉,而我却整整花了十天的功夫说服自己不要放弃现在的锦衣玉食,我又是多么现实。
现实到如今,也许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好歹是在锦衣玉食中回想擦肩而过的恋人,而不是在恋人身边想过去的锦衣玉食。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一生的运数在十四岁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我活到十四岁不也就够了么,还要辛辛苦苦地再活许多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已经被看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又有个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到底十四岁还是一个错误。
阿紫之二
他的手很巧,在山坳里采了无数野花,编成一个漂亮的花环,给我戴在头上。他说我戴着花环的样子就象是个花妖。
可我不是花妖。花妖不知愁而我知道。山坳里面遍布了我孤孤独独的脚印,使我不得不去想这样一个不愉快的问题:如果我苦苦等待的痛苦焦灼最终竟抵不上他的尊严与薄面皮,那么我在他心中的份量究竟能有多重?
他看着象花妖一样的我拍手笑了起来,象一个孩子。我戴着花环笑着钻进他的怀里,也象是一个孩子。然而这种感觉仍然是不对的,他怎么竟恰似一颗裹着糖衣的药丸,慢慢地吮到里面,就会觉出苦的滋味来?
丫头之三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写字,看见我,抬起头来。我扫一眼,看见写的是婚礼请柬。他微笑着问我有事么?恭喜呀,我说。同喜,他回答。我凝视着他。他有些儿慌乱,四处看看而后指着张椅子说坐。我没坐,只慢慢地说现在还来得及。来得及什么?不娶如花,娶我。他蓦地低下头去,重新写字,手不稳,字在纸上发抖。后来他不写了,一只手按着纸,一只手握着笔凝在空中不动。
他的手仍旧漂亮、健康而有力,只是热度降低了,骨关节在变白。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好兆头应该是热度升高肤色发红,而后将毛笔一扔在纸上弹出一个墨团说,一点不错!他忽尔微笑起来,向着我说那怎么行?那怎么不行?要是你只喜欢我?我死劲地盯着他。他缓缓摇头。
我恨他。如果不是他,我就不会从桃花源般别有洞天的窟窿中被抛出来,落到危机四伏的峨嵋山上。如果不是他,我也不必成天成天地看云,因为练不成风云剑法而从骨子里面栗栗生寒。我恨他,尤其恨他什么都能让阿紫说中。阿紫说我永远也没有可能得到他,第一,如花比我漂亮;第二,如花比我更适合做妻子;第三,如花比我有势力;第四,如花代表江湖信誉。怎能设想一个正常人会不顾以上四个优点倒去娶我?我冷笑道,如花的优点再多,难道能顶得上他最终是掉进了我的窟窿?阿紫冷笑回来说,一样的。果然一样。只是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
当初他递过打倒艳阳天的狼牙棒,让我重新演示整个过程。我一招一式地比划了,遗憾的是大功告成的那一剑却怎样也找不回当时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有点儿羞涩,我转过头,却发现他并不在看。他在看着我,很专注地在探究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我不明白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突然之间变得奇怪起来。是因为发生了巨变么?是怀疑我已经被艳阳天做了么?是惊佩我反把艳阳天做了么?可都不该有那么一股笑谑的味儿呀。只有他是不带这种味道的,可还是很不对劲。我莫名其妙地红了脸。他从我手中接过剑棒,也比划了一下,问是这样吗?那顺手刺出去一剑很漂亮,让人看着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的颖悟也该比得上龙儿了,本不该属于尘世,更不该属于凡夫俗子,也不该属于我,最后却要归了如花。是这样的,我说。他看我一眼,眼神还是非常奇怪,我还是不明白为了什么。
懵懂的状态直到最后转回房间才总算结束,我一眼看见了摊开在桌上的那本日记,页数已经不在艳阳天看过的狼牙棒那里。
我不知道他们都看到了些什么。我喜欢他?认了。狼牙棒与天意?那是实事,也认了。但总还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该被看到的,譬如说我对我和他的将来所作的虚构性描述。我于冰冷的冬夜在群山中流浪,看见一簇火光。火光遥远地跳跃着,送来温暖和烤肉的香气。我连剑带鞘拨开长草走过去,看见了他,以及正在火焰上烤着的一只说不上来是鸟还是鸡的东西。他没有看见我,忧郁地凝视着远方,眼光从我脸上穿透过去,深邃而幽远。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注意到了我,但是依旧没有说话。我们隔火相对,很静默、很温暖、烤鸡的味道芬芳如花。
我为我居然编出这么个故事感到害羞。我好好地为什么要去流浪?流浪为什么也流得不三不四,偏要于三更半夜之中出现在深山老林里面?而他为什么又那么奇巧三更半夜也出现在深山老林里面?这也罢了,糟糕的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竟然不象是他。事实上,是一个比他要深沉、沧桑、老辣、冷峻并且潇洒的人。这个人在远山里烧起一堆火,有时候遥望天际,有时候盯着火焰沉思,等着总有一天会走到火前和他共享那只烤鸡的我。
对于情节的这种安排说明我不很坚贞,如果被他看到,恐怕就不大可能跳进我的窟窿里来了。他到底看没看到呢?这一点从行为上不大看得出来,他把剑棒又递还给我。只是递过棒子的时候有点迁延,是不是因为已经了然了棒中真意呢?
如此看来事情果真象龙儿所说在顺其自然地进行着,先是艳阳天将我深藏若虚的日记翻出来,然后又被别人看见,然后他就知道我已经奋不顾身地跳进了他的窟窿,并明白在他的前方也有这么个窟窿在等着他跳进去,再然后当然顺理成章就是他也奋不顾身地往我的窟窿里跳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