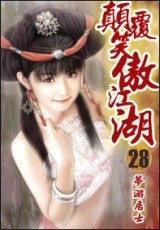江湖 作者:萧拂-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四岁那年,我杀了一只虎。事后人们问我是怎么杀的,我说没怎么杀,就是它自己扑上了我的剑尖。没人信。后来我只好改口说我和它在狂风黑雾中大战三百回合,终于杀了它。还是没人信。不信拉倒,我也懒得再改口了,就是这样,狂风卷地黑雾蔽天,我大战三百回合,刺杀了一只猛虎。
刺杀猛虎之前,我站在山崖上拔剑抒情。一般来说,诗人喜欢来这套,尤其李太白更喜欢。但我不是诗人是江湖人,剑于我不是吟诗的道具而是杀人的利器,所以拔出剑来干的事也比太白出彩。我往后挥剑,剑尖遇上了阻力,并且,控制不住地往下直坠。回过头,就看见这只带着剑尖一起下坠的虎。
这只虎后来我送给了如花。如花可以说是全江湖我最不欲送给这只虎的人,但是没办法,不送给她的话似乎说不过去,谁都知道她的嫁妆就差最后一副虎皮了。我杀了虎,这不是件小事,要瞒也未必瞒得住,何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个猎户。虎一落地,这两个人就无巧不巧地从树林里哗啦啦钻出来,一起将钢叉夹在腋下,空出手来噼噼啪啪地鼓掌:好剑法,一剑穿心!我看看他们,又看看虎,慢吞吞地在虎毛上拭剑,在想该不该将他们杀掉灭口。如果杀掉灭口,如花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我在虎毛上将就着蹭掉剑上的血迹,插回剑鞘。
杀人灭口这种事江湖上挺流行,听起来有一种快刀切水豆腐的爽利感觉,只不过一般不大会为了一只虎给不给如花这种屁大小事而杀罢了。虽然如此,我仍然对两个猎户的生命安全充满怀疑,要是他们碰见的不是我呢?而是另一个恨如花并且很容易将对如花的恨意转移到任何人身上去的人呢?要是遇见了这样的人,他们就得完蛋。如此说来,他们今天之所以苟全性命,完全是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虽然不愿意将虎送给如花,却也不恨如花,更不喜欢随便迁怒。而我的这些品质对于这两个猎户来说,是一种偶然,因此他们是借着偶然才活下去。我也是借着偶然才活下来,虎扑过来的时候正值我挥剑抒情。由此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着偶然才勉强存活,这就是所谓江湖。
虎送出去以后如花父亲天鹰教教主礼尚往来,回敬了我一个绰号。他说你乳名丫头,杀了只虎,就叫搏虎丫头吧。这个绰号太难听了,我请求他重起。他很不高兴,说起绰号又不是为了好听,是要名副其实的。如花替我帮腔说就再起一个嘛,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教主回说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这四个字,切事切人,千金不易,不要再说了。就这样,我由丫头变成了搏虎丫头。关于这个绰号,我印象最深的是龙儿险些笑岔了气。她穿着雪白丝袍,腰间插一朵艳色欲滴的玫瑰花,喘不过气弱不胜笑的样子非常动人。龙儿总是能很好地把握每一个动人的瞬间,换在如花父亲面前,她一定会敛衽颔首说,教主高见。她敛衽颔首的姿态静穆端严,这样,教主就也会觉得她非常动人。
得了绰号以后如花送我出来,开解我说好在只是个绰号,叫得开叫不开还是一回事呢。她当然可以这么说了,她自己的绰号叫如花公主,未免有点神气得过分。如花又说虎是谢了,逃课总不好。我说不逃课,哪儿来的虎呢?如花在我后脑上一推,笑道你这丫头总是不尽不实,难不成你逃课还能是为了我?我说怎么不是?如花说好了好了,下不为例。一山不容二虎,就是有例也没虎再给我杀了,我说。如花在我头上又拍一记,转身走了。她不知道我说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确实是为了她才逃课。逃课那天我刚刚知道她订了亲。订的亲,就是他。
有时候我以为喜欢上他,是天意,是劫数。要不我一贯谨小慎微为什么偏偏会对着他胡说八道什么狼牙棒?什么暗器最好?狼牙棒。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驴头不对马嘴满嘴喷粪信口雌黄,我从来没干过的事,不是劫数不是天意又是什么?但是艳阳天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狼牙棒可以作为暗器,作为暗器如果效果还很好,那么我的回答就没有错,那么,那也就不是天意。为了证明这句话,他还手把手地教我狼牙棒投掷手法。自然,艳阳天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根狼牙棒后来竟会第一个打上他自己的胸口。我们总是无法预见将来,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然而预见了将来,也很悲惨。有些人变成了瞎子,另一些人只能隐居深山终生不出。总而言之,生在江湖,悲惨是逃不脱的了。然而我们既然不能预见将来,就总还以为在将来能够从悲惨中逃脱,这简直就是一件更其悲惨的事。
十四岁的时候,我就总以为我能逃开恐惧。恐惧的源起似乎是很久很久之前的这样一个恶梦:我在沙滩上惶惶奔逃,人们嘭嘭嘭地敲着鼓打着火把执着各式各样的兵器喊叫着从身后直追过来。沙滩是软的,我的腿更软,追兵渐逼渐近,前路毫无希望,我挪不开寸步,绝望地在逃。后来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过来,听见妈妈说烧退了。烧是退了,可是有些东西再也退不了,沙滩、夜空、火光、鼓声、兵器如林、人在追——我恐惧。
因为恐惧,我手握一枚圆溜溜非常适宜于暗器用途的石子却不敢朝墙上挂着的铁锅掷去。铁锅倒扣在墙上,圆圆拱起的锅底宛如靶心,正在以强烈的体态语言呼唤每一种潜在的攻击。然而这口铁锅是轻功教官的,如果我响应了它的号召则该教官就不免会从房间里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飞掠而出,给我以相当教训。因为恐惧,我也不敢斫断坠着庞大葫芦已经绷直了就欠一刀的葫芦藤。内功教官是个酒鬼,似乎是正在试验如果不摘下这个葫芦它到底能长多大、能装多少坛好酒。这样,我就只能从它们面前一事无成地走开,从而感受到一种强烈深沉并且持久的痛苦。铁锅与葫芦藤一日存在,我就得一日痛苦。
龙儿说这是因为我欲望太多。龙儿的话近道近佛,放诸四海而皆准,独独不适用于每个个案。在这件事上,痛苦并非源于欲望太多,而在于我的欲望和别人的岔了道。譬如换一个人,看见铁锅,顶多想起炒菜,看见葫芦藤,不,看不见,顶多看见葫芦,想起喝酒。我的欲望确实已经和别人岔出很远,更严重的是,我不想把已经岔了的道再岔回来。要是看见铁锅,大家就一起抡铲炒菜,江湖上便见无数锅铲此起彼落,那情景实在也很无趣。所以有时候我又有点怀疑那个恶梦并不仅是恶梦而已,实在是一种预兆。可能是说我将来会有一天终于打破了大家赖以炒菜的铁锅,人们一边手持锅铲把碎锅片敲得叮当作响一边呐喊着冲上来和我算帐,反映到梦里,就变形成鼓声与兵器。潮水样的人们都要来和我算账,这确是够恐惧的,十四岁那年我苦思能够逃开恐惧的方法,并且一度认为已经找到了。
我找到的是他。仿佛茫茫沙滩上突然裂开一个窟窿,我噌地跳下去,窟窿跟着又合上了。这样我就算是在追兵面前平地蒸发,安全逃脱。窟窿里面也确实安全,安全到我居然一反常态地逃起课来。如果不逃课,作为红花会的晚辈弟子,我理应在刺虎的那个时间里和其他晚辈一起,呆在练武厅里向十个木偶人中的任一个发射红花镖。与对铁锅的圆锅底进行冲击的强烈愿望恰恰相反的是,我对在身上以鲜红墨点突出无数穴道鼓励你向它射击的木偶人没什么兴趣。这当然是因为我的欲望又和别人的岔了道。那一天尤其岔得厉害,以至于阿紫后来都看不过眼了,跳出来说有本事,你就不射!我说不射就不射,有什么了不起?阿紫说赌!我说赌就赌!这样,为和阿紫赌这一注,我就从练武厅里昂然直出,来到飞来峰顶。
我在飞来峰顶伤心地看着云遮雾罩中群山乱涌,后来,又一种情绪从伤心中跳了出来。我想起龙儿曾经告诫我说窟窿虽好,也不要折腾得太深。我当时的回答是不要紧,反正我要定了他。这个情节从一片柔肠寸断的氛围中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可笑。柔肠寸断是一种美丽的情感,而可笑就远远不是这样,尤其龙儿还很有可能在心底暗暗地笑着我的可笑的时候,那就更加不是这样。我生气、恼火、羞愤,几种心情瞬间混合着达到欲绝的程度,于是只能拔剑抒情,一只虎自剑尖那端出乎意料地坠落下来。
因此这只虎送给如花,也是天意。天意早就注定了的,虎是如花的,狼牙棒是我的。
龙儿之一
丫头一直没有告诉我那只虎她是怎么杀的,印象中,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她和我生分了。从我接过玫瑰的那一刻起她就和我生分了。玫瑰很漂亮,插在我腰上更漂亮,但是丫头说我象个绝世美人而不象个仙子了。
仙子是我从前的梦想。我的窗户朝东开,每到傍晚,推开窗,就能见到从海上涌起来的明月。很艳很艳的颜色,却又嫩得象要滴出水来。艳艳嫩嫩的月亮走在暗沉沉的天上,每个夜晚都显得那么孤傲清华。我很羡慕在这样的月亮上独居的嫦娥。望月久了,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月宫里凭栏眺望,长风卷来把她的长袖吹得飘飘扬扬。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在月宫里凭栏眺望衣袖飞动的人是我,是我驾着月亮,寂寂寞寞自自由由地走过天空。
丫头说我有仙气。也正是因为这个,她喜欢我。我也喜欢丫头,她有妖气。妖妖仙仙的,总之我们都不是人,要好起来也容易。丫头是个痴妖,她说我总有一天会真的飞上天去。其实真的飞上天也没有什么好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不也孤单寂寞得紧么。要是能飞能降,自由来去,那才真的不错。不过丫头太痴,不能明白这一点。因为太痴,她也不能接受那朵玫瑰,不能接受我失去仙气从天空中降落下来。可是总有一天我得降落下来,甚至远在接受那朵玫瑰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所以那天我才会对丫头说逝者如斯。
在没有降落之前,我和丫头喜欢在河岸边看风景。风景很好,近处有水,远处有山,身边枫林低语,天际飞云流动。我扯断数茎青草投往水中说逝者如斯!青草飘在丝绸般的河面上,往下游流去。丫头忽而跳起来拔剑斫水,河面被她划开一线缝隙,瞬间愈合了,青草绕过她的剑锋,继续向下游飘。丫头说未必!要是我练成风云剑法了呢?
风云剑法是很旧的一件往事,那时候我们也是在枫林边看云,云很耐看,一丝丝、一缕缕、一团团、一阵阵,在九千里外的高空上被天风吹荡,忽聚忽散,忽进忽退,连连绵绵无止无息。我说倒象是战阵攻守呢。丫头说说不定可以从中悟出一套剑法也未可知。那就是风云剑法了!我笑道,从九千里的高度上悟出这么一套剑法,天下无敌必矣!连号也一并给你取了吧,就叫天下无敌之大风云剑客!
丫头提着剑,热切地看着我,仿佛真的以为只要练成剑法就可以倒挽时光。我的心很痛。第二天我就接过玫瑰,接过恰似他的多情的玫瑰,插在腰间,从天上降落下来。
丫头不喜欢我的降落,也不喜欢他,多少次都欲言又止。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很多次,他也要对我说什么。说什么呢?从前的忏悔?今后的誓言?不需要。我封住他的嘴,他的嘴唇柔软如蜜。他的笑容如酒。他的眼睛象春天的温泉水,我只想象贵妃那样一丝不挂地走进去,再娇柔无力地让他搀扶起来。蜜、酒以及裸浴,再多一点我都不要了。可丫头却一古脑儿要了很多,爱着不能爱的人,左剑右蜜上荆下酒,全盘收受下来。有时候我想我和丫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怕痛,而她不怕。可是不怕痛,挨了痛,又如何?很多时候我想这样告诉丫头,又没有说,就好象她要告诉我什么,也终于没有说。
温泉中一抹淡淡的血丝飘出来。丫头永远不知道她拔剑斫水,那么矫健又那么无效的一剑到底是落在了什么地方。
如花之一
丫头走了。她象个精灵似的,怎么看都无忧无虑,最大的痛苦也不过是得了个难听的绰号。十四岁的年纪,就是这么让人羡慕。
房间里很暗,我差一点想开窗,手挨在窗子上,又停住了。到我房里来的人都说有股霉味,那肯定是我不开窗的缘故。妈妈有时候来帮我开窗,她前脚刚走,我自己就又关上了。
窗外是个乱糟糟的茶馆,我不想看见它。可是各式各样的声音仍然透过薄薄的窗户冲进来。我听着,总在听着,已经听了三年,似乎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人声鼎沸之中总有一天那圆润的箫声会再次清清新新地跳出来,透过窗纱,吹到我的梦边来。而我打开窗,就看见他坐在那里,穿着干净的青布衫子,肩上打着补丁,微微地低着头,在吹箫。
那是我的十四岁吧?十四岁的年纪,百样都好。窗户开着,连窗纱都绿油油的不染尘埃。窗外是茶馆,煮茶的、卖茶的、倒茶的、喝茶的、说嘴的、骂架的,天天都很热闹,看在眼里,我也觉得热闹。遇见他的那一天我就在这些热闹市声里临贴,瘦精精的柳体,仿佛剑拔弩张的江湖突然跑到纸面上了,让人写着很不畅快。箫声就在这个时候婉婉转转地透过窗纱,象烟雨三月江南水乡里的桃花竹林。
他的人却不象桃花竹林。抬眼看去,首先看见一根竹杆挑着算命卜卦的长布幌倚在墙上,布幌下面才是他。他是个瞎子,专注地按着箫,箫声甜润圆柔,眼珠呆滞灰白。我不禁悲从中来。也许我不该就这样悲从中来,可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容不得你深思熟虑。
我缩回手。其实开窗也有开窗的好处,他再来,不等坐定了吹箫,我就可以一眼看见。我只是不愿意看见茶馆里的那些人,依旧煮茶、卖茶、倒茶、喝茶、说嘴、骂架,和三年前一模一样,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吗?
他在茶馆外面呆了十天。我躲在窗纱后面也看了他十天。他还年轻,三十岁不到的样子。嘴角微微朝上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