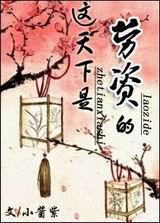这天真蓝啊(穿)-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垂头丧气的蹲下来帮他扎鸡栏。
将来有朝一日,我心血来潮写个回忆录该取何名呢?已有人取“射鸟英雄传”了,我是取“喂猪英雄
传”好呢,还是“养鸡英雄传”好呢,或是“又喂猪又养鸡英雄传”好呢,唉,伤脑筋。
第 14 章
两个人吃饭,香,饭是饭味,菜是菜味。
“草草,这两日,饼好吃,粥好喝。”我含糊的谢了谢。那份心意咱领了。
他笑了笑未应声。
我从鹅腿上撕下几块肉放到他碗里,“草草,其实我喜欢吃贴骨头的肉,有咬劲儿。”
看着碗里的肉,苏芙蓉放下筷子,一只手按按眉心,灯下,他眼波微澜瞧向我,“林中芳草本多情,
清潭冷月愿相似。寒夜孤灯照玉金,碧虽染尘心自坚。”他说的慢而清晰。
正与鹅腿奋战的我,没那个过耳不忘的天分,只记住最后一句,“碧虽染尘心自坚,好诗,好诗,草
草,你念的也好……顺,这鹅腿更好……吃。”不就是吃个鹅腿吗,也用念首诗抒发抒发?细想想,好不
容易记住的那句和这鹅腿不太搭意。
我话说完,他的手捏上我的脸,眉弯眼笑道:“英浩,小雄儿,英浩,小雄儿。”我真没做什么太对
得起他的事儿,就是把几块他买的肉放到他的碗里,何至于他感动的又念诗又叫名字的?
食物中毒了?
嘴有回味的吃完饭,我逼着苏芙蓉一同去离仕潭洗澡,这苏花身上都快成出产大粒丸的地方了。
“草草,鹿土一家是何样的人?”我边给他擦后背边问。
“卓……大叔、大婶,心地……宽厚,待人热心,我的……拳脚……之技和剑法……根基还是……学
……学自于卓大叔。”
“卓家老爹会武功?”
苏芙蓉转过头“小雄儿……想学……武?”
“别乱动,还未擦完。”打下他的肩,我接着道“学武?饶了我吧。”我现在学相扑更适合。
“呵……呵。”他轻笑几声。
我原以为落在了架空的历史,一度妄想把苏芙蓉的那套“吹尘”剑法发扬光大,我也跟着借借光亮。
如今,是没指望了,人算不如天算。
擦完了后背又洗头,少年上半身露出水面趴在潭边,眼睛轻闭,脸上泛着笑,身旁的人问一句,少年
答一句。
今夜,月白风清。
身边的苏芙蓉已睡着。可能是在离仕潭那,话说多了,兴奋,此时我无半点睡意。“富贵”的家人一
直未寻来,遂了我的心愿。苏芙蓉这里,住一日是一日,脸皮厚也要有人给你厚的机会。也许有一天我习
惯了唐朝的生活,可是,于心我不会有归属感,于斯我终是孤魂一缕。
在潭边,苏芙蓉告诉我,鹿土的爹叫卓城,鹿土的娘叫于烟晚。
天刚亮。
我躺着,鞘中剑从脑门点到脚趾尖;我起来,鞘中剑从脑顶捅到脚后跟。
“草草,苏……草……草。”嘴歪了歪,我的忍功又进一步。
院子里,挖猪圈的工具已备好,一把锄头,一把锹。
我看着地上的东西问道:“草草,你用哪个?”
“哪个……也……也不用。”
“你用剑挖猪圈?”唐朝的剑还有这用处?
他眼含秋水,灿烂一笑:“小雄儿,这……猪圈……你一个人挖。”
什么叫怒从心头起,什么叫恶向胆边生,什么叫我他妈的不想忍了。
咱是有风度的人,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脸笑容的走向他,轻唤一声“草草”,然后,在那脸上
留个珍珠手链我的满口牙印。
“这天真蓝啊。”我挺着肚子,扛着锄头,拖着锹,朝屋后走去,不就是挖个猪圈吗。
屋后那片地的土质比想像的松软,憋着一口气我挖了一上午,身上只剩下被汗湿透的裤头,我开始怀
疑本人这趟穿越,是专程过来劳动改造的。
“我是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在哪都是个老百姓。”我边唱边挖,偶尔抬起头看一眼坐在旁边抱着
剑、喝着凉水、摸着牙印的苏芙蓉,顺便给他一个咬牙切齿的笑。
我挖,我挖,挖到下午。
“草草,我的手破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见血,晕。”我做翻白眼状,跌坐在自己挖的坑里,手上
的泡还真他娘娘的疼。
苏芙蓉很没同情心的冰冷说道:“小雄儿,无人……帮得了……你。”
我算见识了他的地主面目。
挖猪圈,真乃减肥之上佳方式。
挖,挖,挖了一天。
晚上,我慢动作般的一点点儿爬上床,手着火样的疼,半睡半醒时,感觉有东西涂在掌心,清清凉凉
。
唐,开元三年,八月初一,是个没风没雨也没云的好天儿。当阳光殷勤的赶走清晨最后一丝凉爽时,
老子来唐朝后,建的第一桩大型工程“北山秀景豪圈”竣工猪圈挖成并搭了棚围了栏。
这两头猪挺好命,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的北山,比我原来住的某山某景某公寓的公共绿地上,矗
立的海拔两千毫米的某山,都高出了几个一点点。
“小雄儿,这……这三日……辛苦。”苏芙蓉手里端着装凉水的碗,站在猪圈边,一只脚轻踏围圈的
矮木栏,笑的两眼水欲滴,那一身补丁,看的我眼乱。
“何谈辛苦,正可减肥,正可减肥,草草,多谢成全。”我站在他旁边,两手来回揉着肚皮,双眼眯
起欣赏自已流血、流汗、流口水弄出的“杰作”,很有种自诩天才的得意模样,“这天真蓝啊,真啊真蓝
啊,哈……哈……,苏草草,轻点,轻点,看清了,在下这是脸。”
“小雄儿,心情……颇……好?”他手不离我脸。
“还好。”
谁说的,劳动人民永远是最快乐的。
人一旦投入到一件事情中,就容易产生热情,引发冲动。这几日,我起早贪黑的挖来挖去,竟也投入
进去,大有以挖猪圈为业的心思,就不知这大唐的养猪业发达否,老子就业的前景光明否。
撇嘴晃脑的赏够“北山秀景”,将“白虎”“黑豹”请到豪圈,我伸伸腰,“从今儿起,我,英浩就
在这儿把猪养了。”
随遇而安,乐天知命,做到之,福也。
两天前,我根据猪屁股的颜色为两位猪老弟起了名,今后,大家也算是邻居兼干亲,有个名,显亲近
。再说,以后如遇个不开眼之人想写本《开元百姓记》之《英浩传》,单听这“白虎”和“黑豹”就让爷
们我的经历平白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后世只道英浩是养着白虎、黑豹的旷世奇人,孰不知,英浩其人就是
唐朝一养猪胖子,连专业户都没混上。
“这苏芙蓉要是个女的,说不定我还会和他成一对神猪侠侣。”我摸着掌心瞧着肥猪自语道。“不知
道这里冬天下雪否,那样的话就是雪山飞猪了,嘿嘿……。”我笑的老年痴呆样。
有人拍了一下我乐的发抖的肩,回身,抬头,是苏芙蓉,手里拿一个碗,碗里装的不是凉水。
“草草?”
“小雄儿,何事……如……如此好笑。”他在我旁边席地坐下。
“哈哈,瞅着白虎和黑豹高兴。”能吃更高兴。
他笑着把碗递过来,“哦,小雄儿,这……猪圈……挖完,药……也该喝了。”
“药?”
他点头
“何药?”
苏芙蓉说出四个字,“减……肥……之药。”
一声惊雷平地起,老天爷爷,饶了我吧,我才挖完猪圈,身体弱啊。
“还喝?草草,我已决定只治标,不治本了,这药就免了。”我不想他的余生是在对我的愧疚中度过
。
他瞧我一会儿,举起碗喝了一大口,然后歪头看着我。眼神专注得让人怀疑他和我的关系“一言难尽
”。
“我喝,我喝。”让脚底的草、眼前的猪误会不好。
喝前看一看,闻一闻,喝时品一品,颜色、味道大大的改进。
……
……
一个时辰后,我知道,这一次我没吃错药。
苏芙蓉大概是请教了高人。
下午,卓鹿土的娘于烟晚来了。
“卓大婶,多日未见,可好。”我于喂鸡的百忙之中和穿着“彩虹”的女人打招呼。
“英浩见外。”她笑着说,眼角现出细纹。
于烟晚,多诗意的名字,人如其名,温柔娴淑。
苏芙蓉从屋里出来“大婶,何事……劳烦……你亲自跑来。”
“也无大事,前几日,芙蓉回家时走的匆忙,未在大婶家多耽搁会儿,临走,连你大叔烙的饼也忘了
拿,今日,新烙了些送来。”她挎着蓝子,边说边进屋。我和苏芙蓉跟在后面。
放下蓝子坐定后,她接着说:“原打算让鹿土送来,可程先生远游未归,鹿土受托照看村里的那几个
孩子。他爹,这些时日要帮张大哥家修葺老屋,一时走不开,只有我这个妇人清闲。”她说话的声音软软
的,脸上始终挂着温婉的笑。
“多谢……大叔、大婶掂念。”苏芙蓉谢道。
“多谢。”我也不拿自己当外人的谢道。
又闲唠了一会儿家常,鹿土娘起身告辞,她的背影,腰枝轻摆,黑发微扬,鹿土他爹何其幸也。
“卓大婶,好啊。”我由衷感慨。
古代的女人真是“女人”啊。
“那晚你没借住在卓鹿土家?”从鹿土娘的话里我听出点意思。
“咳……咳,小雄儿,你喂……猪了吗?”这小子答非所问。
喂完了猪,喂完了鸡,喂完了自己后,我坐在院里石墩上,打了几个饱嗝,踢了几下腿,如此的日子,幸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天已亮,太阳仍藏在东山后,清晨山谷空气怡人,眼里的山是深碧色。
我慢悠悠的走到鸡栏边,“这养鸡也是个技术活啊,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得活的。”弯身,拎起栏子里
的死鸡,对着屋里喊“草草,鸡又死了一只,这次是它自已死的,我什么也没做,不关我的事,我料想它
是伤心死的。”两天,死了三只兄弟,不伤心才怪。
屋里的人没吭声,我接着说:“草草,一会儿,我去遛猪了。”
屋里的人还没吭声。
瞧一眼栏里那只孤单的鸡:“你一定很伤心,一定很没胃口,一定很不想吃东西,不说话我就当你默
认。”说完,我拎着早逝的鸡很没人性的朝猪圈走过去。
把鸡埋在圈边,“唉,母鸡多薄命啊。是黑色的?草草似乎说过你是公的。唉,这公鸡也多薄命啊。
”不禁唏嘘一番。
安葬完鸡,我牵着白虎、黑豹出了圈,一路朝西边的树林走过去。
现在,每日早上的遛猪取代了爬山,运动强度下调了点儿,好在有苏芙蓉的“减肥药”可以治本。不
过,喝了十来天好像没什么疗效,许是我“基数”过大,效果不明显。
悬崖不远处,稀疏的树林边,一个身穿百家衣背着板凳的胖子,一只手负在身后,一只手牵着两头小
花猪,悠闲的沿着树林散步,微风拂过,胖子半闭起眼睛,脸上是怡然自得的表情,给人以在海边遛狗的
错觉。
遛完猪回来,苏芙蓉正在院里晒被。
“回……来了。”
“草草,今天天儿不错,还有太阳,晒被?”我没话找话。
“是。”
“这好像不是我们平日盖的被。”
“是。”
“我记得当日你说家中只有一床被。”
“我说的……是只有一床……夏被。”狡辩,百分之百的狡辩。
“草草,太好了,以后,我俩终于不用每人盖半截被了。”我声音雀跃,得便宜的是我,自是该高兴
。
我正和苏芙蓉说的口沫横飞时,几个身影自南而来。
在第四只鸡不幸夭折的那天,我终于见到了令我羡慕不已的卓鹿土他爹卓城。
小肉球被她娘领着走在前面,后面是卓鹿土和一个四十五六岁、身材魁梧、下巴长着钢丝样络腮胡的
男人,遗传的力量真是伟大,终明白卓孟为何那般黑,真是黑出于黑而非常黑。
我随着苏芙蓉迎出去。
“大叔、大婶,小侄……不知你们……来,有失远迎。”苏芙蓉笑着客气的说。
“英浩也失礼了。”我拱手跟着客气。
“芙蓉,不必如此,这位就是英浩吧,久仰,在下卓城,哈哈。”豪爽的声音响起,接着我的肩膀被
狠狠的拍了几下。
“原来是卓大叔,小侄对大叔是仰慕已久,今日得见,真幸也,哈哈。”我忍疼,抱拳施礼。仔细瞧
其人,五官和鹿土很像,不过脸上有几块不明显的青紫痕迹,一只眼睛微肿着,嘴角带着快好的伤。
“哈哈,英大侄子,在下是个粗人,以后,这些个俗礼就免了。”卓城边说边拍我肩拍,他恐怕是练
沙包练习惯了,再说下去老子就要内伤了。
“城哥,和芙蓉他们进院叙吧。”于烟晚轻柔的说,对我不啻是救星。
“好,好,进院说。”他看着身边的女人,声音放低、放柔了很多。
我和鹿土打过招呼,几个人一同进了院。
进到院中,小肉球挣开他娘的手,颠颠的滚到苏芙蓉的身边,拉住他衣袖,仰头:“苏姐姐,我好多
天没看到你了。姐姐,上次的鹅腿很好吃。”卓新玻璃球一样圆的眼睛笑成一条直线。
“姐姐?”我和苏芙蓉同睡过,同洗过,我咋不知道自己原来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这个肉蛋上回被女人挠过,得了后遗症?开始男女不分?
苏芙蓉疼爱的轻捏卓新的脸,笑着没说话。
他不说,我说:“小新,他是苏哥哥。”
“不是。”他认死理的说。
“为何不是。”我最近喜欢和小孩一般见识
“娘说,长的白白的、高高的、瘦瘦的,呵……呵……,还有美美的就是姐姐。”他的嘴更圆、眼更
眯。小东西的理解力不同常人啊。
“哈哈……。”我两手握了握,互相较下劲儿,打孩子也得看爹娘。
“小新,乱说,让英浩见笑了。”他娘对我一笑,拉过他,搂住。
在院里的石墩上坐下。
我先开口:“卓大叔,我听芙蓉说,你老人家会武功?”
他抬手摸着钢丝胡“哈哈,谈不上武功,防身罢了。”
“大叔常与人交手?”
“很少。”
“但不知大叔脸上的伤何来?”我未经思索脱口而去。
“这伤啊,这伤啊,是……。”他有些结巴。
鹿土他娘,拿出一块手帕,轻轻沾下嘴角,浅笑接道:“那伤是几日前帮邻里修房时伤的。”
“对,对……哈哈。”卓城笑的不自然。
“不对。”小肉球脑袋转了一圈后大声说道。
“小新,无礼。”他爹娘一起开口。
“是娘打的。”一语惊四座。